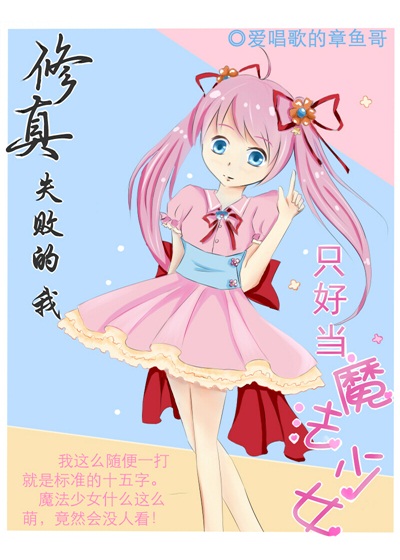失败之书-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瑞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
第一辑 空山帕 斯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 Paz)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可惜这本书在漂泊中遗失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应。周围行人涌动,买东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与诗无关。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傍晚,我打电话到帕斯住的旅馆,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你知道,这类的聚会太多了……”我当然知道,他这一年所受的名声之累,是要折寿的。
也巧了,我们下一站都是巴黎。
一周后的晚上,尚德兰(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大厅等了一会儿,帕斯夫妇下来了。他夫人玛瑞朱丝(MarieJose)是法国人,比帕斯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提议去中国餐馆,帕斯有点儿不放心,叮嘱我说:“可别乱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样的。”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还真不赖。我们吃火锅,喝黄酒,聊唐诗。帕斯翻译过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还跟艾略特合写了一本书《读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我多喝了几杯,变得伤感,大背李煜的词,把帮忙翻译的尚德兰害苦了。在烛光下,帕斯宽容地笑了。
临出门,他被一对法国夫妇认了出来:你是帕斯?
二
帕斯当过多年外交官,在法国、日本、瑞士和印度等国任职。由诗人作家当外交官,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一九六八年,帕斯为抗议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辞去了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在欧美漂流了三年,直到七一年才回国。
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Morelia)参加一个国际环保会议,这个会议请的都是科学家和作家。贫富悬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缝横贯墨西哥。我忘不了跟着汽车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们眼睛中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到山林中的一个蝴蝶巢穴考察。上千万只蝴蝶,每年从这里出发经美国飞到加拿大,再返回这里过冬,行程几千英里。坐在树林中,只见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发出轰鸣。
开完会回到墨西哥城,我给帕斯打了个电话,是玛瑞朱丝接的。她用法语大声呼唤帕斯,能听见房间里的回声。帕斯接过听筒,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我吃顿午饭。美国小伙子若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过帕斯的秘书,母亲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语跟英语一样好。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跟一个古巴作家同居。
餐馆在郊区的山坡上,外观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于花园中。若贝托去查订位名单,没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会儿,帕斯和夫人来了,他戴了一顶遮阳便帽,蓄起满脸花白的胡子,像戴着毛皮面具。
那一阵子墨西哥偏远山区正闹游击队。话题像苍蝇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贝托争论起来,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脸,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喝道:“你美国佬懂什么?滚回家去!”若贝托闭住嘴,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那天帕斯情绪不对劲,跟我也争起来。说起英国诗人奥登,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原创性,帕斯急了:“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
国际环保会议闭幕了,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我注意到记者们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什么。达官显贵并没怎么引起他们的重视,而帕斯一出现,强光灯全亮了,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当天的晚间新闻播放了他对游击队的看法,我认识的几个墨西哥朋友都在摇头。后来听说帕斯后悔了。
帕斯的名声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报刊上跟人打笔仗,打得飞沙走石。艾略特告诉我,斗争使帕斯年轻。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国做了心导管手术,不久又发现癌症,而大火得寸进尺 ,吞没了他的过去。
就在帕斯去世前一个多月,艾略特赶到墨西哥城,参加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帕斯坐在轮椅上,极少说话。当人们颂扬他的成就时,他向前扬扬手,那疲倦的姿势在说: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寿。仅仅四年前,他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美国诗人学会在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朗诵会,请来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和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等美国诗坛的大明星,也请了我,滥竽充数,据说是帕斯的提议。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中那首他早年写的《街》,仍有初读时的新鲜感。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在美国,为一个外国诗人如此隆重的祝寿,恐怕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天票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剧场挤得满满当当。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朗诵结束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天我朗诵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无门。/重重拐角出没/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没人等我,没人跟我,/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第一辑 空山蓝 房 子
一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 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回家查字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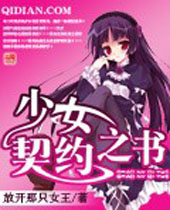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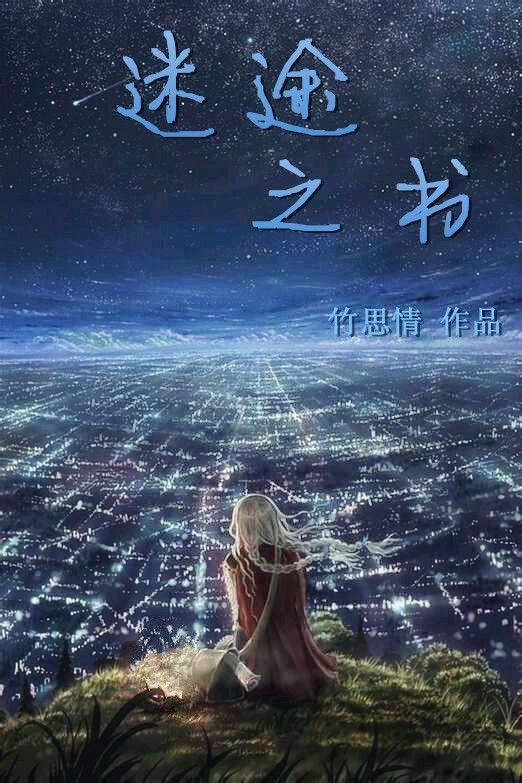
![(家教同人)[家教]芙图罗之书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