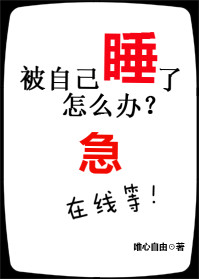谁红跟谁急-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报纸的杂志,单独一张,随正报赠送。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就正式出版了。在此之前,《语丝》也创刊了,《语丝》创刊号是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个周刊,每期十六页。薄薄的一本小杂志。
有人说,这不很正常吗,那儿辞了职,这儿办份杂志,有人请又办份副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听我往下说。
徐志摩和刘勉己,还有《晨报》的主编陈博生,都是好朋友。孙伏园辞职,筹办《语丝》,徐志摩不会不知道,徐志摩知道了,胡适、陈西滢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不会不认真考虑,人家跟《晨报》闹翻了,就自己办个刊物,我们为什么要死死地贴在《晨报》上呢。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么商量的,反正是到了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也创刊了,也是个周刊,也是十六个页码。现在我们来看看,办《现代评论》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是这样介绍的:
《现代评论》周刊,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是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上陈源、徐志摩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陈源就是陈西滢。孙伏园辞后,《晨报副刊》一直由刘勉己代编,刘勉己还是跟徐志摩、陈西滢这些人亲近些。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就由徐志摩编辑了。现在我们把上面说过的几件事归纳一下。可以这么说,撤稿事件导致了两个刊物的创办,又导致了两个副刊的对立。这样,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主要人物的留日派,和以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为主要人物的留英美派,就公开对立起来了。当然了,你们不要理解为一说对立就怎样的水火不相容,跟“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好朋友。只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在生活情趣,社会理念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8)
我曾经把《语丝》和《现代评论》前五期的文章篇数和作者人数做了个统计,是这样的:《语丝》前五期共发文章四十三篇,作者四十四人次,其中鲁迅十三次、周作人十二次、钱玄同三次、章衣萍二次、江绍源二次,共是三十五次,其他人稿子九篇(次)。从人员上说,共是十五人,也就是说,每期只有几个人。
同样的统计方法,《现代评论》每期有七个人。都是同人刊物,《现代评论》的圈子要大些。再说一下第一期的目录,就知道这两个刊物的思想倾向和文章趣味有什么差别了。先说《现代评论》第一期的:
时事短评三则 涵、皓、松三人分写
法统与革命 燕树棠
时局之关键 王世杰
清室优待条件 周鲠生
叫化子(小说 西林
十一月初三(小说) 郁达夫
翻译之难胡适
“非列士第恩” 陈西滢
西林就是丁西林,郁达夫小说较长,不是一次登完,一次只登一小节,好几期才能登完。再看《语丝》第一期的目录:
生活之艺术 开明(周作人)
记顾仲雍伏园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
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钱玄同
清朝的玉玺 开明(周作人)
夜里的荒唐 川岛
译自骆驼文 绍原
月老和爱神 衣萍
“说不出”鲁迅
从文章的题目上可以看出,《现代评论》是个关心时局的文化刊物,《语丝》是个注重个人情调的文化刊物,《现代评论》的格局要大些,《语丝》的格局要小些。当然要是打起笔仗来,两个的格局又都一样了。
两个大的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日后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后来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的互相攻击,闲话事件所以能酿成那么大的风波,根子都在这儿。这些大的事件我就不说了,我说两个很小的事件,就知道这两派是怎样争斗的了。第一件是投稿。孙伏园辞了《晨报副刊》的职务,筹办《语丝》时,想来是向徐志摩约了稿的,这样第三期上,就有了徐志摩的文章,是篇译诗,还带个小序。鲁迅看了不干了,就在第五期上发了篇《“音乐?”》给以讽刺。先不说对不对,应当说这样的互相驳难,在文化人之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别的目的呢,就不能说是正常了。且看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十年后,敢说真话了,在《集外集》的序里说: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结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这就明白了,鲁迅写文章,不是驳难,而是为了“使他不能来”。
再就是,鲁迅自己也说了,这是他和“新月派”,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结仇的第一步。
刚才说了,办《语丝》的起因是撤稿事件,那篇没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我的失恋》,《语丝》办起后,就在第四期上发了。光登那三段还不过瘾,鲁迅又添了第四段,且看第四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样一来,这首诗讽刺的对象就更明确了。当时在北京城里,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而梁家是有汽车的。
再说第二件事,可称之为“答卷事件”。好多人都知道,对于看不看中国书,鲁迅有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就是答卷事件中,鲁迅在答卷上写的话。
孙伏园办起《京报副刊》后,为了吸引年轻人,就搞了个征答活动,一个是“青年必读书十部”,一个是“青年爱读书十部”。先看看广告原文。青年爱读书十部就不说了,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的刊首广告中是这样写的:“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设问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我写《徐志摩传》时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查过《京报副刊》。报纸很旧了,根本不让看原报,看的是缩微胶卷,办好手续后,给你一个胶卷,在投影机上自己看,用手摇那个把儿,摇一下转一圈,想要印,标出来给你印。好些问题,只有看原件,看全部材料,才能明白底细。比如鲁迅的这个回答,只看鲁迅的看不出什么,只有看了全部,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我的看法是,这是鲁迅在出气,在赌气。为什么呢?一、他并不是真的主张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证据是也就在这前后,他的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许寿裳想让鲁迅给他儿子开个书目,他就开了,全是中国有名的经典。二、因为第一个刊出的学者是胡适,接下来还有梁启超等人。鲁迅就不高兴了,就要跟这些人闹闹别扭了。怎么知道前面有胡适呢,我也没有真的查到原文,我是从《鲁迅全集》上看到一句话里推论出来的。在鲁迅《集外集拾遗》中有篇文章叫《聊答“……”》,文后附一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其中说,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先看“青年必读书”再看“时事新闻”。于此可知,第一个刊出的是胡适,至少也是胡适在鲁迅之前。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9)
鲁迅上面那句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非写在答卷里,而是写在附言里,正式答卷上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理睬。这样的事,也只有鲁迅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从鲁迅这边也很好理解,你这个孙伏园,固然是因为我的那首诗让你辞职的,可你辞职后,我组织人给你办《语丝》,又想办法让你进了京报社,可你倒好,一得志马上又和胡适这些人搅在一起,那就对不起了,我要给你个小小的难堪。说是给孙伏园难堪,实际上是向胡适等人叫板。鲁迅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闹翻了,就结成死仇,不管做什么,不管对不对,都要对着干。
可以说,撤稿事件以后,鲁迅就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可以说,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了。甚至可以说,从此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凶猛的对手,一路打下去,直到到了上海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结成强大的阵线,向着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轮番进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后期之分,可以说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如果嫌“撤稿事件”太小的话,那么到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分别创刊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在前期,鲁迅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在后期,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闹翻后,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了。而且一直反下去,直到去世。这样说,一点都不否认鲁迅的成就。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事业,对中国文化新军的建设,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个了不起文章大家。这上头,谁都得承认。
最后我要强调一句。研究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眼光。要记住,历史应当是一条河流,不管怎样惊涛拍岸,怎样浪花飞溅,它的流向一定是归于大海,它的流程一定是顺畅的,奔涌向前的。不能说遇到一座高山,它也能从山梁上翻过去。它能绕过去,能冲开个口子流过去,绝不可能翻过去,除非这边积起一湖水,把山梁淹了溢过去。要是那样的话,也还是顺畅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批评。一定要记往,我不是来宣布我的结论的,我是来教你们研究问题的方法的。只要你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得出什么结论,并不重要。
也谈鲁迅的买书
好多人都谈过鲁迅的买书,尤其是一些作家,一说起买书,就说鲁迅出手怎样的大方,一年买书花了多少钱,一生又花了多少钱。还有的作家,比如孙犁先生,据说是按鲁迅书账上的书目买书的。这自然是因为鲁迅每年都记有书账,其详实几乎无人可比。再就是,一般作家,难得看到同时代别的作家的购书记载,无从比较。
实际上,鲁迅买书是很仔细的,并不怎么大方。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是要买一部《四部丛刊》还是什么大型丛书,书商索价400元,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买。那时鲁迅不过五十出头,绝不会想到几年后就去世,当时已到了上海,正是他稿费最丰的时期,给了同等条件下的读书人,准会毫不犹豫就买下。鲁迅一生藏书的数量,北京、上海两地的合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册(卷)。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而线装书的卷数是无法跟新版书的册数相匹配的,那个总数又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从全集所载书账看,鲁迅一生买书,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一二年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南下,为第一时期,每年买书款相当于他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300元)。一九二七年到上海至去世,为第二个时期,因为北京的书没有带出来,生活安定下来后,便大量买书。这里只说整数,一九三零、一九三一年两年最多,分别为2404元、1447元,其他年份数百元不等,没有上千的。
再看看几乎同时期的作家学者,就知道是怎样的境况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穆应聘到燕大、北大教书,先还是在图书馆借阅,后来大量购藏图书,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五年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罗义俊《钱穆传略》)。
这相当于鲁迅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可找个对比的。
据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那时有名分的读书人买书,都是先记账,到了节上书商来家里收钱,买者也不是全给,能给半数就不错了。从后一句话看,欠270元,只给了160元,等于是给了六成。共开了400元,等于买了600元的书。一年按三个节算(端午、中秋、春节),则全年是1800元。比鲁迅同期的书账开销,几乎高出12倍。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遗失,按前后两年的平均值算是143元。
再将鲁迅购书款占其收入的比例,与我们当今读书人的相比,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时期,不算稿费收入,光在教育部当佥事的月薪,加上在北大等校教书的月薪,不少于400元。这期间,每年买书款平均是245元,每月合20元,占月薪的二十分之一。我们现在一个正高职称的读书人,月薪是800元,二十分之一是40元,也就是说,只要每月买上两本书(一本按20元算),就比得上鲁迅在买书上的开销了。而买两本书,据我所知,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做到。
末了得补充一句,这是不能比的,因为钱跟钱不一样,那时是银元,现在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