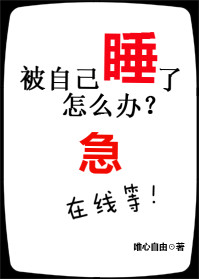谁红跟谁急-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了就不必读了。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可反过来理解,那就是少年时要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不迟。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沉郁的苍凉,都是常人难以比并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酷评路遥
究竟是谁某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
韩石山酷评路遥
这篇文章,严格地说,不能说是单篇文章,最初是《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中的一段。后来觉得这段文字可以单独发表,就把它提出来,重新写过,另拟了这么个题名。那篇《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也收入此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比较一下,看两者有什么不同,看我改写的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手脚。
新时期作家中,我认识路遥是相当早的。一九八零年春天,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里学习,路遥曾来所里向我约过稿,那时他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不过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朴实,强壮,谦恭,我对他的印象很好。然而,他在写作上表现的那种蛮狠,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个奖得了,还要得那个奖,和这个比了,还要和那个比。秦晋两省相邻,消息相通多些,有那么几年,常听到秦地那边传来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总觉得秦晋两省作家身上的农民气重了些,把写作当成了种庄稼,一份耕耘,就一定会有一份收获。在山西,我多次说过这个话,但山西没有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必须是定了格的才有说服力。不能你今天说了他不怎么样,明天人家拿出了惊世的作品。路遥恰符合这样的例子的要求,他写了《平凡的世界》,不久就去世了。这样说有点残忍,批评要的是无可辩驳,也就只能拿老朋友下手了。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后人有所警惕,勿蹈覆辙,绝不是真的和路遥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是谁谋杀了路遥
路遥去世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不厚道,也就没写,现在是不是就该写了,也不知道,大概还是不该写的。只是我已经老了,再不写,往后怕没这个兴趣了。纯粹是为自己,还是写出来吧。
新时期以来,年龄不大而死了的几个著名作家中,我认识的,只有一个路遥。一九八零年初,我在文讲所学习,其时文讲所还在北京左家庄的朝阳区委党校,左家庄这个名字,现在想起来很有意味。路遥代表《延河》编辑部来组稿,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了。那时他还是个普通编辑。第二次见面,是多年之后。他在延安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家不错的饭店请他。这时的路遥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席间,我们向他敬酒,他的憨直的弟弟左一句“厄(我)哥有病”,右一句“厄(我)哥累扎咧”全挡了驾,弄得大家了无兴味。又过了两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没多久便听到他去世的噩耗。
活活叫累死的,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出版之后,我没看过,内子看过报上的连载之后,这么给我说。她说她怎么也弄不懂这位陕西的作家,家在西安,要写长篇了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到了延安哪里不能住,非得住在窑洞里,住在窑洞里也行,为什么明知晚上要加班,不准备些食物,非得弄到吃多少天前剩下的霉窝窝头不可。写完一部长篇本应当是兴奋不已的事,为何竟厌恶到将笔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是懂得的。那时,我已当了一任县委副书记回来,知道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干部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开始反思自己过去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写法究竟值得值不得,正在思谋着怎样轻松地写作,挣上大笔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路遥是个苦孩子,大学是混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他的文学成绩主要得益于模仿。模仿激发了他的灵气,升华了他的生活积累,模仿也使他便捷地掌握了前辈的写作方法,轻易地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好了还要再好,他心里的目标是那个茅盾文学奖。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模仿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非独路遥为然。山西的作家模仿赵树理,河北的作家模仿孙犁,陕西的作家模仿柳青。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文学也像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赵树理虽有土性,但性格中有的是幽默,于是山西作家也下乡,只是下了乡绝不会太苦了自己。孙犁的风格是清丽、飘逸,你想让河北作家吃苦他们还怕坏了自己的手气。陕西作家真不幸,摊上个柳青,那是个肃穆而又古板的人,于是陕西的作家便下乡就是下乡,吃苦就是吃苦,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了。
光是吃苦,放不倒这么一个壮实的陕北汉子,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的鼓励或者说是蛊惑。要写厚重的作品,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要挖掘,深深地挖掘,挖掘人物的本质,挖掘事件的底蕴。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与它的伟大相匹配的作品产生。
于是这只知蛮勇的农村孩子,知道光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买两件新衣裳还远远不够,还要亲手织一件能笼住天下的母亲和妻子的华丽的衣衫。于是这苦命的农村孩子便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终结。
究竟是谁某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那些鼓励或蛊惑过路遥的文学评论家,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懂不懂得文学了。
酷评中国文学
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你吓一跳,中国作家整个是个军事建制呀。这样一支虎贲之师,威武之师,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敢说,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评委诸位老儿则是绰绰有余的。
韩石山酷评中国文学
我这人真是够缺德的了,用北京话说,是缺德带冒烟儿。钱锺书先生那样的博学鸿儒,我一下笔就大加诋毁,汪曾祺先生那样的厚道君子,也是那样的讽刺挖苦,路遥先生曾组过我的稿,人一死马上就掘墓鞭尸。
这里又有三个更为恶劣的例证,且分别言之。
一,早在一九八零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刚刚开办,从全国各省遴选第一批学员,好些省份都没有,山西就我一个。而在《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一文中,我竟说它是个文学写作的扫盲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至于此!
二,我本人是个作家,还是靠写小说出了名的那种作家,但是只要看一下这篇《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就可知道我这个没有多少才华的作家,对那些勤勉写作且才华横溢且声名远播的作家是多么的嫉恨了。
三,最可恶的该是这篇《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我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也可说是某一军的副首领。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可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兵,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机构,也可说是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可是,仅仅因为作家们平日写文章,或是各地作家协会的头头们出于工作的需要,叙述的方便,说了个什么军,明情是个比喻,甚至不妨说是噱头,我就当真了,曲意编排,大加攻击,且说出“热衷此事的是那些平庸的作家和同样平庸的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这样毒汁四溅、杀人无算的话。
这个人,是没救了。
然而,我不后悔。因为我生在这个年代,我爱我的同胞,我爱我的国家。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1)
接连两天收到两本书,一本是《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本是《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前者寄我,因为我是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文讲所是鲁院的前身。后者是采编此书的郑实女士寄来的,她的夫君傅光明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
这半年编刊物,忙起来如同老板,闲下来又如同弃妇。这几天发了稿,正是弃妇期间,断断续续的,这两本书都看了。是怀着敬意看的。鲁院是我的母校,我是她的学生,母子情深嘛。浩然是前辈作家,撇开政治信念不谈,以他这两年表现出的那种决不改悔的铮铮铁骨,我是把他看作陈寅恪、梁漱溟一流人物的。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货色。
然而,人心之险恶,虽蠢笨如我,亦难幸免。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一位久为文坛遗忘的人物——高玉宝,同时想起的还有另一位,我说的是情况与高相似,而名声没有那么大的崔八娃。据前两年专程去西北某地,看望过崔八娃的一位记者说,此人完全成了一个文盲,问他过去写文章的事,已不记得了。我上小学时,课本上选有他俩的文章,高玉宝是有名的《半夜鸡叫》,崔八娃是《狗又叫起来了》,文末那句“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至今我仍认为是极富意境的文学语言。脑子怎么走的神,已无踪迹可寻,那结论却让我大吃一惊,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是不是正发高烧而不自知?
我的结论是:
浩然——一个还有点才气的高玉宝。
鲁院——一个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的扫盲班。
纵然不发高烧,下面的论述能不能自圆其说,我仍没有把握。试试吧。
先看高玉宝是个怎样的作家。《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上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一九二七年生。辽宁瓦房店人。九岁给地主放猪。十岁至十五岁从农村流浪到大连当童工,后当过劳工,学过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等。曾参加辽沈、平津、湘南、广西战役,多次立功。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途中,开始学习识字、写作。一九五一年初,以不凡的毅力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草稿。一九五四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九五五年出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五八年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一九六二年毕业,回部队工作,任文艺干事。曾任旅大警备区大连俱乐部主任,现为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创作员。
再看看浩然是个怎样的作家。同词典中也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生于开滦煤矿。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一九四六年起,当过八年村治安员、区团委书记等基层干部。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任河北日报记者。一九五六年任《俄文友好报》记者。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六一年任《红旗》杂志编辑。一九六四年起在北京从事专业写作。是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东方少年》主编。一九九零年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苍生》等。
两人的革命经历大体相似。学历上稍有不同,高玉宝没上过学,浩然上过三年半小学和半年私塾。词典中半年私塾在后,三年小学在前,好像是上过小学再上私塾,想来绝不会是这样,该是先上私塾后上小学才对。浩然自己曾著文说,他只上过三年小学,成为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云淡了才会显得天高,水落了石头才会出来,为了达到这种比衬效果,学历不高的作家们,说起成就总是越高越好,说起学历总是越低越好。这或许是全世界文人的通病,中国作家似乎更厉害些。对自己上过三年小学,浩然心有未甘,成心要与高玉宝一比高低。《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文字,足以证之:
恰巧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之时,一个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就以一种移山填海之势,在中华大地展开了。设在蓟县城里的干部业余学校在西北隅,即独乐寺东北边一家倒闭的手工作坊里。我大步流星地奔向那里……老校长摘下老花眼镜,仔细打量我一遍,又有些疑惑地问,你还用到这种以认字、识数为主的学校来吗?我回答说,是呀,要当一名普通随大流的干部,不学也凑合够用。不过,我想搞写作,光认字、识数就远远不够了,我得加紧学习文化知识。不然的话,搞写作只能是做梦!……就这样,我又入了学。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因为浩然上进心切,才来这种类似扫盲班的地方学习。不,以浩然当时的知识水平,他就得入这样的学校。就在入这个学校前,他收到《河北青年报》的退稿信,信上就说,他的作品“字迹写得潦草,错别字也很不少,所以稿子距离发表的水平还很远”。这样的水平,只配上这样的学校。
不管怎么说,浩然的成就比高玉宝大多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印了那么多,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见该书封底文字)。且不说这里的“最”还有待查实,即使真是这样,也毫无意义。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就算真是这样,若以发行地域之广而论,不说别人,就是跟高玉宝比,还要稍逊一筹。高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当年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肯定无此殊荣。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2)
至于写得怎样,不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