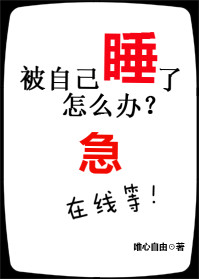谁红跟谁急-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一颗金丹来了——多么到家的功夫。
《听听那冷雨》,是余氏散文的又一名篇,我曾在一本为中学生写的小册子(《得心应手》)里,引用过一段,作为“炼字”的典范。说白了,也不过“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那一套。容我说句刻薄话,这不过是港台三流歌星的句法,在内地,任何一个稍稍有点才气的中文系二年级女学生都会这一手。未必有他那么丰富的联想,至少不会像他那么矫情,那么别扭。
李先生不是最信服港台学者的话么,请听听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港台学者董桥是怎么说余光中的。台湾巨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是余光中、洛夫、聂华苓等九人编选的,书前有余光中的总序。董桥看了,在评论文章中说——
文字蛮顺的,说理叙事也清楚,一点没有他过去散文那种妞妮的“骚”味。这是余光中的进步。(《董桥文录》第86页)
绝无贬低余光中的意思。各人的才分有差别,学养有深浅,对余氏来说,能把汉字用到这个样子,也不易了。我要说的是,余秋雨的缺憾自是他的缺憾,他的优点,虽不必用李先生那样的词句去形容,也自是他的优点。作品在那儿摆着,谁也能看得明白。犯不着惊动余光中这样水准的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位台湾学者,就请来鉴定余秋雨。两人的散文虽不无某些相似之处,但从大的方面说,比如感情的酣畅,此余(秋雨)胜了彼余(光中)不止一筹。拿彼余来鉴定此余,别人感觉如何我不敢说,至于我的感觉,不客气地说,只有四个字:不着边际。
若说余光中是杆秤,这杆秤的定盘星先就钉得不是地方。
有道理说自己的道理,好赖总能说个清爽,别动不动就搬上个海外学者唬人,不说对他人怎样了,先就是对自己不相信,不尊重。这就是我要对李秀生先生进的一句忠言。至于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我一点也不反感你说的那些话。无论什么评价,只要是你的就行。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二零零三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是较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有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吗。你写的是文化散文,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去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一九七零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一九七四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要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最近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酷评余杰、摩罗、孔庆东
看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以当代鲁迅自命的思想随笔作家吧,他们是要把鲁迅走过的路倒着走。这话不确,只有在他们多少年后,依次出了几本散文集,几本学术著作,几本(至少两本)小说集之后,才能这样说。
韩石山酷评余杰、摩罗、孔庆东
这要算是一篇游戏文章。我有时候写文章,不一定是觉得对方有多大的不对,而是觉得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就写了。在文学批评上,我是信奉“艺术至上”原则的。有时意思很好,气也很大,但一想写不成好文章,就不写了。
余杰、摩罗、孔庆东,据说是北京大学有名的才子,都是年轻人。对年轻人的批评,我向来是慎之又慎。总觉得这年头能冒出来不容易,得成全他们,至少不必伤害他们。这篇文章中,看似嘲讽得很厉害,实则还是喜爱他们的。只是想告诉他们,要在文坛安身立命,卓然成为大家,不能光写杂文,还是要做真学问,有真本事。
有人会说,你还是太狠毒了。我说,你看写得多风趣,那一二一的步伐,那倒着走的模样,不全是一幅幅漫画吗?再看看我是怎样批评谢冕的,批评孟繁华的,就知道我对这几个年轻人是多么厚道了。
批评并不总是气冲冲的,也可以是笑嘻嘻的。
倒着走的“鲁迅”们(1)
一二一,一二一!大街上走来一队人,一律的青布长衫胶底鞋,一律的浓浓黑发平板头,一律的隶书一字的黑胡须,一律的一米五几的矮个头,一律的稍微外斜地摆着不长的手臂,一律的横眉冷对的深沉模样。
这不都是些鲁迅吗!
本来已经够惊奇的了,仔细一看,人们更惊奇了,怎么都在脸朝后,脚后跟朝前,迈着短腿,噔噔噔地走着?
这是一条文学的大街。行走着的全是些当代的青年作家,更具体点的头衔该是思想随笔作家。依稀能辨出其中有余杰、摩罗、孔庆东等人的身影,还有一些,分明都能叫出名字,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是我眼前的幻觉,却不能说是不真实的。说他们是鲁迅,或自比鲁迅,不是我加给的恶谥或是美誉,乃是他们文字的彰显,评论者的归拢和推断。且看下面这些话:
孔庆东在为余杰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写的序中说:“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汽。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撰文称赞孔庆东说:“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是长久的。”
摩罗在《什么是写作》中说:“所谓写作,乃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与确认,是对天上与地上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规划与建立。我不但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也这样理解一切受我尊敬的作家的写作。当初读卢梭、读拜伦、读鲁迅、读卡夫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理解的,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余杰将这本书题款亲手交给我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缅怀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缅怀了陈独秀、鲁迅、蔡元培。”
余杰则是这样称赞摩罗的:“我认为,摩罗的文章是二十世纪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余杰在批判了王蒙,刘心武、谈歌、刘醒龙,贬损了路遥、陈忠实之后,说:“摩罗继承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的视角,而又有所超越。”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春光灿烂三兄弟》,载《山西文学》二零零一年第六期。作者苏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他们内部之间彼此的吹捧,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可用来吹捧抬举的词语都翻出来,一股脑儿地搁在对方的身上。我说你是鲁迅,你就说我是哈维尔,我说你是君子,你就说我是楷模,你说我是大侠,我就说你是壮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可见说他们是鲁迅,或自比鲁迅,不是我加给的恶谥或是美誉,而是他们文字的彰显,评论者的归拢和推断。
至于说还有一些,分明都能叫出名字,一时却想不起来了,不过是掉个花枪。他们那么大的名声,我又这么好的记性,怎会事到临头而想不起来呢。所以这么处置,一则他们几个中,似乎没有这么无聊地相互吹捧过,也没有这么不知羞耻地自命不凡过。再则,他们不是北大的,我对他们也就不像对北大学者、作家那样敬重。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北大的,可不能这样,西门牌匾那宝蓝色的底色,映衬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未名湖上潋滟的波光,折射着中国文化往后几千年的瑞祥。爱之深,责之切,我这没资格上北大的村学究,总也抹不去的是对北大的敬仰。
下面再说我那个幻觉是怎么来的,即分明是些鲁迅们,却为何是在甩着短胳臂倒着走路。
鲁迅的著作,均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全集是以单本著作为单位收录,同时又要考虑单本著作中单篇写作的时间,不免有些凌乱。比如以单本论,《呐喊》出书早,《坟》出书迟,而以书中单篇论,《坟》中有些文章又早得多,这样就把《坟》放在了《呐喊》的前面,给人的感觉是鲁迅先出了《坟》后出了《呐喊》。好在全集中,附有《鲁迅著译年表》,我们且根据这个年表,看看鲁迅先生一生写作的大致脉络。
一九一八年之前,有一个时期辑校《稽康集》等古书。本年写成《狂人日记》,可视作文学创作或是新式写作之始。三四年间,完成了《呐喊》中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底编起,一九二三年新潮社出版。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小说十一篇,结集为《彷徨》,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出版。这期间,《中国小说史略》上下两册,分别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出版。也就是说,鲁迅在六七年间,已奠定了他小说家和学者的双重地位。鲁迅的写作是比较迟的,《呐喊》出版这年四十二岁。
他的散文集有两个,一个是《野草》,一个是《朝花夕拾》。前者收录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散文诗(实为散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后者收录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坟》是他的第一个杂文集,收录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章,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一年鲁迅到了上海,此后他的写作就进入了以杂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到去世这年,经他自己亲手编辑的杂文集子共计十本,其中《且介亭杂文》两集是去世后才出版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兼有作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写作的顺序是:小说、学术、散文、杂文。其中学术贯穿了一生,直到晚年才停下来。散文可说是从小说写作到杂文写作的过渡。杂文则是由少到多,后几年专事之。
倒着走的“鲁迅”们(2)
于此可知,鲁迅的杂文虽然造诣极高且历久弥新,而他是以小说作家和中国文学史学者立身的。现在的年轻人,多以杂文家视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怕会长嘘一声,继而言道:何物小子,无知乃尔!
鲁迅是军校出身,按步兵操典走走步子该是行的,假如文学是一条大道且是分段的,鲁迅迈着“一二一,一二一”的步伐,是小说、学术著作,散文、杂文这么一段一段走过来的。
再看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以当代鲁迅自命的思想随笔作家吧,他们是要把鲁迅走过的路倒着走。这话不确,只有在他们多少年后,依次出了几本散文集,几本学术著作,几本(至少两本)小说集之后,才能这样说。但他们既然以鲁迅自命,且已走上了第一段,我们也只好这么说了。虽然这么说实际上是一种透支。从后往前走,还要学鲁迅的样子,在我的幻觉或者说是感觉上,他们就是在脸朝后,脚跟朝前倒着走。
鲁迅出过十几本杂文集,这几个年轻人,想来也出过六七本思想随笔集了吧,也就是,正走到鲁迅第一段路的中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