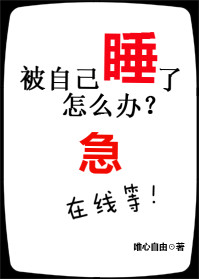谁红跟谁急-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鲁迅出过十几本杂文集,这几个年轻人,想来也出过六七本思想随笔集了吧,也就是,正走到鲁迅第一段路的中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不想说什么刻薄话了,君其勉旃!
还得补充两句,对余杰,摩罗,孔庆东诸位,我的态度与对谢冕和他的那几个弟子不同,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的。先拿出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创作或是学术著作,再当什么思想随笔作家不迟。路要顺着走,不能倒着走,那样子不好看。
酷评钱锺书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韩石山酷评钱锺书
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赞美他的,和批评他的,很可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不得要领。从小说层面认识他的,看到的是他的诙谐、多智,是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从学术层面看他的,看到的是博学多识,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若是想到他成名于解放前,生存最久的又在解放后,处逆境而自甘淡泊,受尊崇而不事张扬,还得说是个耿介之士。尤其是他的死,那么平静,那么简约。综合这几点,可以说,只有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
我对钱氏,绝无一究其底里的奢望,只是对他的为人与为文,有一些兴趣。写他的“淫喻”,评他的“赞语”,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对他的为人与为文,能会心地一笑,已然是了不起的理解。虽然如此,在别的文章中,对他的学问,也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记得曾说过,要靠他的《管锥编》打通中西文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还说过,他的学问有多大,若用白话文写出来,就全明白了,用文言文写出来,实在不敢恭维。为这几句话,还受到几个坚定的钱迷的攻击,说我是无知,是伧夫。我没有辩白,本来就是伧夫,就是无知嘛。
然而,待到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围城》的校注本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大张挞伐,为《钱锺书与》一文的笺证对辽宁的范旭仑、李洪岩提起诉讼,我就觉得这两位大作家大学者做得有些过了。偌大年纪,偌大名气,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些许小事上动真格的呢,“四人帮”肆虐多年,也没见你们动过这么大的气,怎么几个年轻人不过是因为热爱你们才校注、笺证你们的作品,就这么不依不饶呢?莫非钱、杨这样的大智者,到了晚年也会像常人一样糊涂了吗?
钱锺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锺书先生对比喻的卓识,颇为人称道。两柄执何柄,多边据何边,却不能说与取喻者的心性没有一点关联了。不是精确的统计,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瞎猜,根据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我忽地悟出,钱先生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薄薄的一本《写在人生边上》中,顺手就可捡拾这么几例——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
对一则伊索寓言——老婆子想让母鸡一天下两个蛋,便加倍喂养,结果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钱先生却说:“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小心眼。”似乎和男女之事无关,细想一下不难明白其奥妙所在。
有本传记中说,钱先生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英制烟斗赠予友人,也俏皮地用了个“淫喻”:“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于此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妙喻,钱先生平日也是“曲不离口”的。
若有人将《围城》中的比喻摘出来,作一种统计学上的考察,这类由男女之事取喻的例子,怕也不会少。
《红楼梦》里有意淫之说,那是第三者的宏伟蓝图,比手淫便捷而不实用。钱先生取喻多涉男女之事,可说是“喻淫”了。只是这喻淫较之彼意淫,要艺术得多,也高尚得多,可说是一种雅淫。盖因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平常之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取喻,最能为人理解。文字典雅而内里涉俗,又由极俗而体味出极深的意蕴,正是取喻的精义。
然而,行文中述及男女之事,也如同猴儿从火中取栗,稍一不慎,便会烫着自家的手指头。正惟其有这种危险,烫与不烫也就看出了技艺的高低。钱先生的高超处在于,他从男女之事取喻,只让你感受到作者的聪敏机警,却绝然不会想到龌龊。这一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或许不无小小的启发。再往开里说,联系钱先生少年时的“顽劣”,如与堂弟锺韩在隔扇上刻“刺宝宝处”等,还可看出这位大学者品格中最富人性,也最为明丽的一面,不知众多的钱学家以为然否?
钱锺书的赞语
钱锺书赞人,语多夸饰。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正好来了个引子。
今天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证据是《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
作者还说,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第三版)
此文作者马斗全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同校同系的校友,不过我早他十多年离校罢了。这几年马先生的文章车载斗量,风行天下,我是极为钦佩的。看了这篇文章,却不免生智者千虑之叹。
先得说清,能得到钱先生的赞赏,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不光因为钱先生是当今的“文化昆仑”、“博学鸿儒”,还因为钱先生素有出语刻薄的“恶名”,你想嘛,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看得起谁呢?这样的人忽然有一天对某人表示“极佩”,此某人该是何等了得。文中为了坐实“称赏最甚”四字,还给钱先生添了一个“莫须有”的品质,说钱先生“对文化界一些人士的评论,如他治学一样,极为严谨负责,从不轻易称赏什么人,更不廉价地送人以溢美之辞,为文化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且不说年轻时和年老时不一样,写信和写小说不一样,就算确有其事,确有其言,怎么可以当真呢?
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
像这类动不动就“可惊可佩”的信,钱先生在世时,不知写过多少封。手边有本《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出版,范旭仑等编),内中有篇《钱锺书书札书抄》,随手摘录几则看看。
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喷珠漱玉之诗,脱兔惊鸿之字,昔闻双绝,今斯见之。”罗家伦的诗和字真的就这么好吗?可罗是他的校长,不这么说你叫他说什么?
给孔凡礼的信中说:“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柢,叹佩之至。”对一个年轻人,钱真的就佩服到“至”的程度吗?
下面四句赞语,是从四封信里摘出的,请猜猜是给何许人的:
“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
“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
“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
“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的。告诉你吧,这是称赞一位叫何新的年轻人的。
是不是钱先生真的不负责任,就这样随意夸赞他人呢?不是这样。这只是个礼数,该说什么他还是要说的。比如赞何新的第一条,何来信中可能想要钱先生一本书,钱先生说他新出的书“为友好索尽,未由呈献通人,尤所疚憾”。只看字面,自己的著作不能呈献给通人指点,你以为他会难受得要哭吧?错了,他只是要说“不给”,至少也是这次给不成了。再如赞何新的第四条,何的来信中似乎要以钱的某书为题写文章,钱说:“你可写文章的题目很多,何必用拙著呢?”等于明说“我的著作不用你评”。
像这样的礼数,还可以举出一些。过去的时代,教师给学生的信中多称学生为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前,给许的信里就称许为兄,绝不是鲁迅早就心怀叵测,要先在辈分上拉平从而恋爱之。闻一多信中称陈梦家为兄,陈是闻的学生,不知轻重回信自称弟,闻大为恼火。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他是京剧大师,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不容易”,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
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
反叛了的“钱迷”
一九九八年的文坛,似乎平平淡淡没什么新花样儿,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从年初就闹起的“马桥事件”,到年底都完不了。那是你不细心。细心的人们仍可发现,在这平静之中,还是有几个热点的。一是对知青作家文学品质的指摘,一是“钱迷”的反叛。这里只说后一个。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