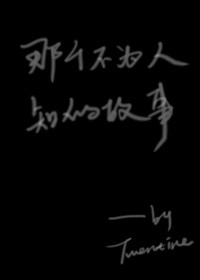7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王朔-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不能一概而论。”张名高发言。“有爱情不一定结婚,结婚也不一定没爱情。”陈主编拿起那根一直搁在桌上的烟,林一洲忙划火给他点燃。陈主编:“你结婚了吗?”
林一洲:“结。”“够累的吧?”“可不,小三儿都进过公安局了。”
“哎哎,你们是不是另挑个日子再开婚姻与爱情的座谈会,拉上妇联的侃侃?”于德利朝沸沸扬扬的众人嚷。“我这跟作者还没交流完呢——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既然好成这样儿,后来就该结婚,怎么又吹了?你这是悲剧吧?我没看结尾,不知道往后的事。”
“后来……”李东宝看林一洲。“后来也没出什么事对吧?”
“对,没大事,都是小事上过不去。”林一洲说。“感情依生生活习惯产生矛盾,不断冲突,不断积累,只好分手。”
于德利:“挥泪分手?”
林一洲:“噢,哭过—场。”
“这听着倒有点意思啊。”张名高对陈主编说:“硬拽两把,能跟‘新写实’套上。”“嗯,改好了相当有意思啊。”陈主编仰头吐出一个又大又浓的烟圈。“烟圈烟圈。”戈玲指着笑。“还说不会抽,老烟枪了。”
“不行了。”陈主编笑着挥手赶散烟圈。“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还能吐出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呢。”
“哎,女的认识男的之前另外有男朋友吗?”牛大姐探着头问林一洲。“没有。”林一洲回答。
“男的呢?没跟谁竹马青梅?”刘书友也问。
“也没有。”林一洲客气答复。“那不好,应该有,你说是不是老牛?”刘书友挺不满意。“应该多设些相思局,多来几角儿,抱起这个放不下那个,这才好看也真实。我们人的0处境都是介于两难之间的嘛。要多写写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恼。”
“应该有一个不要脸的女流氓或者男流氓,总在里头捣乱,不让人家好好过日子。”牛大姐说。“批判批判那些不道德的第三者。干嘛专搞别人的配偶!”
“就写女流氓吧,比较普遍。”刘书友瞪着眼睛绘声绘色地说。“听说了吗?皮肤科的号现在最难挂,全是年轻妇女排长队。”牛大姐“一个动掌拍不响,我还听说男澡堂全改药水浴了。”于德利:“我觉得你们俩的想法都够俗的。干嘛得是个流氓?正人君子就不脚踩两只船了?要我写,就写一水儿的良好妇女一水儿的优青年,温柔善良,道貌岸然,有那么三五个花搭着爱到一筐里,那才难分难解,撕捋不开,把谁摘外边都是伤心事,还怕不是悲剧?”
牛大姐:“倒是倒是,狺情小说是这套路,好人们搅在一起你忍我让的倒是不如坏蛋来得干脆——这我太有感受了。”
刘书友:“让来让去,全耽误了。深刻。你就这么写吧,写出来准轰动,好人多嘛。”
于德利拍林一洲肩膀:“哎,老林,我给你出这高招儿得收费吧?”“几位老师,我是那么想的。”林一洲耐着性子给大家做解释。“就写俩人物,从头到尾,写足写透。我不想用什么第三者呀、门第差别呀、金钱诱惑呀。包括不治之症之类的所有属于外部原因造成两个人的关系破裂,纯粹是两人之间互相设置的造成隔阂,酿成悲剧。之所以我不写像你们几位老师刚才说的那些人纠葛,就是想和其它描写悲剧爱情的特别是名著区别开来——陈老师您说我这么想对吗?”
陈主编:“想法不能说不好。但下笔前全考虑周到了删繁就简地写和写我时候根本没想到,从作品上还是看得出来的。”于德利:“我觉得你这么写没劲。
两个人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肯定罗嗦,当然你对写得好,像人家那《两个人的车站》也行,你能吗?”刘书友:“人外国还有一个人演的电影呢。”
于德利:“还有没人的《狐狸的故事》,那得大手笔,你不是,咱中国人也不认这个。还是老老实实的吧,写点中国人民关心的事吧。大伙儿关心什么?就是桃花了眼了,瞅见什么都好,得了自己那份儿还嫌不够,甭用管媳妇也好,钱也好都想拿双份几。”“哎,东宝,你看过前一阵演的那外国片了吗?”戈玲忽然问李东宝。“没有,什么名字?”“哎,倍儿棒,什么名字我给忘了,是讲时间的。”
“我看过,是科学幻想吧?”刘书友说。
“不是,言情片!”戈玲说。“就前一阵咱这门口影院演过的。”“我知道你说前那部片子。”张名高说。“女主角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陈道明?”“没错,是不是特棒?东宝你应该看看那部片子。”
“还演吗?”“不演了。”戈玲对林一洲说。“我建议你也应该看看那部片子,刚才我听你说话一下想到那部片子,肯定特有启发。人家也是写爱情,也是写悲剧,也没有讲门第呀金钱呀疾病什么的。而是写时间,时间使爱人分离,永不相聚。绝吧?深刻吧?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以拆散一对真正相爱的男女,但在时间面前他们注定要失散。”
于德利一拍大腿:“唉哟戈玲,你这一说我浑身一机灵。”
张名高也扼腕叹道:“人家那故事编得,不服不行,极干脆地讲了个罗嗦的故事。”
“你听懂他们说的意思了吗?”刘书友问牛大姐。
“扯操!”牛大姐轻蔑地一晃头发。
“我也没听出什么有意思来。”刘书友问戈玲。“时间怎么会妨碍爱情?日久见人心。”
“你真是不开窍!”于德利拦住正要开口的戈玲。“你甭管,我来问他,时的尽头是什么?”
“喊!我不懂?”刘书友说。“时间的尽头还是时间,时间是没有尽头的。
”“可对一个人来说呢?”李东宝上身一冲,问道:“譬如说你。”“我?”“对呀,”戈玲接上来说。“时间对你是有尽太的,尽头是什么——死亡!”
于德利:“懂了吧,你逃得了一死吗?”
刘书友:“可我不怕死,民不畏死……”
众人一齐扭脸侧目:”没劲没劲,这么说就是耍赖了。”
刘书友:“本来嘛,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戈玲:“谁跟你讨论精神了?先弄清这儿说什么呢再搭话。”张名高慢条斯理地开口:“而且时间本身也是有尽头的。地球爆炸了,时间就消失了——你否认吗?”
目光灼灼盯着老刘。众人:“没词了没词了,这下问住了。”
牛大姐也笑。戈玲对林一洲说:“你要能写出这种类似的人那外国片的东西,那你就名垂千古了。”
“垂了千古又怎么样?千古之后呢?”刘书友说。
“你瞧,你这个人就抬杠,那么大岁数。”于德利批评刘书友。“怎么,你还想搞一言堂?”刘书友瞪眼。
李东宝问戈玲:“哎,你刚才说那片子你那儿有录相带吗?”“没有。”戈玲说。“不过我可以找人借。”
“我那儿倒有一盘,不过录得不太好。”张名高说。“回头我借你。”“好。”李东宝看着手表,站起来伸懒腰。“快开饭了。戈玲,中午借我点饭票。”“咳,”戈玲指指林一洲。“你别把人家作者晾这儿,中午请人家吃一顿吧。”“噢,李东宝再次发现林一洲,接着转着脖子四处找。“这老陈呢?怎么眨眼工夫就不见了,溜得倒快,话还说着半截儿。”李东宝对林一洲说:“怎么样,就谈到这儿吧?你回去就这么改,改完尽快送来——都清楚了吧?”
“嗯,嗯,”林一洲不太有把握地说。“给人物设计个来历,背景弄实在点儿。”“差不多是这意思。”李东宝颠着脚问。“你估计多长时间能改完?”林一洲说:“我白天得上班,只能晚上干,怎么也得十天,最多半个月。”反正你抓紧吧,饭多吃点觉少睡点。”
“我是不是要跟陈主编告个别?”林一洲问。
李东宝陪着林一洲进了主编室,老陈正在拿手纸擦着饭碗。“哟,还没走哪?都谈了吧?”陈主编一边擦着饭碗一边朝林一洲颌着点头。“谈完了,”林一洲说。“那我回去就按着这改了。”
“啊,不一定非按我们的改。”陈主编拿着擦得锃亮的饭碗绕桌走起来。“我们的意见都是提出来供你参考,不一定合适。你是作者嘛,还是要尊重你的意见,你觉得好的地方你就坚持。”“嗯,好。”林一洲连忙与老陈那只不拿碗的手相握。“感谢你百忙中那么仔细看了我的稿子,还提出了那么些宝贵意见——李编辑,也感激你。”
林一洲一手拉一个。“应该的。”老陈脱出手腕子说。“好好改,你还是很有才华。我很希望看到你通过我们刊物步人文坛。”
“还得请您……和您,老师们多指点。”林一洲暗忖:“作肉麻状没我想得那么艰难嘛。
“噢,有一点我刚才忘了。”陈主编叫住一路点头哈腰倒退着用屁肢顶开门欲溜走的林一洲。“你那个稿子中对话里有些调侃最好不要。没必要嘛印度洋神圣的东西还是让其神圣好啦,不要随随便便拿来开玩笑,有什么意思?就你聪明?并不显得深刻还徒然惹事。”
“好,好,我一定,统统删掉。”
李东宝陪伴林一洲下楼时,对林一洲说:
“我倒觉得你那里有些对话不应该删,写得挺好。你甭听老陈的,他这人胆小,就怕出事哪那么容易就出事了?我还告你,你要是把对话里那些骨头都剔了,你这小说就没法看了。我喜欢的还就是你那对话。还有,需要增加情节和人物你就尽管加,不要考虑篇幅,不怕长,只要加得好,多长我都给你发。其实我觉得你这小说发展好了能写成一个特不错的长篇。”李东宝说完哼着小曲儿扬长而去。
林一洲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刺眼。
林一洲默默地乘车,默默地步行,默默地掏钥匙开门进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又默默地躺了半天,然后默默地做饭,默默地和老婆一起吃掉,默默抽了几支烟喝了两杯水,开口骂了一句:“操他妈!”心情才好转过来。
他把那迭稿子从包里掏出来,坐下懒洋洋看着。
老婆在一边说:“干嘛非得改?不改不行吗?咱豁着一个月吃素油印了它。
”林一洲便说:“甭招我啊,我这儿正烦着呢,小心我跟你急。”“他们这就是欺负你老实,怎不叫别人改光叫你改?回头我找他们评理去。”“去去,少跟我这儿聒噪,你哪懂我们文人的规矩,净老娘们的是非。”林一洲赶走老婆这才重新看稿。昨天还不往昔兀自恋恋不舍,今日方知这种日子一刻也捱不得,于是加倍努力阅读,心倒惭惭定了下来。看着看着,不禁为自己的机智忍俊不禁,不禁为自己的细腻、洞察人微浠嘘不已,看完稿子已是一身大汗,拍桌喝道:“挺好的嘛!这帮瞎了眼的王八蛋!”
骂完仍旧按着王八蛋的旨意深入思索。
时凡林一洲这等人旷废时日端出来文字犹如乡下妇女缝的土布小褂,款式不说针脚却是密密匝匝,如今拆了改旗袍,光拆线颇费手脚。林一洲定睛看了半夜,在文中看出几处破绽,有了入手处,便忧郁地上床睡觉去了。
此后的几日,他像个缝穷婆似的东拼西凑。后来笔起顺了,自己变出无穷样,竟也写得兴致勃勃,不留神就涨出七、八万字,一发不可收拾了。
俟其终篇,回头一看,本属旁逸斜出的一枝意百花丛。独成蓬伞大树,余者皆在荫下。
初时还有几分慌张,细一打量,又觉别有洞天,更其深邃,更其秘不可测。
不免得意,不免诧讶:我还有这么一手?
掩卷长思:妈的要是没人管我,我还了不得了!
倒是狠下心来把原稿文字尽行删除,留待日后唾沫成珠进以佚文发表。狎思之余,不由小瞧了《人间指南》诸辈,暗自发恨:再来呀,难得倒我吗?毕竟东流去!
狎思之余,不由小瞧了《人民指南》诸辈,暗本发恨:再来呀,难得倒我吗?毕竟东流去!
李东宝这几日正为一条大尾巴生气。这是位素以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著称于世的老宇儿匠。这二年政通人和,他也撂荒了,终日长嗥其声如蚊,自是有几分寂寞。前日携着来京串门带割痔疮,宰到《人间指南》头上。老陈念其风华正茂时赏过《人间指南的》的脸,指派李东宝陪同接待。
想《人间指南》一个芥豆似的机构,在华盖云集的京里,哪有他们横冲直撞的份儿?腰里又不趁几两银子。住旅馆,上医院,买车票全得靠死皮赖脸。李东宝为使老字儿匠事儿顺,连平时自己舍不得用的路子都献了出来,承了偌大的人情,孰料老字儿匠临走还不满意。本来是客气,跟他约两篇小稿,他倒破尿盆——端起来了,昂着脸不理人,真是割了鸡巴敬神,神也得了,自己也疼死了。
林一洲去送稿那天,正赶上李东宝在编辑部开骂:
“以后这破事甭找我,有那工夫我养两条金鱼好不好?”
并没林一洲的千系,可他还是立时瘟头瘟脑,似乎骂了瓷缸子,他这捏瓦盆的也跟着问心有愧。
李东宝见了他,倒还客气了虽仍一脸盛气,话说得却也和缓。“啊,来了,稿子改完了?”
“完了完了。”林一洲拌出新誊清的手稿递上去,几分拘泥几分为媚。“按您说的改了,多了几万字。”
“放桌上吧。”李东宝不无腻歪地看了眼那一大厚摞稿子,问:“怎么样,改得感觉如何。?”
这倒叫林一洲不好回答了,本来兴冲冲想描绘些新改的得意之笔,看李编辑这副嘴脸,也浊倾心面谈的敢氛。讪讪地说:“您自个儿看吧,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我爱人看了新改的这遍,仍然哭了。”“好好,如实为我看,哭不哭可不一定。”李东宝接着对众人发牢骚:“我这烦老陈这点,什么文丐文妓都钉当爷敬着。有什么呀?没了谁的稿子还不一样办刊物?就说那张名高,他说把删掉的恢复了就一个字不拉地赶紧给人全补上了。我看就该删!”众人只是笑,似点头赞同,可并无一人应声附和。
林一洲坐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他,一支烟抽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