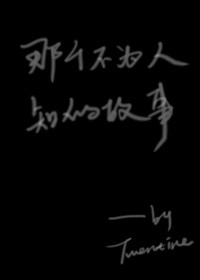7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王朔-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一洲坐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他,一支烟抽了半截便灰溜溜地走了,到粮店排队买切面去了。
那边李东宝生了一日气,晚上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班倒也若无其事,照旧有说有笑的,一边和戈玲等人说着闲话,一边看林一洲新改的稿子。因为对前一稿已全无印象,这稿看下来倒也不觉得突兀。看到三分之一处,牛大姐拿了一个邻居中学生的习作让李东宝看,支分紧急,明天人家就要听回音。于是就放下林一洲的稿子,看那十六岁少年的踏青心得。
少的文字难拙,感情鲜嫩,倒使李东宝看得轻松,生出几分语文老师的雅兴,提笔批改,念念有词,挑出常人不及处朗诵给大家听,众人都叹:
“真是不错,这岁数就有这等沟壑,劝劝他父母,将来千万别当工人农民。
”牛大姐也觉脸上有光:“这孩子我看着就像有出息的,闲来无事也没少点拨他。”后来李东宝把稿子还给牛大姐,说:“还是等他再长长吧,我说得不错也就是在中学当手抄本不错。”
牛大姐还要要力争。李东宝劝道:“太早出名对他也没好处,没准毁了他呢?哪次作文课让他把这东西交上去,肯定得优。”
牛大姐不得已求其次:“退也得你给写个意见,以示郑重处理过,我们是街坊不好说话——平时我净勉励他了。”
李东宝就去求戈玲:“麻烦你人写个意见,我这儿敬礼了。”戈玲也不傻:“又往我这儿推,我看都没看怎么写意见?”
李东宝便央求:“好写,所有初写者的毛病这儿上全有,还不好写吗?”倒是于德利听见大包大揽:“不好退给我,不是小孩写的吗?我有个朋友刚在云南办了个红领巾刊物,就想找个真小孩写的稿子突出儿童性、低幼性、不管好歹。
”
还是牛大姐,有眼光,对于德利说:“你别坑人家孩子了。”
一把夺回稿子,用左手写了几行言不由衷的褒贬话。
三混两混,日末过午,李东宝已经觉得一天的工作干完了,叼着烟去别的编辑室找相好的聊天去了。
林一洲逍遥了几日,自第五日起开始狐疑,心神不定,日益发甚。屈指计算,五、七万字的稿子一边打吨一边看,有三天也该完了,再转给陈老汉,速度降几十公里,一星期也看个大概了。就算写得深奥、曲折,几个笨蛋要再费几天猜谜,一个月怎么也该批出来了作莫非拿不准报上去了?如此一想倒把自己吓了一跳。想去探个虚实以又怕人家笑自己小样儿,几次拿起电话,拨到四、五个号便没了勇气。有次愣撑着拨通了,对方一张嘴,吓得逃也似的扔了电话就跑,看电话的老太太追了好几条街,最后在联防员的协助下,才把他擒住。心情郁闷,嘴上还强努着,跟老婆那儿不承认,往好处估计着。“没动静就是快了,没准已经发了,所以不关键,盯着点下期刊物。”老婆也是意在凑趣:“这篇彻底脱手了,下部长篇该动手了。”“动手动手。再接再励。”林一洲很认真的。“否则群众刚见识我掉脸又把我忘了。”
“长篇写谁呀?”老婆娇俏卖痴。
”还是写你。”林一洲庄严保证。
林一洲已经觉得自己被证明了是有毅力的人,再等下去,就成二百五了。终于提电话给《人间指南》打了一问询。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古然说不知道此事,这下可给林一洲气坏了,还是和和气气地百般提醒,软缠硬磨,让人家去查,点了李东宝和陈主编的名讳。那女同志去问了一遍,回首说那两个知情人都不在,让他过后再来电话或留下电话号码等他们打回去,说了些他们如何忙稿子如何国让他再耐心等等的便宜话,不等他讨情便挂了电话,倒好像是他求他们似的!彼时其它那些碰了壁的编辑部的客气回信一齐在林一洲脑海中涌现,都成了求贤若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证据。
林一洲一想索性撤了稿子,另登高枝,让《人间指南》后悔去,并想象了些如何在得意之后见到那些小人雍容大度的举措和轻轻射去的眼神儿,一路演习着,给谁都是白眼儿。
好在很快醒了过来,想想还是赌气不得。回忆了些关于大丈夫遇到此事应有风度,忍了,于晚风中体味了些悲凉和失恋的感觉。如同那些痴心女子,林一洲还未彻底绝望,气忿过后便想出万般情由为失约的心上人辨解,满腹怨恨化为一腔体贴,伊人病了?伊人出车祸了?你虽焦头烂额身遭磨难可知我这里也正为你苦苦煎熬愁肠百结?何不让我为你分担些许?难道我还跟你讨价不成?
正胡思乱想,自怨自艾,老婆一步跨进来,拎着一兜鲜灵灵的菠菜,笑盈盈地打问:
“构思哪?”如此邋遢老婆,焉能不让人火气上窜?
林一洲大喝:“少跟我开这种玩笑!”
老婆撅着嘴:“瞧神气的,这就见不得人了?”
“我告诉你齐宝琴。”林一洲指着老婆训斥。“你要注意了。我还没怎么样,你倒先抖起来了。是不是出去逮谁给谁都吹了牛?事情坏就都坏在你们这些女人身上——一个星期不要来见我!”其实林一洲打电话时,李东宝就坐在电话旁抽烟。。一听找他便连连朝戈玲摇手让她说人不在。于是戈玲便把听筒在桌上放了会儿又操起来如此这般应酬了一顿。
戈玲放下电话对李东宝学说了一番。
李东宝笑嘻嘻地说:“让他着急去吧,我何必苦巴巴地又给自己找个爷?这会儿孙子似的,事成之后就不是他了,一个例外的可有?叫我哪只眼睛瞧得上?”
话虽如此说。还是动身找林一洲的稿子,翻了一气倒茫然了:“搁哪儿了我给?”李东宝找了半日稿子,连柜底都翻了,问谁谁不知道,直到害怕了,刘书友也看完了那篇稿子,合上最后一页,对李东宝说:“在我这儿呢!”
既然稿子没丢,李东宝又不怕了。笔直地坐着,一眼一眼地看。外面突然刮风,飞沙走石,编辑部又不断有人进出,他也不大看得进去。后来稿子上的一行句子又让他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一个旧时的人,遥忆了半天那人少年时的音容笑貌,才集中注意力继续往下看,可下班时间到了。
老实说,李东宝这几日的确是有一空就看林一洲的稿子。偏林一洲忍了一个月,这时忍不住了,一天打八回电话找李编辑,拿贼似的,搞得李东宝很不高兴,一听电话铃响就精神紧张,本来挺喜欢上班的人现在一进办公室便盼着星期天快到。见生人便躲躲闪闪,提防着林一洲到编辑部堵他。
他对大家说:“你们都看到了,这是他逼着不让我看完他这稿子,不是我草菅他。”
大家也说:“就是,这人太讨厌了。”
李东宝赌气跳过中间五分之二,直接看了眼结尾,便去找陈主编,进门便坐下,拧着眉头说:
“不行呵老陈,这稿子我看了,第一稿好的东西都没了,加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不得了。”
老陈正在给什么人细声细语打电话,捂住话筒扭着个脸下巴堆起一层褶子皮,低声问:“什么稿子?”
“《风车》”李东宝说。“忘了?”
老陈没言声,李东宝也不多说,他相信老陈的记忆力。
“噢。”老陈只过了几十秒便想了起来,从没忘过似的问:z在怎么,改得不如以前了?”
“完全走样了。”李东宝摊开双手。“彻底不入流。我认为是完了,连修改的基础都没了,这种稿子只能退了。”
老陈轻声对话筒里说:“等会儿别挂。”双手捧着话筒仰脸呆了片刻,这回是真想起来了,低头说:
“这么糟糕?一稿基础不错嘛,怎么倒越改越差了?”
“要不您再看看,”李东宝把稿子递过来,“没准儿您觉得好呢。”“算了算了,我就不看了吧——没跟你说。”老陈摆着手对话筒里的人解释了一句。“既然你觉得那么差,不行就退了。”老陈转身对话筒说:“我晚饭得回家吃,饭后倒可以溜出来。”“那我可就直接退了。”李东宝站起来。
“慢!”老陈再次转过脸,“不要那么退,本来要用的搞子嘛印度洋退得讲究点。”“开点退稿费?”老陈又犹豫:“再商量,原来也没说一定要用他的。
”
“您要舍不得钱又讲究,那我只好让他再改一稿了。”
“那就再改一稿。”老陈下了决心。“争取他自己主动撤。”
林一洲奉召再来《人间指南》编辑部,一进门就看见每个编辑都在用朱笔删批稿子,一部部镐子勾满红墨水,血淋淋的,当场就有点误闯法场的感觉,双脚发软后脖直冒凉气。
撒腿就跑也不象话。李东宝皮笑肉不笑地迎上来,指着远远一把椅子:
“坐啊,你倒坐啊。天热吧?”
“热,热。”林一洲擦了擦额头的汗,斜着坐下,拿眼偷着去瞅旁人。
李东宝在他对面坐下,并不说话,只是抽着烟瞧着他。
林一洲笑笑,忽然爽朗了,全臀坐牢,也拿出烟抽,不开口。想法很有道理:你叫我来的,自然该你先张嘴。
李东宝想得也简单:就不先开口!
二人抽了多半支烟,还是林一洲先沉不住气:我是卖方,再充回小吧。“稿子看了?”“噢。”李东宝作魂儿归窍状,随之手端下巴半晌不语,仿佛那儿有撮山羊胡子。尔后抬头直视林一洲:
“看了。”“怎么样……看完后?”
“恐怕还得改。”李东宝很同情的样子。
林一洲嘴上的烟灰齐根儿掉下一截儿。
李东宝活跃起来:“坦率地说,你这稿我看完很不满意。你怎么把第一稿里好的东西全改掉了?你第一稿有些地方催我泪下,我看这稿特意借了手绢,没想到看了一半倒给我看乐了。”“你甭说,言情小说能出喜剧效果也不错。”戈玲在一边说。“问题不是逗乐的,嗯,诙谐了一把,是气乐的。”李东宝严肃地看林一洲。“怎么回事?你改的时候怎么想的我都不明白?”林一洲倒臊了,倒心虚了,喃喃的:“我是按你教的……”李东宝打断他:“我是让你增添点世俗的情趣,没让你庸俗啊。这世俗和庸俗可太不一样了,两回事,一个是死气息一个……是……你这思路不对,满拧!”
“我……”“我明白,你是想迎合我,一切都依我的喜好来。”李东宝转向戈玲。“这责任可能在我,说得太多,把他限制死了——
你别听我的呀!我不也跟你说了,你自己的好东西千万别丢,丢了就不是你了。”“我是……”林一洲忽然产生一个可怕的怀疑:这孙子看我新改那稿没有?谁听你了?我正是由着性儿写的。
没敢再往下想,作真的被说中了状。
戈玲趁火打劫,循循善诱:“每个作家都该有自己的风格,谁学谁也学不来,就像歌星根据自己嗓子选择唱法一样。”
数这丫头坏!没准上次就是她接的电话。林一洲狠毒地想,多暂晚卖窑子里去!刘书友拧过脸来问:“你是不是学张名高了?他的东西可就是庸俗。”“没有没有。”林一洲负气回答。“老实说我也就是在你们这儿才知道有他这么一号。”
刘书友:“肯定是学他,你别不好意思承认。”
“我知道他学谁。”牛大姐说,“我看了两行就看出来了——博尔赫斯。”林一洲:“怎么可能?我就看过他一个段子,第一句就看恶心了。”牛大姐:“别抵赖了,我搞了这么些年编辑工作我还不知道?你书桌上肯定搁着本人家的中文段子集锦,看一行写一行。你这句式我一眼就认出
来了。别看我没怎么读过他的书。”
林一洲:“我要学他我是孙子!”
戈玲:“那你学谁呀?”
于德利:“就是,总得学谁,否则怎么写?潜移默化也算。”
戈玲:“平时你最爱看谁的书?”
李东宝:“你最崇拜中外哪个作家包括不著名的?”
林一洲:“平时我就不看书——就怕让人说这个。”
众人笑:“没劲,没劲,不说实话。”
戈玲娇嗔道:“你就崇拜一个人怎么啦?”
牛大姐说得性起,离座端着茶缸子凑过来,李东宝要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她自己不肯,和戈玲挤坐在一起,说一句拉一下林一洲的袖子:“小伙子,你要吃写作这饭饭,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有哪几个人是不能学的。”“我真没打算要学谁包括能学的。”林一洲恨不能把心窝子掏给这位慈祥的大妈。“听听怎么啦?又没坏处,三人行必有你师。”戈玲捅他一下,又朝他眨眨眼。牛大姐全然不顾,似乎迟一步那点经验之谈就要烂在心里,掰着手指头数给数一洲:
“第一不能学老舍,你学得再像人家也当是又发现了老舍遗作没你什么事儿更甭说那学得不怎么地的了。第二不能学沈从文,五十年前吹洞箫那是优雅现而今含管箫那叫仿古。第三不能学鲁迅,为什么不能学我也甭说了……”
戈玲天真地翘着鼻子:“学施耐庵行吗?”
“当然。”牛大姐手指到天上。“蒲松龄,罗贯中这帮都能学。《聊斋》呀,《水浒》呀,《三国演义》什么的,都是民间传说,没什么章法,说谁写的都成。”
“还有一个能学的。”于德利说,“无名氏。”
林一洲退出正热闹的圈子,踅到走到一边翻看报纸的李东宝跟前,怯生生地扯扯他后襟:
“李编辑,您给我句实话,我这稿子还可改吗?”
李东宝放下报纸也叹气:“没瞧我正为你发愁呢?改是没有不能改的,但照目前这路子改,肯定没戏。”
一直呆在一边没说话的刘书友忽然扭头说:“说他那稿子呢?那稿子我看过,不是挺好吗?我一气儿就读完了。”
“那您处理这稿子吧,没准是我看太国遍陷进去了。”李东宝忙把林一洲推到刘书友跟前。“这是我们这儿最老最经验的编辑,看稿子从没打过眼。”
“坐下吧,坐下谈。”刘书友倚老卖老地说。“稿子我看了基础不错,但光我觉得不错还不行,还得读者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