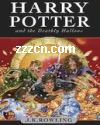夏之波-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样的地方漫步,你内心的感受当如何呢?
感到满意。好像被按摩。好像被爱犬舐遍了全身。好像笑得更加高雅。好像被花瓣洒
下,被花瓣埋葬起。
感到消受不了,承受不了。感到自己的肠胃太无能。感到肿胀、停食、漾酸水。好像一
艘船因为超载而正在沉没。
感到愤怒。感到侮辱。像一个乞丐。像一个被逮捕押解的囚徒。感到羞愧。像不肖子卖
掉了传家宝。
而最根本的,只是孤独。越热闹越红火就越孤独。人与环境、人与土地、人与族姓的关
系竟是这样脆弱的吗?
下起了小雨。为了躲雨,他们紧靠着店铺的橱窗和门户。而使城市变得安静幽雅。汽车
也开得小心翼翼。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商场。假发、首饰、大大小小的皮箱、化妆品。又穿
过一个空荡的、堆放着许多塑料垃圾袋的小街,小街发出一种陌生的刺鼻气味而且街面发
黑。然后他们走进一间白房子。白桌子白凳子白圆椅。落地镜面里也是一片洁白。然后他们
要了咖啡。土耳其式还是意大利式的?侍应生问。加不加一种兑咖啡的酒,南非出品?联合
国正在对坚持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贸易制裁。
他凝视着窗外的树影,车流,人行。匆匆而又心事重重。“从前有两个最淘气的孩子,
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就用这两个孩子命名了一个著名的餐馆……”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姑妈老是说我,管我,还打过我。
她养着一只金毛狗,有一天我把狗鼻子涂成红色……”
他变得闷闷不乐。“咱们走吧,我累了。”他说。
过去是我领导,现在是我承包,而且说是,承包三年。说是一切权力下放到我这里了。
我可以“生杀予夺”。
第一个问题,我聘用谁,不聘用谁。
我最不想聘用的是老赵。他喜欢串宅门,送礼请客,叫作“关系学”、“名单学”、
“致敬学”。对任何实际事不出主意、不出头办,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又事事计效,事
事争先,事事作梗。在我们讨论要不要给每一个科室发一听速溶咖啡的时候,他撇着嘴说:
“也不能说喝咖啡就是对外开放,不喝咖啡就是保守僵化。”当我们为了尊重他的意见拟议
不发咖啡的时候,他又说:“也不能说不喝咖啡就维护民族传统,喝了咖啡就崇洋媚欧。”
当我们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见的时候,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见,“一切听大家的。”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他就会造成震动。不聘他就会使有关领导有关人士都同情他。就会
落一个排斥异己,不顾大局的恶名。就会得罪一串人。就会使一直在那儿“反”老赵反得起
劲的小张他们得到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忘形起来放肆起来越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起
来。又会使老董他们得到一种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纷纷地去请求调动去请假休养
去住医院,然后群起上书对我进行弹劾,而我是最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的。
我其次不想聘用的是老董。她“文化革命”中补来了三代贫农家庭出身、本人从7岁做
童工的证明。去年又突然补来了50年代已经在夜大学本科毕业、具有高等教育毕业学历资
格的证明。她要求评次高级职称,为这个又哭又闹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喝了敌敌畏。最后连
小张也服气了,说:“评吧评吧,捏着鼻子也承认她是副研究员吧……我只提一条建议,咱
们单位需要给老董规定一条特殊的劳动纪律:上一天班扣工资一元,旷工一天奖励一角,旷
工一年就算全勤一年,年终戴红花发全勤奖。”
说得过分了一点。他她上班只能带来麻烦,是事实。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她就会闹你个人仰马翻。而且她的舅舅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一个可
敬的人,一个大人物。这位可敬的人物小时候讨了农村老婆,比他大五岁,小脚、文盲。而
他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对这样的人物的外甥女是不能怠慢的。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在公
众中通不过。
想聘的,未必是可以聘的。不想聘的,却是一定不能不聘的。所谓生杀予夺的全权,只
能使我更加为难,更加狼狈。因为,不再有一个无形的“上级”代替我负得罪人的责。不要
把事情做绝了啊!人人都这样说,包括我自己也在提醒自己。
接到老友A、K患癌症去世的电报。猝不及想。就像一架正平稳飞翔的飞机,没有任何
预兆便突然爆炸坠毁了。
在挨斗的那几年,他却那么活泼。做打油诗。唱《临行喝妈一碗酒》。跳“忠”字舞。
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同车间的老木
匠师傅叹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收过一个这样灵的徒弟。完全是八级工的材料呀,去当那
个熊干部,多可惜了儿的!”
一架飞机飞着飞着,没有任何原因,就会突然爆炸吗?
这是一架巨大的秋千。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这是一艘风浪里的帆船,帆船随
着圆号声翻滚腾跌。这是一张破了孔的降落伞,我欲乘风归去,飞将军自青天落。
完全错了。他本来不该问:“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后来他才得知,依据这里的风俗,
晚间的这种提议有一种过分亲昵的含义。
城市在旋转。灯光如线如缠。地面倾斜了,直立了。罩到了头上去了。人影绰绰,笑语
滔滔。错落的喊叫声充满青春的欢乐。无烟的晕眩。无花的芬芳。无原由的心悸。就像坐
“碰碰车”、“碰碰船”,互不相识、互相提防互相躲闪而又终于互相碰撞。躲避的是碰
撞。期待的也是碰撞。人为什么愿意和陌生者碰碰撞撞呢?
而她太寂寞了。寂寞如花坛的枯草。寂寞如雪地的灰雀,寂寞得过早地出现了一根又一
根白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而她是无助的。像一架下坠的飞机。像一艘下沉的船。像一幢洁白的房子。墙上是洁白
的浮雕。连壁炉也是洁白的。为什么夏天也需要投几片木柴呢?这里有夜的海风,凄凉。需
要听木片的剥剥声。需要看火焰的升腾。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了这点声音和这点运动。
而城市是一片喧嚣一片豪华一片欢腾。莫非她和他都是乞丐?在呛人的发臭的烟气中,
不可想象的超分贝的滚石乐震动耳膜、震动心室、震得胃痉挛,而且震得牙疼,震得牙齿一
个又一个松动,再震一会连舌头也会脱落下来。
一片喧嚣中他疲倦得睁不开眼。如睡如痴中他被击打被揉搓被碰撞。
如果三十年前,他也许会翩翩起舞。他愿意回答这寂寞这热情这喧嚣这陌生,他会拥抱
这陌生。
不。飞机是不应该在空中爆炸的。
我远非一无所为。
“悲观的论点,停滞的论点和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说。
曾几何时,人们已经不能流利地背诵红宝书上的语录了。报纸上愈来愈少看到他的教导的被
引用。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安息。
我增设了一个搞生产、搞有偿服务、搞第三产业的“中心”。让四分之一强的人员转而
从事这项有风险有麻烦但也不无油水的事业。也就是说,事实上、我裁减了四分之一强的人
员。即使人人心中有数我也必须多次郑重声明:不是裁减,不是裁减,不是裁减……直到说
破了嘴,听厚了耳膜。否则,就会不堪承受。
年轻的父母给年幼的孩子吃药的时候有时候解释说:“那不是药。是糖。是果汁。”而
年幼的孩子会哭诉:“是药。”
我们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么好的人民!
大喊大叫了许多天。最后,有两个人没有被聘用。一个是小刘,他已经打了三次请调报
告,他正在忙着筹备婚事,他埋怨在我们这里既提拔不成官又难以成名成家而且还捞不上
钱,“我干脆去做生意!我有路子!我们可以去倒腾彩色电视接收机,一台赚一千!”他
说。小张说,中国的未来看小刘。
一个是老张,她病休已经三年。再有半年,也就达到了退休年龄。为了使她接受不被聘
用,我们先提升她为副处长,再宣布暂不聘用,却仍然保留处级干部待遇。
炎热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改革月”、“改革季”就这样过去了。人们陆续从北戴
河、从青岛、从大连和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太阳岛回来。人们称赞我的魄力,称赞我迈出了一
个大的步子。部属们点点,说:“你办事还差不离。”老赵在有些会上批评我改得太慢,在
另一些会上指出我改得太急。还批评玻璃窗擦得不干净,汽车司机不应该用公款做服装并且
指出汽车司机的服装必须改善,这不仅是一个服装问题。老董找我谈,既然老张可以做副处
长,为什么她不可以做副局长呢?她明确指出,在她离休以前(还有一年),必须明确她的
副局级待遇。
几个平行单位除一个地方按既定计划做了些人事变动外都由原来的领导人承包,都聘用
了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宣布了任期与聘用期,都讲了一些提高效率效能破除大锅饭铁饭碗的
弊病的话。
然后一切照旧。
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调门儿不同的文章。说是铁饭碗是长期斗争的果实,不能笼统否定。
说是提倡穿西服是消费过热。
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永垂不朽。
蝉鸣也放慢了节奏,没有那么多切分音,咝——无比地悠长,若有若无,半疑半信。
我感到你的亲切,你的温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忍看你的含泪的眼睛。如不忍看璀璨的华灯下的一个踽踽独行的老人。如看一个拉
提琴的病人,他不停地、千次万次重复地拉着一个悲哀的曲子,欲罢不能。
拒绝她伸出的手,是太残酷了。像杀人。
本来不应该建议您喝一杯金黄的橙汁。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喝不上这样一杯橙
汁呢?有许多笑话,有儿时的回忆。就像你燃放的第一枚爆竹,你紧张得全身发抖,好像长
大了,去炸碉堡。然而,你期待着,发着冷,发着热。爆竹没有响。
机会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
也许,世界可以重新开始?昆仑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飞到大海,北冰洋可以按照我们
的意志欢迎游艇,树上将会结出红宝石而所有的绵羊都会露出凶猛的、却是无尚尊严的牙
齿?也许,就在他和她拥抱的一刹那,天堂的钟声将会敲响,巨大的海龟将驮着天启圣图爬
到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而所有的绳索,所有的戒律,所有的关于恒星、行星和卫星的规则都
将解体,一轮红日将会把他们烧尽而她的眼眶里的泪水也将蒸发散失?
不。
只剩下了一个字词。一个英雄与懦夫都喜欢的字。
还是让我们平平淡淡地度过我们的一生吧。
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其实你不知道是已经过了五个月,是已经过了五年。
忽然连续收到了讣告,得知一个又一个老友凋谢的消息。还有一个由于大脑软化变成了
植物人,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康复的希望,也没有人愿意他早日平安归去。至少是为了:待
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却不可能获得生者的待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在我们这个越
发古老和越发孩子气的国家,都会很快被淡忘。
没有遗忘的帮助,炎黄子孙怎么可能绵延至今日!
我去理发店理发,排队,等待,锻炼意志与性格。问理发员:“你们不是租赁承包了
吗?”
“是的是的,都包了。唉,只是个形式。”
“形式?国营理发店包给个人是形式?”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你们不是计件工资制吗?理发不是最容易搞计件吗?而且,现在理发价目不是翻了一
番还多吗?”
“计什么件?老师傅怎么办?哪个承包的人敢得罪老师傅?您承包三年,三年以后还活
不活?什么多劳多得?多劳多得罪!干得少的挣得更多!”
他的牢骚太多了。我将信将疑。
而在我“承包”的这个单位,攻击也开始了。带头攻击我的恰恰是小张。
“什么改革什么改革!改革了这么些日子了,也没给我们涨工资!也没给我们发皮大
衣!瞧人家××部,一人发了一架钢琴!”
于是我懂了,改革就是涨工资。改革就是发皮鞋发铜火锅发电冰箱发钢琴。改革就是给
每个男人发两个媳妇、给每个女人发四个情夫。改革就是冬天不刮冷风、夏天吃冰棍不收
钱。改革就是每个人去美利坚合众国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公费旅游,而儿孙
们去那里自费留学。改革就是每个人张开大嘴,然后源源不绝地输送灌溉啤酒茅台酒人参蜂
王浆果汁牛尾汤。改革就是给每人发一柄中子枪,目标:咽喉,距离:75厘米,预备——
放!
而小张他们,在一些时日以前,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地盯着催问着我:“怎么还不改
革呀!”
“您们要点什么喝的?”
侍应生彬彬有礼。穿着黑上衣、烟色裤子,打着标准如爵士的黑领结。
钢琴声在大厅里回旋。洒落如夏日的雨点,来自一朵黑色的、犹豫不决的云。
你也是彬彬有礼的,好像是经过了精心排练。苏打水和杜松子酒和插着牙签的柠檬,竖
在他和她中间,像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据说是保障了两个方面的安全。
“我们缺少的,只剩下悬挂在头上的氢弹。”
而她是无望的。她是不解的。你知道她在问:为什么?
她甚至迟疑地说:“让我们捅破那面墙。”
先捅破他的心吧。如果没有墙和炸弹。如果当真如东方歌舞团众歌星在激光束挥舞中演
唱的《让世界充满爱》那样,世界真的充满了爱,这将是第几次洪水泛滥的年代?
世界充满了爱。你有救生圈吗?
我倡导的搞生产搞有偿服务的“中心”办起来了,发挥了潜力,增加了工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