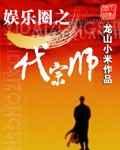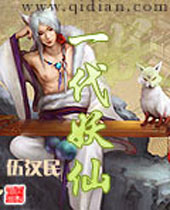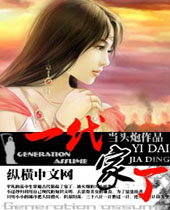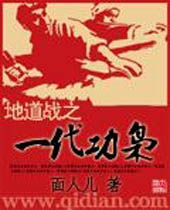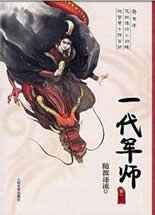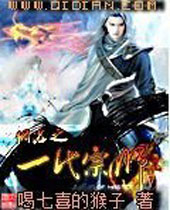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做共产党员,他仍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他又说,他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茅盾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两人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谈了很久。
秋白走后,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总以为他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哪里想到他会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还辗转反侧,难以安睡。他对孔德止说:“明天,我再去和鲁迅先生谈谈,一定要设法营救瞿秋白!”
这以后的几天,茅盾经常去见鲁迅,也去慰问了杨之华。他知道党组织和鲁迅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在鲁迅打算筹资开的铺子尚无头绪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牺牲后,茅盾去找杨之华、鲁迅;商谈出版瞿秋白遗作的事情。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不过瞿秋白的遗作究竟怎样编印,我还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来印。”
茅盾赞同鲁迅的意见。又过了几天,他和鲁迅、郑振铎又详细商量了筹款印刷秋白遗作的各项问题。他捐款一百元。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印刷精美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终于在1936年10月初出版了。出版单位署名为“诸夏怀霜社”,寓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最初议定编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个人,我仅仅是个‘促进派’,振铎由于《译文》停刊事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而主动避开了,只有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这两卷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疴不起的一年!”
二六、和史沫特莱的友谊
茅盾用“方保宗”的化名,在静安寺东面一条街道里租到了一幢房子。
新搬家后的一天上午,他正准备拿出纸、笔写作,忽听有人叩门。原来是徐志摩,他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一个外国女记者来看他。
“这位女士是A·史沫特莱,”徐志摩向茅盾介绍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驻北平记者。她要我介绍认识你,并且希望你送给她一本你的大作《蚀》。”
“茅盾先生,认识你我很荣幸。”史沫特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茅盾热情地说,转身去取出一本《蚀》,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史沫特莱,“请你指教。”
史沫特莱翻开《蚀》,瞧着扉页上茅盾的照片,笑着说:“Like a young lady(象一个年青的小姐)。”
这是茅盾和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时间为1930年夏季。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友谊也愈益深厚。茅盾还了解到,史沫特莱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也是这位女士创办的。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茅盾和鲁迅以后,就介绍他们给这两家刊物写稿。
史沫特莱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是精通英语和德语,而茅盾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语,一个懂德语。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交谈。茅盾的英语则说得流利。
这样,当史沫特莱有事需要和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往往是三人聚合地一起,由茅盾充作翻译。
起先,他们三人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以后就经常合作,为西欧、美国的一些杂志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史沫特莱后来写道:“茅盾和我常常在某个角落会晤,然后,仔细的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入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附近的菜馆中点菜来一同进餐,一谈便是好几个钟头。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都认为:能把帮助并且支持给与那些为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和牺牲的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1935年12月的一天,茅盾看到夫人起早买回一大篮子鸡、鱼、肉、蛋和蔬菜,就对她说:
“今天史沫特莱要来,又要你忙了。”
“忙倒没啥,只有你的洋朋友不再说你瘦多了,也高兴吃,我就开心了。”妻子说着走进了厨房。
这使茅盾想起今年初夏,史沫特莱拜访他时两人交谈时的情景:
“啊,茅先生,你比过去要瘦,这不好。我看你的营养不良,要注意增加营养呵!”
“瘦一点没关系,我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只是眼睛近视,没有办法复原。”
“你平时锻炼身体吗?”
“没有时间呀。再说,我也不能太公开露面,要引起麻烦的。”
“对,对。不过,我看你们中国的革命作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身体锻炼,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你的见解很对。可是……”
“哦,我知道,”她打断茅盾的话,“在你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改变革命作家的生活状况,还不具备条件。”
接着,她又一次问茅盾:“茅,你的《蚀》和《子夜》是很好的作品,是否已经有人把它们翻译成英文?”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法告诉你。”茅盾说:“我想,目前是不会有人翻译它们的。因为,翻译长篇小说,要作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在我们国内,敢于涉足的人是极少的;在国外,翻译家又对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现状十分隔膜。”
“不,你的小说应该介绍欧洲、美国、德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我来找人把你的《子夜》译成英文!”史沫特莱热情地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茅盾说。
“你放心,我一定要去做的。”她很坚决地表示。
这天当史沫特莱一走进茅盾的家,就笑着告诉他:“哈罗,茅,已经有人把《子夜》译成英文了!”
“真的?那太好了。”茅盾喜悦地说。
“我已经读过了译文。现在,我要请你为这个英译本写一篇自传,并且作一篇自序。”
她坐下后向茅盾提出。
茅盾想了想,答道:“小传我可以写一篇,并且打算用第三者的口气写。因为,外国的读者更欣赏客观的介绍,而不喜欢作者自己去说三道四。”
“噢,是这样,是这样。”史沫特莱听了连连点头。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建议序由你来写。”
“我可以写序,”她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又说,“不过,我需要一些材料──一份中国读者对作者评价的综合材料,你能不能提供?”
茅盾为难地摊开了双手,说:
“这个我也不好办,对我的评论有各式各样,即使是战友,对我尚且褒贬不一,由我来归纳这些意见就太难了。”
史沫特莱从椅中站起身,在室内慢慢走了一圈,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对茅盾说:
“有了,我请鲁迅先生写!”
茅盾听了一愣,想了一想说:“这当然好,史是大先生从来不写这类文章,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除非你亲自向他提出来。”
“当然,我要亲自向他请求,我这就来写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史沫特莱爽快地说。
茅盾心想,料不到她会这么直爽,怎么办呢?现在我又不便再推托,毕竟她是为了给《子夜》的英译本写序呀。
史沫特莱摊开信纸就给鲁迅写信,她说明了原委,希望鲁迅能帮助她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一,作者的地位;二,作者的作风和形式;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的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作者的态度。
吃饭时间到了。看到茅盾夫人摆到桌上的丰盛菜肴,史沫特莱高兴地拍着手说道:
“太美了!这么多菜,你夫人待你真好!”
“史沫特莱,我夫人是专门做来招待你的。请你多吃一些!”茅盾笑着邀她加入席。
过了两天,茅盾把史沫特莱的信面交鲁迅,并向鲁迅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鲁迅让茅盾把信翻译给他听,一面在纸上记下了史沫特莱的要求。然后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史沫特莱的信,微笑着说:“让我来考虑考虑。你也知道,我平时是不注意这方面材料的。”
茅盾回家之后,就动手写自传。原稿纸上现出了一行行清秀的字迹:
“茅盾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1896年7月生的。浙江人。他的祖先,本为农民;太平开国起义的时候,始在乡镇上为小商人;‘太平天国’的战争蔓延到江、浙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带着家小避难到了上海,不久又到了汉口,就在汉口经商。后来又捐了官,到广东、广西去做了几年官,从此就变做半官半商的家庭。从他的祖父以来,就是‘读书人’了。……”
在《自传》写了一半的时候,鲁迅来信告诉他,史沫特莱要的材料,他已托胡风代笔了。
于是茅盾继续埋头写《自传》。对《蚀》的创作是这样写的:“……从‘三部曲’看来,那时茅盾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显然失去了正确的理解;他感到悲观,他消极了。同时他的病也一天一天重起来,他常常连连几夜不能睡眠……“对于《子夜》,他写道:“《子夜》是茅盾所写的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他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