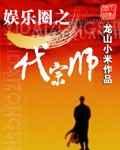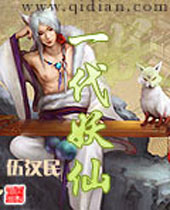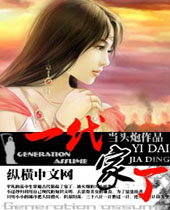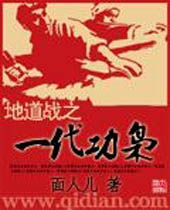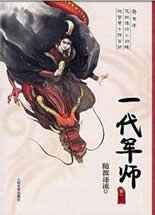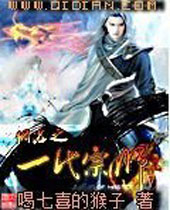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发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京,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做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
四八、清明前后
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党像慈母般地关怀着我,而我却是工作得太少、太少了。
下旬,茅盾签名的《文艺界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
3月初,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迫害民主人士,强化独裁统治。
接着,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黄金自每两二万元提价至三万五千元。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乘机抢购以获暴利。案发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是那些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大户,草草退款了事;却把几个挪用存款合伙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抓了起来,作为替罪羊。
这件黄金提价舞弊案发生在“清明”前不久。
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他向妻子要了把剪刀,把这天报纸上的新闻剪了下来,又一篇一篇地看着,想着:“这是个好材料,要以写!”他想到有些朋友曾向他建议:“你使枪使了这么多年,何不换把刀来试试呢?”
于是他决定写剧本。
茅盾认认真真地写起大纲来。抗战以来,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两万七千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
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吴祖光还把他的大纲拿回家,让他的弟弟吴祖强帮茅盾誊抄清楚。茅盾怀疑自己的剧本是否适合演出。曹禺鼓励他:
“西洋戏剧史上不乏不适宜演出的好剧本,譬如萧伯纳的有些剧本就是。茅公,您写小说是大手笔,写剧本也会成功的!”
过了两个星期,话剧《清明前后》开始由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连载。当茅盾刚把第二幕写完,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使他异常兴奋。但是他并未停笔。他知道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经济界将有大变,他的题材会显得有点过时,而且自己的编剧能力不行,然而他又转念:公然卖国殃民的事还在大量产生,我又何不在这乌烟瘴气中喊几声?
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清明前后》。
茅盾这次创作,是在“使枪使了许多年”之后第一次学着“使一回刀”。剧本以国民党的“黄金案”丑闻为背景,写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觉醒的过程,以及小职员李维勤购买黄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
如此一本话剧,谁来演出呢?没有一个导演敢接受。他们一怕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二怕万一演砸了,不好向茅盾这位大作家交代。
“莫非我这第一个剧本真的要步萧伯纳的后尘?”茅盾的确很忧虑。
“茅公,您的《清明前后》交给我们演吧!”4月初,赵丹登门拜访,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从新疆监狱中逃出的难友,刚刚组成了中国艺术剧社,决定第一个戏就上演您的《清明前后》,并且由我担任导演。”
“啊,那可太好了!”茅盾深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该剧社初创,万一演出失败,将会影响剧社的前途和几个十个人的生活,就劝赵丹说,“这件事对你们非同小可,你可要慎重呀!”
“我们考虑过了,愿意冒这个风险,相信这个戏会取得成功。沈先生的脚本我已读了三遍,从内容讲,这剧本具有尖锐的、丰富的现实意义,正是当前最需要的。只是从演出的角度看,怎样使它能够更加……”
看到赵丹欲言又止,茅盾笑道:“请只管大胆说,是不是有些地方不合话剧的规律?”
“不是这个意思,”赵丹接着说,“我是说如何加强戏剧效果,怎样更能出戏,说干脆点,沈先生能不能允许我这个导演对脚本作一些技术性的变动,譬如把太长的对话改得短些,把某些情节改得更富于戏剧性些?……”
“可以,完全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加强演出的效果,你尽管全权处理。”
“沈先生这样信赖我,使我信心倍增。等我把脚本改好,就送来请您过目。”赵丹说。
“不必了,”茅盾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排练,争取早日公演,要趁现在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机会,把戏推出去。我想,老蒋囿于目前国共谈判的形势,大概不好意思下令禁演。你既看过脚本,总有一个修改的想法,你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大的改动有吗?”
赵丹说:“大的改动只有一处,就是把全剧的演潮移到最后一幕,现在的高潮在第四幕,第五幕又低落下来了,所以想把四、五两幕颠倒一下,或者把两幕合并为一幕。另外一点比较大的改动是金澹庵,他是官僚资本的化身,我打算一直不让他出场,却又随处使观众感到有他在幕后,直到最后一幕全剧达到高潮时,才让他出场亮相。您看行不行?”
茅盾感到赵丹所提两点大的改动,都很有理,便欣然同意了。
9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则广告:“中国艺术剧社不日公演茅盾第一部剧作《清明前后》,导演赵丹,舞台监督朱今明,演员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
这天晚上,茅盾偕夫人进城看了彩排,发现赵丹扮演了那个只露一面的金澹庵。
9月26日,《清明前后》正式公演了。第一天的上座率只有六、七成。茅盾心里很担心,怕演出成了兔子尾巴。第四天,他不放心,戴了一副墨镜,悄悄去察看售票情况。他大吃一惊:嚯,售票处排起了双行长队!
后来他听说,从第二天起,上座率就逐日增加了。由于场场爆满,星期日还要加演一场。
演出气氛热烈,剧场内掌声不绝。记者在报导中称之为“罕见的现象”,“盛况空前”。
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当时《清明前后》已连续演到第三个星期,12日茅盾就听到消息:当局要停演《清明前后》。他想,赵丹他们的剧团已打响了第一炮,我的剧本也走到了大众中间,停就停吧。
然而停演并未成为事实,不仅如此,国民党的中央电台还在10月16日设立了一个特别节目,介绍《清明前后》。但他们的“介绍”却是:这个话剧内容有毒素,观看过此剧的人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切切不要去看。
岂料他们这么一广播,反而帮茅盾和赵丹的中国艺术剧社做了义务广告,观众更加踊跃。
不少工厂的老板看了《清明前后》的演出,大为感动,居然慷慨解囊,包场招待他们的职员、工人看白戏。
有一天,茅盾收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厂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允许该厂排演《清明前后》。茅盾在信中表示,欢迎他们排演《清明前后》,他将不收取演出税。这个工厂公演了好几场。他们给茅盾寄来了铅印的说明书。
10月8日,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六人,特地设宴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