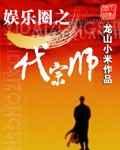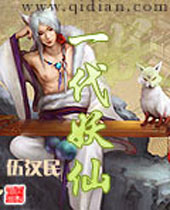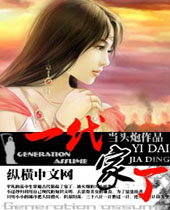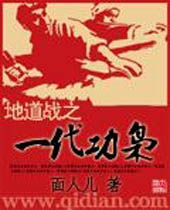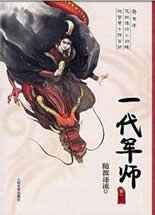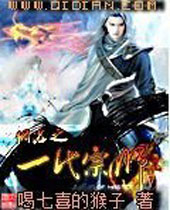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
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教你们作诗、填词。但是,学人选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我要先教你们作对子。什么是对子?
你们知道?……”
对子,德鸿当然知道,这就是对联嘛。虽然他还不会作对联,却接触过不少对联。他的祖父沈砚耕擅长书法,常用楷书为乌镇的商店、人家书写对联。他常站在一旁观看。他舅父陈粟香也是一个喜欢作对联的人。前年暑假,他跟母亲到外婆家“歇夏”,曾听陈粟香舅父和母亲谈话。舅父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家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可是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北栅头多有是小偷、私贩、盐枭,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
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德鸿母亲问:“那下联呢?”“下联是:
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何如?”德鸿母亲笑道:“你这是实话。对联作得好,白地对苍天尤其妙。”至于母亲写在父亲遗像两旁的那副对联,他更是历历在目。
德鸿竖起耳朵聆听张献之讲解对联的特点和写作方法:撰写对联,看来虽似小道,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问见识和文字功夫,例如区分平仄,要懂音韵;别词类和句子结构,要懂文法;遣辞造句,须善修辞;用典使事,须熟文史……这使得他懂得作对子是诗词的真功夫,不是什么雕虫小技。
张献之在课堂当场示范,详细地讲解平仄如何直协调,词类怎样选择,哪里是描写,何处是议论。并且,常常写了上联,叫学生们做下联。做后由他当场批改。
又有一天,德鸿听张献之为他们讲长联的写作:“说到长联,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
这是德鸿不知道的。于是专注地盯着黑板,只见张先生一字一句地把全联默写了出来。
他数了一下,两联共有一百八十字。
张献之要每个学生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
沈德鸿过去写史论、时论和游记都颇好,却从未作过对联。然而作对联的兴头被张先生鼓得高高的,便就年前游西湖所见的风光景色,模仿黑板上的大观楼长联写了起来。他先写了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心想不好,这是前人的诗句,应自出心裁地写。又写道:“万顷湖平似玉境静无尘照葛岭苏堤凭栏看云影波光照我全身入画”,可是下联如何对呢?他怎么凑也凑不好,不是平仄失调,就是词语失对,甚至结构不相应。这一来,他才知道“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一人到西湖游玩。这时的西湖已是桃花飞红,翠柳飘絮,晴光拂眼,游人如织。他却无心赏看,而是徜徉在一处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之间。他来到一副对联前,只见上写:“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他品味着,觉得昨天上课时张先生的分析确是入木三分:“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此乃这副对联的弱点。”
走过西泠桥,便是苏小小墓。沈德鸿知道,苏小小是南齐时的一个侠妓。在她的坟墓的小石亭上,刻满了各种对联。于是在本子上抄录着。忽然听到一个人唤他的名字,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胡哲谋。
“张先生讲的哪副对联在哪里,你找到了吗?”胡哲谋问。
“呶,在这里,你看。”德鸿指给他看。
这副对联是:“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张献之对这一对联极为称许,他在课堂上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德鸿看看眼前石柱上这副未曾署名的对联,更感到张先生分析得透辟。胡哲谋对他说:“张先生指出的此联,的确是这些称赞苏小小联语中的佳作。”
他俩又结伴同去岳王庙、灵隐寺,抄录了许多楹联。待到日暮时离开湖滨返校,他的小本子已记得满满的。
沈德鸿后来写道:“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1913年夏天,沈德鸿成为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第八届毕业生之一,以三年半时间修完五年的中学课程,提前毕业了。
对于西湖风光,他一直未能制作一副长联,直到1979年8月才为《西湖揽胜》画册填了一首《沁园春》:
西子湖边,
保叔塔尖,
暮霭迷蒙。
看雷峰夕照,
斜晖去尽;
三潭印月,
夜色方浓。
出海朝霞,
苏堤春晓,
叠嶂层次染渐红。
群芳圃,
又紫藤引蝶,
玫瑰招峰。
人间万事匆匆,
邪与正往来如转蓬。
喜青山有幸,
长埋忠骨;
白铁无辜,
仍铸奸凶。
一代女雄,
成仁就义,
谈笑从容气贯虹。
千秋业,党英明领导,
赢得大同。
七、北大深造
“德鸿,你来看!”陈爱珠指着《申报》上的一条广告对儿子说。
那是《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的学校有北京大学预科、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其中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史地、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和图书。
德鸿看完这则招生广告,听母亲说,外婆给她的一千两银子,自他父亲逝世后存在乌镇的钱庄里,到现在连本带息已有七千元。他和弟弟两人平均分,各得一半,每人三千五百元。这样,她还可以供德鸿再读三年大学。北京大学预科的毕业年限正好三年,所以她想让德鸿报考这所大学。又对儿子说:“你卢叔在北京的财政部供职,你到北大预科求学,可以得到他的照顾。再说,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早两年,他们的毕业生都钦赐翰林呢。进这所大学,准能得到深造!德鸿,你考这所学校,行不?”
“妈,你想得周到,我就考北京大学预科吧。”德鸿答道。
7月下旬,他来到上海,借住在二叔祖家里。然后到设在江苏教育总会内的报名处去报名。
这时,他才知道北大预科第一类是文、法、商三科,第二类是理、工、农三科。虽然考试科目相同,但是愿入大学预科第一类者得于理论、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他想,自己数学不行,不是学理工科的料,还是读文科为好,于是选报了第一类。
8月11日,沈德鸿一大早来到虹口唐山路的澄衷学校,按时进入试场应考。除了数学,其它几门课他都考得很顺利,尤其是国文和英文。
返回乌镇,他将自己选报第一类和考试的情况禀告了母亲。他后来写道:“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了。但她也默认了,大概她那时也觉得学工业未必有饭吃……,还有一层,父亲的遗嘱上预言十年之内中国大乱,后将为列强瓜分,所以不学‘西艺’,恐无以糊口;可是父亲死后不到十年,中国就起了革命,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亲也就不很拘拘于那张遗嘱了。”
陈爱珠这位知书识礼、通情达理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的,她听了儿子的禀告,只说了一句:“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出了北大预科录取的新生名单。然而他和母亲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沈德鸣”。他母亲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想必弄错了。不久,录取通知终于寄来,他被录取了。
9月初,德鸿从上海搭乘海轮北上。抵天津后,再坐火车到北京崇文门车站。他的表叔卢学溥派了儿子卢桂芳,带着佣人接他,表兄表弟一见如故。卢桂芳虽比他小几岁,却很能干。在陪德鸿到预科新生宿舍所在的译学馆安顿下来之后,他告诉德鸿,自己在读中学,还没毕业。德鸿问了他,才知道卢表叔担任的是公债司司长,每天都忙得很。
这天晚上,他到卢表叔家吃晚饭。卢学溥见了德鸿,笑着说:“几年不见,德鸿长得一表人才了!”又对桂芳说,“那年你表兄十二岁,他祖母和二姑母主张他到纸店做学徒,我想,这不是要把‘料改成马褂’吗?就去对他祖父母和他母亲说,才使他能继续求学。
德鸿,你母亲为了你能读书,可真是操够了心呵!”他嘱咐德鸿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他,缺什么就到他家里拿。饭后喝茶时,卢学溥对桂芳提起德鸿童生会考曾获第一名的往事。
德鸿说,那全是卢表叔的鼓励。卢学溥夸他说,他那篇《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的作文确实写得好。“我还记得给你写了一段批语,却忘记了,你还记得吗?”
德鸿见问,答道:“您写的是,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这一说,卢学溥也记起来了,“对么,我是针对你写的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说的。德鸿,桂芳,你们不仅要记住这句话,还要以这句话立身行事。”
几天后,大学的新生活开始了。
沈德鸿看到了许多外国教授,教外国文学和第二外语──法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教授大多是有名的学者,如教国文的沈尹默,教文字学的沈兼士,教中国历史的陈汉章等。
德鸿喜爱读的依然是小说。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任凭他随意借阅。他曾写道:“……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那时在北京大学尽看自己喜欢的书……”
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对于沈尹默的古代文论课,更是学得津津有味。
沈尹默学贯中西,精于诗文。他教国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