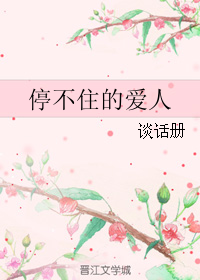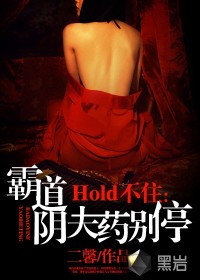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是性质不同。
再加上非常重要的一条,餐馆之类的工作场所,是有可能遭到移民局的突击检查的,
而移民局想要进入别人的私宅可就麻烦大了,他们决不会为了一个非法保姆惹这个麻烦。
所以谁也没有听说过移民局上哪个家庭去查非法移民的。于是,这种雇非法工作的保姆
的情况,就开始多起来。而且基本上是发生在一些收入较高的工薪家庭,也就是克林顿
那两个“提名人”这一类的家庭。所以,这也是克林顿有可能会连续撞上两个“保姆问
题”的原因。
不管这么说,堂堂美国总统任命司法部长的精心策划,就这么栽在两个墨西哥小保
姆手里。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克林顿行政分支下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实际上已
经是他被迫推出的第三名人选了。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
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么尴尬
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么
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
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
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
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
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
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会,司法
部门,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一大帮“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事儿多”是理所当然
的。再者,他们也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
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决不会罢休。他们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再投他
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
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
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
有按我们的想象,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
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均势力敌而
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
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自然会提出前面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既然美国总统在这里
不是一个独立的顶端人物,而只是这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脱离这个整体结构孤
立地去谈美国大选,就意义不大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费点力气,探出一个究竟来。
如果去探究这一切的源头的话,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句话。这是今年老朋友送给
我的“顾准文集”里,顾准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一个原来象是洋娃娃一样被丈夫养在家里的一百年前的女子,没有外援,仅仅为了
个人的理想,就断然出走。这一事件怎么看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难怪一百多年
来,同一个娜拉,已经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从她的出走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甚
至是并不相同的“革命意义”。
娜拉被“带到”中国之后,不知有多少几十年前的新女性,从这个洋榜样身上汲取
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一一冲出各自不同的家庭,造就了无数“中国娜拉”。娜拉不仅
在出走的举动上具有革命性,更在广义的精神上具有革命性。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挪
威女子娜拉,她的“出走”也成了充满刚阳之气的“革命”的代名词。
在娜拉的这场“革命”中,其他的一切皆可视为“革命的代价”而被忽略不计,可
是,把一腔热情满腹关怀都倾注在娜拉身上的人们,怎么可以忽略“出走以后的娜拉”
本人!于是,又引出了不少话题。在中国,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就是鲁迅对于娜拉出
走以后的感慨。看上去,他是对为数众多的“出走后的娜拉”忧心忡忡。他觉得“出走”
还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若是社会环境险恶,那么孤身一个弱娜拉,到
最后不是哭哭啼啼重新回家,就是流落风尘,未见得就是好结果。这么一来,破坏了大
家为娜拉喝彩的好心情。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
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
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
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
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
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
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
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于是,革命胜利最终成了大家梦寐以求一个日子,一个突破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
候,大家在狂欢之中醉眼惺忪,看出去的一切都笼罩在五彩的光环之下,大家再一次弹
冠相庆举杯互祝,互道:这下好了。
这样的欢庆,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广场上,庆祝各种不同年代所发生的
性质不同的“革命成功”。我有时候会觉得一种深深的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地
方,这样一杯欢庆的美酒会如此长久地起作用。因为,毕竟陶醉其中的各色人等都有,
其中有不少人似乎是不应该久久地迷失在这样虚幻的光环里的。
这种庆典的气氛持续越久,当疑问升起的时候就越沉重。“这下真的就好了吗?”
在中国,终于又一次有人提起“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但是这一次的提问,比起当年鲁
迅的沉重发问,更增添了何止百倍的沉重。娜拉已经被升华为一个象征,天翻地覆般社
会巨变的“出走”已经完成,既已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相同一个问题?
我突然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美国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独立革
命吗?那么,这位美国娜拉“出走”以后又是怎样的呢?当初这位“美国娜拉”的一举
一动,不就是我今天看到的美国的种种现象的根源吗?这种联想使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我发现,美国娜拉在经历“出走”之前,对自己“以后将会怎样”这个后果问题,
也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她也是迫于现实才静静地坐下来,非常理性也非常现实地认真考
虑这个问题的。
美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没有值得夸耀的年头长达四位数的深
厚文化传统。不错,它的早期移民来自英国。但是,它确实并不因此就敢拉大旗做虎皮,
在自己的文化与英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之间划等号。在独立之前,他们断断续续地是从
英国带过来一些“文化”,但是即使是带过来的这点文化,也早已被新大陆强劲的风迅
速地吹散开来,吹得变了味儿。令人联想起南橘北枳这样的故事。
独立以前的美州殖民地,如果说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从表面看上去有什么相
同之处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那种“流动散沙”的状态。这种无规律的流动,
既意味着新大陆的内部流动,也包含了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对于流动的推波助澜。
虽然在殖民时期,也有英国派来的总督政府及其一套班子。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生
活的人们,始终也没有遇到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死盯一层的严密控制。其根本原因倒
不是英皇不想对他的子民严加管束,而是在当时的新大陆,这种管束在技术上是做不到
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意义。不仅皇帝远,皇帝所拥有的
庞大管理体制远,甚至连产生皇帝的文化,都非常遥远。人们的分散与流动,又使得殖
民地仅有的统治,其强度从中心向外迅速递减。
即使是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也远不象在英国本土那样有章法。照说,他们有
着悠久的治理传统,只需开来一批人马,移植一个模式,照搬一套制度即可。而且,他
们是在统治殖民地,背后,已经有现成的洋洋万卷各式英国法律法规在支撑。他们只需
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也许是情况太不相同,也许是人手不够,也许是交通不便。总之,
就是管不住。所以,对许多在执行中被因地制宜篡改了的规矩,他们也只好眼开眼闭,
听之任之。
更何况,北美的殖民政府对于到底如何去开发治理这样一块新大陆,也是心中无数。
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有过一些实验性的管理方法。比如说,甚至有过
在佐治亚州完全失败的如军垦农场一样的“开发实验”。
于是,在殖民时期的北美洲是一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地方,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条条管
理,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是分散流动的,作为群体的人是分
散的,甚至有时也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和宗教理想的人们,
也在一块块有着高度自治权的“小国土”上,进行过各种不同的理想实验。权力是分散
的。在独立之前,这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十三个政治中心。
我想,如果真要把一大片国土比作“一张白纸”,作“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类
的比喻,那么,按说几百年前的这块地方大概是最象一张白纸,最合适按构想的蓝图去
实践了。但是,在从一开始移民进入北美起,大凡仅仅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完美的宗教理
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甚至是经济建设理想去实行的,最后往往碰壁,反倒是一些
世俗的随遇而安的做法,更容易延续下来。于是,回顾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几乎是一
部充满了各种理想实验,又同时充满了妥协,退让,放弃和变通的历史。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大概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服从新大陆上无情
的生存规律。在这里刚刚开发,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移民最重视的是生存。生存是首要
的,理想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别说是几百年前站在蛮荒大地上的移民了,就是今天
踏上这块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富国土的新移民,也很难逃避这样的生存规律。他们被迫
变得比原来的自己,也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实际。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导致这样历史结果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如我们这样的新移民
们同样必须面对的。就是每一个进入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文化打交道,
如何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文化群相遇的时候,妥协和变通是
和平相处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和几百年来的北美移民们的共同课题。
这种北美新大陆特有的妥协,变通和实际,看上去确实显得“俗气”,所以也始终
为欧洲的理想主义者们所不齿。
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了,在这样一块殖民地上,老百姓事实上对英国并没有大的
什么依赖性。北美的老百姓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松散的,那么他们是靠什么维系
了那么久远的关系呢?我觉得形象点说,这种关系几乎就象是娜拉对丈夫和家庭的感情
维系。这是从哪儿说起的呢?
实际上曾在不短的时期里,除了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之外,美国人自己也是陷在很
深的自卑里难以自拔。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脑后就有反骨”。他们自己没有辉煌的文
化,就希望能与古老的欧洲文化至少不要断了那点血脉关系。
说实在的,至今为止,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对于相当一部分建筑庭园设计,家具及
手工艺品,“殖民时期风格”还是足以炫耀的广告用语。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
样的广告宣传颇不理解。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对这样“殖民时期风格”的自豪
广告,在感情上疙疙瘩瘩。按说我们是外国人,这块土地在两百多年前是不是英国的殖
民地,与我们根本毫不相干。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在我们的逻辑里,被“殖民”则意味着是
一段屈辱的历史。如此的广告宣传就意味着“没有民族自尊心”和“把耻辱当光荣”等
等一系列“殖民地奴隶心态”。“半殖民”都尚且不堪回首,何况是“全殖民”。凡是
“殖民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只能充作激扬“爱国主义”的教材。这种逻辑和概
念,已经随同我们的文化背景溶化在血液里。因此,我们是在本能地如条件反射一般,
从心里抵制这样一种“辱国求荣”的文化现象。
但是,我终于发现,美国人对此从来不产生这样强刺激的联想。对于他们来说,殖
民时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殖民者有好有坏。大大小小的殖民总督和殖民者,
他们的名字至今还是美国许多城市和街道的命名,他们的铜像依然在美国各地熠熠闪光。
因为他们与这块土地的开发建设历史紧紧相连。至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