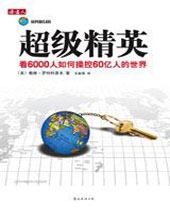精英的聚会-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六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背后的感情是伟大的。杰文斯下结论说:“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到了那一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为可以完全抛开,但我们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切实的进步将会使每个阶级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
虽然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一些现实想法的影响,杰文斯逐渐向“左”靠拢,虽然远没有达到穆勒生前所达到的程度。他始终不渝地呼吁对教育(因为这显然与医疗不同,它会改善穷人的“品格”)和适宜的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他在“民众的娱乐”一文中,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为广泛的民众提供有益的音乐看作是一项公共职责。他把由于“大量定居的、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大厅管弦乐看作是可以引进到曼彻斯特的最好的东西。他在伦敦的日子里曾写道:“一个人时常会渴望那伟大的管弦乐中嘹亮的长号、滚滚而过的鼓声、音叉的庄严鸣响以及那推向高潮时愈来愈急的兴奋感”。显然,不管杰文斯对医院怎么想,他会
为英国广播公司而欢呼。他逐渐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对于邮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对包裹运输与电报的政策的评判标准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年)采取了一种谨慎、折衷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是尽可能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一般会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并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权威挑战……这一质询的结果是使我们不再制定粗制滥造的法则,而是根据是非曲直来仔细判断每一件事情。”
记录下杰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为止的发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里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课本:
《纯逻辑》(1863),1000。
《煤炭问题》(1865),2000。
《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7000。
《科学原理》(1874),9000。
《演绎逻辑研究》(1880),6000。
《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9000。
《社会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2000。
《经济学原理》(1905), 1000。
从表面情况来看,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高处,荒原边上的一所房子里。1880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由于他更乐于写作,所以他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他计划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时间完成拟议中的《经济学原理》,这本遗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经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贝克斯希尔与黑斯廷斯之间游泳时,突然感到一阵虚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赫伯特·斯坦利·杰文斯像他父亲一样,接受的是科学方面的教育——地理学与化学,然而他依靠经济学方面的天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获得了加的夫大学、阿拉哈巴德大学以及仰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席位。杰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将近30年。
对于杰文斯的死,举世同悲。虽然他在46岁就英年早逝,但我认为,他死得其所。在从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时期,他的天才、神圣的直觉以及炽烈的使命感处于鼎盛阶段。最后时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经微弱而且闪烁不定。
七
杰文斯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象被记录下来,而在他去世54年后,已经极少有人认识他了,即使有人认识,在他们头脑中寻找有关杰文斯的清晰的印记,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并未给他的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非常内敛的。他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强单独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着,又被它所拒斥着。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无穷的信心。他渴望去影响别人,而不受别人的影响。他深爱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亲密。在他27岁的时候,他以这段话来描述自己16岁时的精神状态:“在1851年的时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阴森的房子,至今看到还心有余悸——生活得并不愉快,同伴们不是恶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时候,当我在房顶上的小卧室里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光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能够而且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多……我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相信对于我的动机与目标,任何人都不能知其万一。我父亲可能知道但很少。我从来没有和他敞开心扉地谈话。在学校和学院里,我在班级上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细掩藏起来。我常常想,这种冷漠性格既不欢快也不可爱,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正是必需的吗?”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一个人独居。他不愿意参加殖民生活中的社会活动。1857年,他22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姐姐,来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机敏方面没什么闪光之处。我所仅有的是糟糕的记忆力,任何时候我都只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数人都能记住很多。我不是一间堆放物品的仓库,而是一台制造物品的机器。给我一些事实和资料,我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井井有条、细密编织的理论,或者给它们以新的外观。我的头脑里有着最有序的结构,我对给事物分类的兴趣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常常招致痛苦。同时我想,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确有能力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一定的创造力,我能搞出新东西来。这并不是说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而是指我能抓住一两个想法并把它们发展成协调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往里扔一个曲别针,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一个全新而匀称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1865年,在他就要结婚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时候,我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而其他时候,我只是感到责任的压迫。我越来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项毕生的工作在等着我,逃脱它是不可能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感到我所怀有的潜能,它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培养和开发,对它们的任何误用和忽视都将是一种最大的背叛。然而,这样一项艰深繁难的工作带给我的麻烦却是绝不轻松的。一种责任又在与其他责任相冲突,我的头脑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我将去爱与被爱。然而我要从事的研究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感到无法在其他方面实现我的想法。首先,我将命定贫穷。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别人。在这样一个挣钱爱钱的世界里,忍受贫穷带来的粗鄙与寒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亲属能同样忍受。那么,我的另一半感情与挚爱只能怀着伤痛深深埋藏起来。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