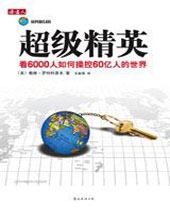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Ӣ�ľۻ�-��4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ٴμ�������������һ�����ᡣ������跨���˴Ӱ�ķ˹�ص���������һ���籨��˵�ҽ������պ�ִ����ϣ���ܼ�������������������ˡ�
����������ķ˹�ص������˼���Ͷ����ߣ�������Ϊ��ò�Ҫ���ùݻ��档�����ҵ�����άɪ˼�����������ܲã��������鷿��������֧�䡣��ס�ڻ����˺Ӹ�������Щ�˺������ͬ��ԲȦ���γɰ�ķ˹�ص�����ɫ����������ǰ��һ���˺ӣ�����������һ���˺ӡ��������ݣ���Ϊ������ȥ���ٵ����˸�ۡ����һ����խ����Ϊ����Ŀ�������ɢ����С������������ʹ�û�����ֱ�Ӵ��˺��ϵIJ����б����ŵ���¥��ȥ�������ܳ�Ϊס�����ջ֮һ���������������У�άɪ˼��ʿ����צ�������ܲã������������鷿���������������˺��Ͽս���ڰ������Զ�����צ�۵ƾߡ�Ӱ�ƹ��һ�б����в������˵�С���裬������I7���ͺ��������ʵĸ߹�����ϡ�û�������Ƕ��������Ų�С�ĝ���ϸ�꣬�ҷ������˺���ȥ����ʱ�ҿ�ʼ����ڵ����ҷ��籨֪ͨ÷�����¶��ij嶯����Ϊ�����뿪Ӣ��֮ǰ��������û����������ͷ����λ����ܴﵽʲô���ܵ�Ŀ���أ�Ȼ�����Ҽ���ϣ�������������ڣ��ſ��ˣ�÷�����¶����˽�����
����������������������˾������ڵжԡ���ں;����л��������ˣ��ܺ����谭�ػ��棬�Ǻܲ�ƽ���ġ���Щ����̸���ƺ��ǿ�Ц�ģ�����һ���Σ���һ�̵ĸ���ִ�֮��������������ʼ��һ����������̸����������ͨ���������������ҹ�����κ���������ӣ��Լ�����Լ��ǩ�ֵĶ��������Լ��Ĵ�ְ����Щ�������������������������µģ������Ȳ�����ξ��ı��ѣ���Ӣ��������һ�������˳�����ŵ˹�ơ���ά�����Լ�֮���һ�������ڸ����ľ�������������Ͼ������κ��¼������DZ���ǩ�֣�����÷�����¶��������Ϊ���ͺϡ��������վ�������������ӹ��Ŭ�����Dz�֪�����������÷�����¶��ĸ��������ŵ¹��������Լ���������������Լ�����ٺ����裬�������������ǡ���ʱ����һ�Σ���Ҳ����������⣬���¾����������������������������˵���ⳡս����һ���Զ�����ս���������������ǣ����ںڰ������Ŀ��ǣ���ɺڰ��������ڿ������ڴӶ���������Ҳ����ǰ���õ����⣬����һλ�����ı�������ǫǫ���ӣ�һλ�ϸ�ģ���ֱ�ĵ��¼ң�һλ��̫��ѧ�ߡ�Υ����ŵ��Υ�����ɣ������ֹ��˥�ˣ�һ���˱��ѳ�ŵ����һ���˲���ʵ�ؽ��ܲ����ܵ���������ʵ��֮�ģ��¹��������������е�������������ЭԼ��ǿ��������Ȩǿ�ӵĶ���һ��������ġ���������ЩΥ�����ɵ������������ص��˺�������
��������������̸��ȥʱ�������ȥ�ˣ��ʼ���Ҷ����Եû��������Dz�Ӧ������һ�����ͣ����κ�����һ��һ����������������ҵ��ùݣ����Ƕ���һλ����������̫�ˣ����ޡ��ֲ���÷�����¶��ĺ��������ֵܣ�����ǰ�������ίԱ�����Ҫ��������쵼�Խ��ڼ�֮һ����Ҳ��Ϊ�ҵĿ��ˡ��������������ķ˹�ص�������÷�����¶���������˽������ˣ���·�ϴ���ȥ���Ŵ�ƶ��Ժ��ͥԺ����˵�����������ش���������������������ա����Ǹ����˵����ڣ����������ӵ�������
�ҵ�����ʱû������������������д�Ĺ�����ͳһ�µIJݸ塣��ͺ��ҽ���������������Ϊ���徲��������¥�����û��ȥ÷�����¶������Ҷ���ȥ���ҵ����ҡ���ע�����λ��̫�˵ķ�Ӧ���ֶ������ڸ���ԭ��������ͳ�������ľ��ȸе�һ�ָ��ˣ���Ц�ţ�����Ц�ţ���Ϊ����һ�����õĴ������÷�����¶������Ҷ�ʱ����ø������ˣ�ֱ����β�����Եü���Ҫ�����������ˡ��⣬����Ļ������һ�棬�Ȳ��������ԭ��Ҳ���Dz��ɱ�������ˣ�Ҳ����ׯ�ϵ�а��
�ԡ��ҵ������������ĵ�ע
��������������ƪ��������Ϊ�ҵ�һƪ����¼�Ľ����д�ġ��ҵĻ���¼����ʱ��¡�����˹���ڣ��������������ļ�������������������û�а���ȷ������˹���ҵ����µ����ڣ���װ�����ŷ����������1938��8�µס��������£�ӡ�������9�³�д�ġ���ʱ�ҵ�����������ͷ���������ʵġ��ҵĻ���¼����Ŀ�ǹ�����Щ�µĹ��£��ҽ����ҵļ�λ���Ѹ�D��H������˹����ǿ�ҵز�ϲ�����ǣ���ʹ�ҷdz�ʹ��Ҳ�dz�ʧ������Ҳʹ����ֹͣ������˹������˹������˹�ϲ�����ҵ��������е�һ�������������ǵĸо�����ʵ����˵�����ڽ̵IJ����ݡ�����һλԤ���ߣ���������Щ���ǵ�����ʹ���������ܳ�Ϊ������ͽ���ˡ����ҵĻ���¼�У��ҽ���д�˳�����������¿���˹�����������������������¡�
���������ҿ�ʼ��ʶ����˹�ͷ��������1912�꣬�������Ҹ���ͬ�������ꡣ
���������ҷdz�ϲ���������Һ���������Ҳϲ���ҡ��Ҵ�δ���������ֳ����������ŵ����ҡ��Ҽ�Ϊ��ݣ�������Ȼ��ݡ������Ķ�ƪ���£�����ʫ�����ļ���С˵���ر������ĵ�һ��С˵����ȸ����������һ�����������ߺͿ�ѧ�ң��ҷ�����ֱ���ĺ���ϵ���ѧ��ͬʱ�������Խ��ŵ������ǵĹ���ʹ�Ҹ���Ȥ���������ҡ�
���������������Dz��ɱ���ģ���ٻ��磬����˹����ѵ���ң���Ȼ����Զ��������ؽ���������ѧ��ͨ��������ҵ������ǣ����ԭ�ѳ��ֵ��Ѻ�Խ�������ˡ������һ�ΰݷã�ͬ����˹����һ��֮����д����������Ī��Ůʿ������Ҳ���������ܸ���������һ�������������ͨ�ż������У�
���������������д�ά�������غͷ�����˹�����������һ��ȹ���ĩ�������ն���ʱ�������е�ãȻ��ʧ�����������Ұ����������ҵ��ϵۣ�����̸��ʹ�ҷ��衣����Щ������̸������ʹ�ҳ�����ɫ�ķ�ŭ������û��û�˵�̸������û��û�ˡ����Ӳ����Ӳ�˵ʲô�ö���������ÿ�˱�װ�����Լ���һ����Ӳ��С����������������˵����������Ҳû���κθо������ƣ�û������û��һƬ����һ�����������������Ҳ�Ը�������������ѡ��������ɶ���������ʹ���μ���һֻ��Ы��һ��ҧ�˵ļ׳档��ɱ����������һֻ�dz���ļ׳档��Ū�������������ˣ��������ٴ�������ɱ�������������������ܵĶ����һСȺ�Լ��˵Ŀ־塣
����������ͬһ�죬1915��4��19�գ�����˹д�Ÿ��ң�
�������������װ��Ĵ�ά��
����������Զ��Ҫ�ٴ����ն������ҡ�����������ڼ׳�һ�����������Ķ��������ǿ��µġ�����ġ��Ҹо��ҽ���÷�����뵽���־Ȥ��Ͷ��һȺ�ˡ����˿ϡ������غͿ���˹�����ն�����ʹ���μ��˼׳档�ڽ���������һ��ͬ�����Ρ���ǰ����˹���������������е���������������������������ǰ���ڿ���˹�͵˿ϡ����������ϣ��������ڱ��ն�������һ����ʶ��������������뿪��Щ���ѣ���Щ�׳档���ն��͵˿ϡ���������Զ���ɾ�ҩ�ˡ�����˹��û���ա����������������ڽ��ſ�������˹ʱ�������������е�Σ��֮һ����ʹ�ҷ����ˣ�����ʹ�ࡢ����ͷ�ŭ����
�������������Ǹ�����ͬ����ͬ�ҵ������Ǿ��ѵ�һ�����ͨ뺣���������Ϊ���ʵķ�ʽ��������š��Ժ�żȻ�أ���ͣս֮ҹ��1918��11��11�գ��ڰ��¶��Ƶ������š�ϣ�����ķ�����ҽ����ټ�������˹һ�Ρ��Ѻ۽������������ˣ���������˹����������Ӣ����������ﶨ�ڷ�Ӣʱ�Ҽ���������������1928��д������˹һ��ʹ�����˵����У��������Ҷ�ô��ݡ���̩�����˵����ˡ�����Ϊ�ر�����Ҳ����д��һ����ů���Ѻõ��š�
������������������������Щ��ʵ����Щ��ʵ����÷�ɵ¡�����˹���¼���������������������ܵ������ǵ����������������ǽ��ŵĴ�ѧ��ʱ��
����������
����ʮ���¡��ҵ���������
���������Ҷ�1914�꣨����˵��1915�꣬���ҵļ��������Ҫ������һЩ����D��H������˹�Ļ���������¡�������Ҳ��һ�����м�������μ��棬�����Ǿ��ֲ��ϴμ���ʱ���������õ����ݡ��������ҵ��ǣ��ҶԵ�ʱ��̸����������һ�ɶ�����ֻ����ϡ�ǵ�һЩ���ܡ�
������������һ����;ۻᣬ����ά����Ժ���١����أ������ڴ��Dz�����Bertrand���dzƣ��ķ�������С���ʱֻ�����������ˡ�������֮ǰ������˹���һֱ�벮�ٴ���һ��������ǰһ�����Ͼ��й�һ�μ��ᣬϯ�䣬����˹�����Ķ��ǽ��ŵ���ʿ����������ϲ��������ᡣ�Ҽǵã�������̸���Ŀ�ʼ������˹��������������Ĭ���ԣ�ֻ��ʱ��ʱ��ð�����䷴�ԵĻ��������糿������ˡ�̸����Ҫ�����ҺͲ���֮����еġ����ڵ�ʱ̸��Щʲô��������һ�㶼���ǵ��ˡ�������Ƕ��˵�����һ�������Dz�������̸���ġ����̸����רΪ����˹���ŵģ�����ϣ�����ܲ�����������������ǵ�Ŭ����������ʧ���ˡ�����Χ���ڻ�¯�ߵ�ɳ�������˹�������ף���������ڶ��ţ����ʹ����Դ�������ʱ��ʱ���ڻ�¯��վ����������˼��ʱ��Ҳվ��������֪�������������ߵľۻ��У���λ������֮��̸���������龰������ǰû�м�������˹������Ҳ��û�м�����������֮������ͨ�ż������ˣ���һ��������˵�����Dz�¬ķ˹������ֲ�Ψһ֧�����ij�Ա����Ϊ�Ҷ��������ġ���̩�����˵����ˡ���
�������������ǵõľ�����Щ�ˡ��������������˹����ƽ���������������ҿ�������һЩ�ƶϡ����룬����˹��һ���ܵ����������о�����Ӱ�졣��һ�Ǽ����ڰ��������ϡ�������ʼ�ն���������һ���罻Ȧ�ӡ����˲������⣬���źͲ�¬ķ˹����Ҳ����������������˹�������ա����ֶ�����ȹ���ϲ�ͬ�ļ����ޱߡ�����˹��������λ�Ĵ�ʼ�����ʱ�����ŵ�Ψ�������Ȯ�����������ڶ�ʢʱ�ڣ���ʹ�������˵ִ����������룬����ʹ���γ��˶Խ��ŵĵ�һӡ����ѹ����������������Ҳ�ܳ��������������������һ�������ϵķ��ҡ�����Ȼ��һ�ֽ�����Ҳ��Ȼ�����е����ʵĺ����ġ�����ȼ���ؾܳ�������Ҳ������������������ڣ������Լ���������������Ȳ���ͨ��������Ҳ����ͨ�����Ż�¬ķ˹�������Ȼ��ϲ�����ᣬ������������Ϊ����������ʱ�����Ͷ��ĸ�ʢ�ˣ���������������������ڽ��Ŷ����в���һ�������˼���֮�⣬����˹��սǰ���ŵĶ�������Ҳ���ص����Ը��ӡ�
����������Ȼ��ˣ���ô����˹�ĸ������Ƿ���һЩ��ȡ֮���أ�һ��˵�����еġ����ķ�Ӧ��Ȼ��ʧƫ�ģ���Ҳ������ȫ�ǿ�Ѩ���硣��˵������������̸�����ݣ����������������˹��̬���Ǻ����ױ����Ƶġ�����Ȼ�������˵�̬��������ȫվ��ס�š���ˣ���������̸���ı����ֵ���Ͽ�����������������ɼ��ģ�����������ֵ�������������̬������û����Ҫ֮���أ�����˹��������������Щ�������м�ֵ�Ķ�������������ֱ������ⲻ�ܲ�˵��һ��ȱ�ݡ�������д�Ĵ���ʹ�������»ع���սǰʮ���������ǵ�����ʷ������ⲻ������ֲ���������ô�ҽ�����ƪͶ���`�ĸ���лع�һ�������������Ϻ;����ϣ������������ϵ����̣��Դ���˵��һ���հ�ͷ����������������ӡ�ǡ���Щӡ���ִӺζ������Լ�һ�����Ƿ�ӦȻ����������ʱ��������
��������������1902��������ս��������ŵġ��������Ħ���ġ�����ѧԭ���������ˡ�������һ���ƺ���������ȥ������Ȼ������Ȼ������Ӱ���������Ӱ���Լ�Χ�������е�������������ͳϽ��һ�У�Ҳ��������ȻͳϽ��һ�С�����������ʱ����һ���˵�������Ӱ��һ���˵���Ϊ����Ҳ���������˵����ԣ��ڳ��������������ͻᵭ������ʱ�������γɵĶ��ص��������δ�ġ�������Щ���ص����Ӱ�������Ǵ�����ˣ�ʹ���ǻ㼯��������ֲ��������������˷ֿ�������������Щ���������ͬ��������Ӱ���������˵�ǹ�ͬ�ġ���Ħ�������Ǹ����ͽ��˹�����棨���������ʱ�����֣����Ǹ�����̩�����ߣ��������λ���ȣ����Լ��Ǹ��ǹ��̽�ͽ��л�õ��Ǹ����̽�ͽ�ͣ����ڳ�Ϊ����ʦ���������Ǹ��������ֺǺǵļһϤ�ᡭ�����Ǹ��ž��̽�ͽ���������Ǹ����������ߡ�������Щ�ողμӽ��������У������Ͱ�˹��˼��Ħ����˽�����꣬�����Ħ����Ӱ������˹��������ʱ����ò��࣬����ʱ�Ѿ�������Ⱥ֮���ˡ�ֻ�Ƕ�������Щ��1903��ܻ�Ծ������˵��Ħ����Ӱ����ȫȡ������������ء��Ͻ�ɭ�����ء�����Ӱ�첻������ѹ���Եģ���������˹�����泣˵�ġ����˾�ɥ�����������һ�����ˡ���һ�ж���ô�����˷ܰ���������һ�����ո��˵Ŀ�ʼ������һ���µ��˼����ã������������µ�������Ԥ���ߣ�����ʲô�����¡������������ķ�Χ�г��������ʹ��������Ϊ����ʧ���ʱ��������Ȼ���л�����������������һ�������߱��ģ�����ֻ�Ƕ�ijЩ�����Լ�Ч�£�Ȼ���ǵ����ܳ�Խ���ǣ��������������еĻ��������ˡ�
�����������Ǵ�Ħ�������õIJ�������������ġ�����һֻ���Ѿ��������µ����õ��ż���Ȼ����һֻ��ȴ��Ȼ�������������˺ͱ��ڵĹ�����������Լ���ͳ��Ϊ��һ�����С�������ѧ��ԭ���У���һ�������Dz�мһ�˵ġ�����˵�����ǽ�����Ħ�����������־ܳ������ĵ���������ʵ���ϣ����ҿ�������������������ŵ�֮һ������ʹ����������Ϊ����Ҫ�Ķ���������������ָ���˱����Լ��ռ�Ŀ�꣬�������¡�����ָ���������н顣�����ҽ���˵����һ����������������������������ǽ���������
����������ʹ���ֲ����³�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