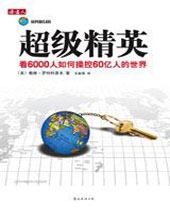精英的聚会-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击复辟势力、缩短内战时间、减少其受害者数目。如果不采取这种步骤,那最好就根本别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组织一场广泛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放弃了广泛斗争,那就不会有任何严峻斗争的思想。”
考虑他的假说,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辩是不可答复的。没有比游戏于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这就是他的有意义的话。不过,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假定社会转变的道德与智力问题已被解决了——存在着一个计划,除将其付诸实施外,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假定,社会被划分成两块--信仰计划的无产阶级和出于纯粹利己原同而反对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说服许多人之前没有一种计划能取得胜利;假如真有一种计划,那它会从许多不同来源获取支持。他如此倾心于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诉我们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第二篇 经济学家的生活
献给玛丽·佩利·马歇尔
威廉·佩利之曾孙女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妻
第十二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Bacchus——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
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 (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而在复辞时代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而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找们的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员)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去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的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内,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他“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资料。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作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都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他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丹尼尔·马尔萨斯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论》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以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论》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
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