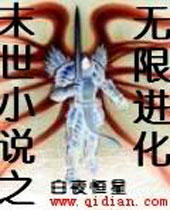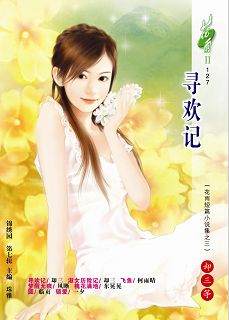短篇小说(第十八辑)-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佳选择。只有他本人才能透彻理解,在妙园不经意观察到那个女孩子的微笑对他意
味着什么。他十分恳切地说,对他这样心性孤傲的一个冷冰冰的人,这无异于一灯
如豆,融解了原始冰川。讲到了这些,博士也深为那位女士感到痛惜。她原先的笑
容,如同声光电子信号,在她全然不知不觉中尽数脱落了。她哪里知道,如果她希
望恢复原有的信号,不可能依照程序又从外部重新录入。她只能逆时针流转,回到
她本来的那一抹笑意的发祥地去寻觅,只此一途,其外没有任何近便可行的路。
他的这一番言语,是不是带有过多神圣化的夸张呢?博士争辩说,他无意用神
圣的光环来装扮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一汪山泉,清澈见底,气泡儿时断时续涌
上水面,一簇簇一串串,如泄珠玑。不妨说,这便是大地的一个自觉不自觉的笑容,
如果没有外力去改变地下水的经络,它总是会不断向我们这个世界送出一簇簇一串
串微笑。女孩子的一个微笑,和一个水泡儿没有什么两样,说到底,无非是天地造
化馈赠给人类的一个小小的微缩景观,无神圣可言。当然,也不可归入凡俗,落入
凡俗,自然远离了神圣,着意神圣,也已经无异于凡俗了。以这小小的微缩景观,
比之于世界十大人文景观,便显示出了截然的不同。人文景观是人力物力财力堆出
来的,不难计算出它的价值几何。如果可以把一个笑容比作日出,那么这眉宇间的
日出,便足可等同于宇宙间的日出。你无从计算这两种日出的价值,两者都是无价
的。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单位一个家属认识了那位女士,并且建立了亲密友谊。
她告诉女士,很久以前有过那么一位年轻军官,换了便服暗暗追踪她达十年之久,
夸张一点说,她是在一名军人远距离守卫之下长大成人的。非常难得的是,经历那
样漫长的年月,这位守卫者只求尽心尽职,从没有一次打扰过她。起初女士以为是
说笑话罢了,越听越认真起来,对方竟能说得出,她上小学背的是什么样的书包,
书包带子太长了,在胯骨上一磕一磕的。又说她中学时代,用的是一辆二六凤凰女
车,把车座升得老高老高,经过妙园不许骑车,她总是一只手拎着车把走。女士绝
对不相信,分明又绝对的真实无误。她惊异极了,好一阵大惑不解。她回忆说,还
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经过妙园,好像有人在注意她,她很不好意思,因为
没有买门票,是从栅栏墙钻过去的。回头看看,又看不到人。从那天起,每次经过
妙园,总感觉银杏树林里有人在观望着她,久而久之,也就不大在意了,可是这种
有形无形的感觉始终存在的。她清楚地记得,那年高中毕业考试,她冒雨赶到学校
去,雨衣被槐树枝挂住了,手扎得生疼生疼,怎么也摘不开。她不知怎么突然意识
到,银杏树林里一双眼睛正远远注视着她。女孩子家,发现有人注意自己,不知怎
么好,丢下雨衣不要了。女士自我解嘲说,当时下着瓢泼大雨,四处迷迷蒙蒙,大
风要把银杏树卷跑了,树林里还会有什么人呢,只不过是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种直
觉罢了。
[注]中国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合著《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
的想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2 月出版。
(此文原载于《人民文学》2000年第一期)
文学视界
挟持进京
韩东一
袁义打电话给我,说郑一川最近要回国。他准备从北京走,然后回成都。袁义
问我要不要来北京一见?我说:到时候再说吧。袁义说:一川一周内准到,你要到
什么时候再说呢?他的意思是让
我马上决定。
说实话,我并不想去北京见一川,没有那样的冲动。我们分别已经十二年了,
我早就做了准备,永世不再见面。不是说我和一川之间有什么过节,恰恰相反,当
年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和一川住一个宿舍。袁义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常来
串门。一度我们三个关系亲密。可事过境迁,再来补续前缘不是我的习惯。这方面
我有些冷漠和不近人情。
袁义一直留在国内,但我们的距离也不算近。
若不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这个朋友恐怕也已经失去了。我从
来没有主动给袁义打过电话,因为时间和距离,还有职业关系,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通过上面的叙述,你大概已经看出我的问题来了。总之,我变得越来越古怪。
袁义他们一直在试图“挽救”我。他们想把我“拉出来”,和大家在一起,好吃好
玩,快快活活开开心心的,就像当年一样。
此刻袁义力劝我前往北京。与老朋友见面事小,帮助我脱离苦海事大。或者说
与帮助我脱离苦海相比,老朋友的欢聚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要知道无论是袁义还是一川,对我都有极深厚的兄弟感情,这也正是我不敢面
对的东西。
虽说我并不想去北京,但也不便就此拒绝。袁义正是抓住了我的这一弱点。他
说一川25号到北京,他21号去上海,开一个会。回北京时他准备从南京走,和我同
行。
同行,说得动听,不过是挟持而已,或者说是押送。袁义问我怎么样?我说:
等你来南京再说嘛。我总不至于会不让他来。南京是我的家乡,我的地盘,有什么
理由拒绝袁义来此做客呢?袁义一向善于抓住我的弱点,紧追不舍。
你到底去不去?赶快决定。要是你不去我就不来南京了。
赶快决定,我好定票,临时购票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样,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去了北京。一切都是按袁义的计划进行的。他去上海,
他来南京,和我见面、吃饭、喝茶、拿机票、联系去机场的汽车。最后我们终于登
上了去北京的飞机。我和袁义的座位紧挨着,他坐外面,我坐里面。安全带束住了
袁义肥大的肚皮,使睡着的他不至顺着座椅下滑。我可怜的朋友,终于可以放下心
来了。
二
我们是23日抵达北京的。我被安排在燕京饭店里,等待一川一家的到达。袁义
回家住。他白天上班,晚上到饭店来,陪我吃饭、聊天。
25日,也就是一川一家抵达的那天,我换了饭店,由燕京转到了中山。当然越
换越高级了。这一举措是为了迎接一川的到来。届时,我们将住在一起,袁义也将
住到饭店里来。我们将通宵达旦地喝酒、忆旧,无所不为,这是可以想见的。
袁义由于工作太忙,换饭店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他的司机为我办理了一切。
下午,袁义从公司打电话给我,问我去不去机场接一川。我说:“算了吧,我
就在饭店里等着 。”这次袁义没有勉强我。四点左右,他亲自驾车去机场,迎接一
川一家。同行的还有小鲍,袁义新婚的妻子。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久别重逢,也
是两个家庭的首次见面。我孤身一人,没有去还是正确的。
我在中山宾馆里等消息。其间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称自己是袁义所在公司
办公室的,说是袁总交代的,让我换到十四楼去,房间会好一些。他解释说:上午
来的时候十四楼没有房间,这会儿有了。让我去下面的大堂办理手续,他在那儿等
我。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这儿已经够好的了。对方也不勉强,挂了电话。这一
插曲勾起我的好奇心。过了一会儿我独自溜进下面的大堂,看房间的牌价。我住的
这种规格每天八百八十元,一川一家入住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每天两千八百八
十八元。好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均花费和我差不多。而刚才让我换的房间,是和一
川他们同一规格的,也是两千多。这是何苦来呢?
当然住店不用我们掏钱,都记在袁义的账上。回想起这两天在饭店餐厅里吃饭,
我也都是签单的。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开始颇不习惯,后来竟然越签越爽,来劲了。
袁义工作繁忙,有时不能来陪我吃饭,我就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些写东西的朋友,让
他们到饭店里来看我,我请他们吃饭 。我对他们说:只管点,反正是签单,不用自
己掏钱的。于是这帮人狂点一气。你知道,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很穷,嘴又都很馋。
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自己是一个住在高级饭店里签单的人。虽然我越签越习惯越
签越喜欢,但还是不敢相信。我不相信,别人也同样不信。饭店里的服务人员大约
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签单的人(不相信我的衣着还是不相信我的气质?),每次
签单时他们都要核对我的房卡。每次核对房卡的时间都很长,足以使任何一个骗子
心惊胆战。
有一次他们终于憋不住了,向我指出房卡上的签名和我签单时的笔迹有所不同。
他们拿来一张纸,让我再签一遍。我的脸不禁涨得通红。幸亏我宴请的朋友中有一
个是见过世面的,他让我模仿房卡上的签名签一个。我照他说的那样做了,果然顺
利过关。服务员小姐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了句:先生对不起,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房卡是入住时袁义签的,当然与我的笔迹不同。好在我从小爱好画画,还考过
美术学院,临摹功夫不错,这回便用上了。
三
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我房间里的电话才响。是袁义打来的,说他们已经到了,
在下面的大堂里,让我赶快下去。
我带上房间的门,乘电梯一直下到一层。远远地就看见一川一家还有袁义、小
鲍坐在大堂东侧的咖啡座上喝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一川,与十多年前相比几乎没
有什么变化,只是人胖了一圈。他笑眯眯地站起来和我拥抱。在座的所有人都目光
炯炯地看着我们。
一川女儿的眼睛又圆又亮,睁得老大,模样一点也不像中国孩子,倒有一点像
印度小孩。她长得胖胖的,肤色黝黑,满脸的认真和坦然。一川让她叫我“伯伯”。
了了叫了声:伯伯,发音有些生硬。
最后我看见了李娜。想当年她可是美丽非凡的“川妹子”。一川每天坐在宿舍
里“撅着屁股给老婆写信”(袁义语),指的就是给李娜写信这回事了。
一家三口总的特征是胖。一川可用“胖大”来形容,宽阔的肚腹束着一只鼓胀
的钱包。了了也胖,个头已经和她妈妈差不多高了。我们(我和袁义夫妇)尾随他
们升上十四楼,来到预定的房间里。随后,行李也被运送上来了。
休息片刻,稍事整理后一川一家随我们出去吃饭。了了开始不想去,经过一番
说服才勉强同意 。这时已经九点多钟了,北京的饭馆大都已经关门。没关门又值得
一去的地方,又太远了。最后决定还是去宾馆内的餐厅。
众人再次乘电梯下到一楼,进了右手的餐厅。由于时间关系,除了我们这一桌,
已经没有客人了。袁义点了一大桌,足有二十几个菜。本已疲惫的餐厅方面立刻活
跃起来。一川大声地嚷嚷着,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时而四川话,引得袁义夫妇发出
一阵阵笑声。李娜也很兴奋,抢着说话。也难怪,他们终于回来了,落地了,放心
了,也轻松了。尽管餐厅里灯光刺目,客人寥落,但他们一样地感到开心和高兴。
连服务员小姐也受到了感染,在一边抿嘴而笑。
要了无数的啤酒。当问道“要什么牌子的?”一川说:当然是当地的。于是要
了燕京。他一直在说:这些年就没吃过正宗的中国菜,连做梦都梦见四川火锅。当
正宗的中国菜(想假都假不了)放满面前的时候一川反倒没胃口了。了了不习惯中
国菜,所以几乎没吃什么。李娜忙于照顾女儿和说话,也吃得不多。席间,只是我
吃得比较正常,喝得也比较正常,但说得就不行了。阔别多年,各自的境遇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四
了了最先离席,自己拿了钥匙回房间去了。她对中国菜没有兴趣,对他爸爸的
中国朋友也没有兴趣。了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这下文再说。
大约十一点左右,我签了单,所有的人都离席上楼来了。这次签单一共签了一
千六,大部分菜都没有动过,有的只动了一两筷子,够气派的,也是我短暂的签单
史上最辉煌的一次。
李娜回房间照看女儿去了。一川和袁义夫妇一起,进了我的房间。打开电视,
我们开始看一场足球赛。一川依然非常兴奋,后悔没有将餐厅里的啤酒带上来。他
打电话去服务台要酒,由于时间太晚,饭店的供应已经停止了。一川大骂中国饭店
落后。
他嚷着要下去到街上买啤酒。袁义说:商店早就关门了,北方就这点不好。他
大约不想让一川再喝,后者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这场球是德国对法国,一川看得兴奋不已。他是一个球迷,看起现场直播来理
应很激动。但德国和法国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和中国人一起看
球,和袁义和我一起看球,这才是关键所在。据袁义说,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川
25日到北京,27日离开,能在一起看两场球。球、祖国、朋友和酒,让一川兴奋得
一塌糊涂。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球迷,自觉没有祖国(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对朋友
我热情不足。酒,能喝一点,但从来不会过量。但是我也很兴奋,那是因为一川,
他的兴奋不得不感染你。他一面兴奋,一面还诉说着让他兴奋的理由。这就使我觉
得,自己也是爱足球、爱祖国、朋友和酒的。
我突然想到,房间的冰柜里还有啤酒。于是通通取出来,一共四罐。四罐啤酒
一川喝了三罐,我喝了一罐。我们不停地说话,时而鼓掌欢呼(随着球场的气氛)。
袁义夫妇那边则始终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