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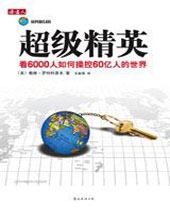



![[hp]我与蛇院有个约会 作者:女狼当道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2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