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如何估价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呢?关于美,是否存在独立的客观评判标准呢?美,从它的定义来说,就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吗?是否真的存在“美”这样一种客观的属性,正如“绿”或“好”那样呢?知识,同样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件事实的研究与思索都同样有益呢?——比如说,数清一堆沙子的颗粒数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极力否认这样的观点,即有用的知识比无用的知识更可取。然而我们又不无轻率地认为,存在一种是否“有趣”的内在品质——这可能与“绿”、“善”和“美”这几个概念不相干——而探索那些有趣的知识比探索那些无趣的知识更有意义。假定“重要”与“有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重要”就成为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修饰语。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最爱谈论的话题上来,是短暂而热烈的爱更美好呢,还是持久而平淡的爱更美好呢?我们也许倾向于前者。然而,在作了这么多的质疑之后,我们已然清楚的是:衡量这一切是何其困难。
这都是受了摩尔的方法的影响。根据这种方法,你可以通过使用精确的语言和提出准确的问题使基本上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这是借助于完善的语法工具和清楚的语汇来发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在反复的询问下,如果你没能确切地表达出任何事情,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言之无物。这是辩证法中的一种严格的训练,但实际上这又是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格的力量远比思维的精细有价值得多。在他的巨著的序言中,透过许许多多的斜体字,那些了解他的读者们就会听到他那激烈的措词,这一点就像是维多利亚女王。摩尔一开篇就指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急于回答问题,而不事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含义,我想,回答问题的种种理由也就变得简单而明白了。”所以,让我们先来花时间搞清楚我们所问的问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只要我们是在确切地提问,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摩尔正是这样做的。在有关“理想”的那著名的一章中,他写道:“实际上,一旦对问题的含义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其概略的答案就会显而易见了,从而似乎有成为陈辞滥调的危险。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极有价值的事物,就是一定的意识状态;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人类交流的快乐和欣赏美的客体的快乐。任何一个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的人,也许绝不会怀疑:对个人的爱和对艺术品或自然美的欣赏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哪些事物是单单因其本身的缘故就值得拥有,那么任何人似乎也不可能认为:除了包括在这两大项目之内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几乎具有同样巨大的价值。”
接下来就是快乐问题。当时间渐渐指向20世纪初,我想我们对快乐问题有点犹豫不决了。然而,在我们的全盛时期,快乐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我以为,如果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只不过是一个人快乐而一个人痛苦,那么关于前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有机整体性的原则却不允许我这样做。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虽然不完全是来自于《伦理学原理》),快乐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总的说来,快乐的精神状态总让人怀疑是否缺乏深沉的感情。
那时候,×还没有对女人产生兴趣,伍尔夫也还没有喜欢恶作剧,他们还都不像今天这样快快乐乐。他们两人总是呆在黑黢黢的屋里,面对面坐在火炉旁的柳条椅里,一言不发,不抽烟斗的时候,就喃喃自语:良好的精神状态总是极其痛苦的,而痛苦的精神状态则是无比幸福的。斯特雷奇也支持他们——他在自己的第二个童年里才开始享受快乐——尽管他并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总是郁郁寡欢而只是时时感到忧伤。而谢泼德和我则总是沉溺于欢乐之中,为此我们颇受羞辱。一天晚上,我们变得不服管教,鲁莽地坚持认为,快乐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结果他们作出结论:与三一学院的肃穆相反,这种低级趣味正是皇家学院独有的特点。这可真是个可怕的晚上。
苏格拉底曾奉劝普罗塔库斯说,纯粹的享乐是荒谬的。摩尔则把快乐仅仅看作是其他美好事物的点缀。但摩尔痛恨罪恶,他在自己的信仰中设下了不可宽恕的惩罚。“快乐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益处的,而且会招致罪恶……对一个精神状态恶劣的人,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那么就应该使其经受痛苦而不是宽恕他。至于这会不会产生好的结果,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请注意“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这一限定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拥有一个仁慈的上帝。
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柏拉图的本质上的善;胜过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加尔文教派的远离快乐和名利;并且压制了像维特一样的种种忧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常带欢声笑语,我们非常自信,富有优越感,鄙视群氓。但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良知所能始终维持下去的。当麦卡锡来度周末的时候,他就会温情脉脉地微笑着邀请摩尔到钢琴边来演唱他的德国浪漫曲,我们一起感受这美好的精神状态。或者鼓动鲍勃·特里维作一次蹩脚的演说,来滑稽而狂乱地模仿一些人物,其中的乐趣在于,你无法确定哪些是鲍勃自己的表演,哪些是他在模仿别人。
回首往事之时,看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成长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不再算计和衡量、不再问自己的所知所感,但我仍然认为我们的信仰更接近于真理,它把那些无关的问题抛在一边,它也不包含任何的羞耻心理。它所带来的纯净而美妙的氛围远远胜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因而,它仍然是我内心的信仰。上个星期,我又重读了摩尔关于“理想”的那著名一章。他试图确定生活中的行为品质和生活的总体模式,而这些都被人们大大淡忘了。他沉浸于一种无限的喜悦之中。他把自己的独特情感转化为抽象语言的方式是多么富有魅力、多么令人惊喜啊。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段落呢?如果一个人更注重精神品质,那么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否应该看重美貌呢?他的结论是,美貌要略胜于“精神品质”一筹。这个段落如此曼妙,我且毕恭毕敬地引述于下:“我认为,可以承认:在这种热爱最有价值的场合,对各个精神品质的鉴赏必定构成其中的一大部分;而这部分的出现使得整体的价值远远超过没有这部分时的情形。但是,这种鉴赏本身所能具有的价值,是否同这样一个整体,即这种鉴赏和对上述各个精神品质的恰当的有形表现之鉴赏结合而成的整体所具有的价值相等,这似乎是大大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就有价值的热爱之一切实例而言,品性之有形表现,无论见之于仪表,或见之于言词,或见之于行为,确实都构成所热爱的客体之部分;而整个状态包含这些表现这一事实,显然使其价值有所提高。实际上,很难想象对各个单纯的,不伴随任何有形表现的精神品质到底是什么;而且,就我们能作出这种抽象而言,所考虑的整体无疑似乎会具有较小的价值。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可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的赞美是重要的,这主要在于这种赞美所属的整体胜过一个不具有这种赞美的整体,而不在于这种赞美本身具有任何巨大的内在价值。这种赞美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否同对单纯有形的美的鉴赏所具有的价值一样大,那就是说,对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东西的鉴赏,是否同单纯对美的东西的鉴赏同等有价值,这似乎是颇可怀疑的。
“而且,如果我们根据值得赞美的各个精神品质本身来考虑其本性,那么,很明显,对其正当的鉴赏包含对单纯物质美的另一种关系。值得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基本上确实在于对各个美客体的有感情的鉴赏,如果我们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话。因此,对其鉴赏将根本在于此种欣赏。实际上,对人物的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在于鉴赏其对别人的鉴赏。但是,不但就这个例子中所鉴赏的可能是单纯对美的东西的欣赏而言,而且就对一人物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包括对其有形表现的鉴赏而言,这里似乎都包括一种对物质美的关系。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的鉴赏,或者说,对爱的爱,确实是我们所知的最有价值的,并且远比单纯对美的爱更有价值;但是,只有把前者理解为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包括后者,我们才能承认这一点。”
与摩尔关于“理想”的一章比起来,《新约全书》不过是给政治家们看的手册。自柏拉图以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文字能与这一章相当。它甚至要胜过柏拉图,因为它从不耽于空想。它传达出了摩尔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识见的纯粹和饱含激情,他的从不空想和从不斧凿。有一次在梦中,摩尔把命题与桌子搞混了,但即使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也无法把爱、美与真同家具分开。在他看来,它们都同样地确实、稳固、实在、客观,它们的存在如同常识一般。
没有理由放弃《伦理学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觉,尽管与内容丰富多彩的经验事实相比,它显得过于局促。但它提供了一种与外部事件无关的经历,这是一种额外的惬意,虽然,对我们这些人乃至所有人来说,今天都已经不能安然地生活在个人主义之中,而这正是爱德华治下早期的杰出成就。
我距离D.H劳伦斯还相去甚远,也还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但现在我还不准备讨论这个主题。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的信仰当中的其他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个人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又当如何理解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
摩尔的著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区分作为精神属性的善和作为行为属性的公正。关于行为的一般法则,他也有所论述。他关于正确行为的可能性的理论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我把我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于研究这一课题。我的写作受到了来自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两方面的影响。然而对于该书的绝大部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还没有注意此书在这方面的特点,也还没有对它尽量加以运用。我们沉醉于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中,却还没有开始玩推断的游戏。我们生活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还没有接近他的《理想国》,更不用说他的《法律篇》了。
这使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已把享乐主义抛出窗外,又放弃了摩尔那些很成问题的利益计算,从而回到了现实中来。社会行为本身即是目标,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理想之外的悲哀的责任。不仅仅社会行为是如此,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权力、政治、成功、财富、野心都是如此,另外还有经济动机和经济标准,尽管这在我们的哲学中并不像那位做毫无意义的收藏的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看待得那样突出。因此,我们成了这一代人中最早,也许是唯一的摆脱了边沁传统的人。实际上,起码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没有把外部世界抛到九霄云外。我只不过是在反思早些年里,我们认为思索和交流应当排斥其他一切目的的想法。在这篇回忆录中,我并不准备解释为什么摆脱了边沁传统就是一大进步。不过,我的确认为,正是边沁主义传统在蚕食着现代文明,它应当对现今的道德败坏负责。我们过去总是把基督徒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似乎就是传统、保守和欺骗的代表。实际上,是把经济标准奉为圭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破坏着大众的理想。
不仅如此,正是从边沁传统的脱离,再加上我们始终不渝的个人主义哲学,使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避免了从边沁主义矫枉过正到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们没能保护我们的后辈们,也没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我们没有提出能与这种虚假的经济信仰相抗衡的东西。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所有我们这些人——还都能免于这种病毒的侵害。我们有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正如罗马教皇有他的最后避难所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但摩尔不仅仅在第五章“关于行为的伦理学”中讨论了行为的义务,即应当通过因果联系在未来的数个年代中创造出最大可能的善(这部分的讨论充满了谬误),而且还指出了个人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完全否认个人有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主张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经验和自制力正可以胜任这一切。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它,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正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拒斥那些传统的道德、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智慧。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是不道德的人。考察其后果就应该考虑其价值所在。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我们也不准备顺从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我逐渐意识到,这也许更像是俄国式的特点,总之英国不是这样的。这产生出了一种虽然有所隐藏但却普遍存在的自我怀疑,怀疑我们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怀疑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在,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它笼罩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相关的生活。现在,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就我自己来说,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是,并将永远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即使当我们完全正确之时,也往往会令人震惊。其中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看法的基础是薄弱的,它建立在一种先验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一错误却是灾难性的。
我说过,我们是最先摆脱边沁主义的人。但我们却是18世纪另一项异端邪说的坚定的继承者和拥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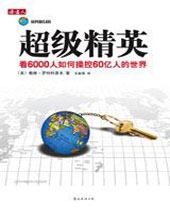



![[hp]我与蛇院有个约会 作者:女狼当道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2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