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已为这一场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侧光。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这种印象被强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脱离现实,充满着一切错误的怀疑。不过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尔先生的总结是公正的。
“美国对欧洲问题解决的强大、超然、善意的影响,是一种珍贵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冲突和半命令半纠缠的干涉中被浪费掉了。假如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埃德·乔治和克里孟梭团结一致,那么这三巨头的整体力量可能会在欧洲悲剧的广阔场景上施加以绝对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和他们的力量浪费在了冲突中,在冲突中他总是被打败。作为一位对手和纠错者,同那些能获得同志关系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遗憾、可怜。他本来会使每件事变得迅速而容易,他却使每件事变得更缓慢更困难了。他本来能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他却在精疲力竭和枝节横生的阶段默认了二流结局。”
“但是,作为船长,他使他的船沉没了。”
这部编年史结束了。人们翻过丘吉尔先生的第Z000页时,感觉如何?感谢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辩,和对作为所有我们这场战争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见的、了解的比我们更切近、更清楚——而写作。钦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对这一工作的智力兴趣和基本感情的强烈专注——这是他最好的素质。可能,还有一丝嫉妒,由于他的无可置疑的宣告:边界、种族、爱国心,甚至还有战争,如果需要的话,就是人类的终极真实;对他来说,它赋予事件以一种自负甚至高贯性,对其他人来说,则仅仅是梦魇般的间隔,应当永远避免的东西。
1929年3月
精英的聚会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当个人的和党派的裂痕——结束于阿斯奎思先生的辞职——将雷金纳德·麦克纳的内阁部长生涯推至终点时,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新职业。在这个职业上,他的卓越程度已开始变得不逊于在政治领域。
不过直到1925年这个国家遭受致命的损失为止,曾围绕阿斯奎思先生的那光荣班子的最富于冒险性又最富于建设性和持久性的智慧,由于离权力的宝座太遥远,难以对事件进程起决定性影响。从恢复黄金前的岁月到它在灾难中被抛弃,以及到更晚一些时候紧缩主义的声名狼藉,麦克纳以其他任何银行家未曾尝试的方式,使他这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变成了一个讲坛,从那儿指挥和训练着公众舆论。通过这种方法,他担任着信号的角色,创造那种新的公众意见,使那时显得不可一世的20年代正统犹如旧伦敦的雾一般消失了。在那些年月中,他是新观念的一位有力支持者,从这个城市一个不可挑战的位置上讲话。不过,他仅仅是作为一名教师而已,同实际上政策形成是相隔断的;直到灾祸发生后,他才能占据支配地位。
在发生着另一场战争的这个季节,我的思绪回到了1915年的财政部,以及他给予那些人——一些发现自己在为他工作的人——的重要友情和真诚接近。如今回忆起来很有趣,我本人与他的首次密切交往,是在1915年6月他访问奈斯期间。他访问的目的是对财政状况进行安排,在此基础上意大利将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自那以后,我就接触到了他自信、乐观、然而怀疑的思想——有时过于自信,过分乐观,过度怀疑,但总是热情投入到公众福利中去。在政治同僚们同他对阿斯奎斯先生坚定的忠诚之间的斗争,那时引起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分歧,以致一种始终一贯的战时财政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大的不幸。在战争期间,麦克纳习惯于因这一次对事务的处理比上一次好得多,而慷慨地为他的继任者祝贺。不过尤其在抛弃昂贵的货币和高利率时,他就像在危机时期应合适地做的那样,是亲自操作。
雷吉·麦克纳深爱看自己和睦的家庭,他的妻子从她母亲杰基尔女士那里,继承了最美好的传统,它不是英国富豪之户、而是中产之家的传统。女主人对他的客人们的真诚照拂,就像优雅的诗一般令人舒适。在闲谈中,在音乐和野外风光与气息的背景下,人们至少可以通过放弃劳作而奉守着安息日,即使战时也是如此。在芒斯埃德和梅尔斯,他这个久过单身汉生活的人体验着生活的温馨,他的儿子们正在茁壮成长。
1943年9月15日
精英的聚会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冈恩先生致力于推进高尔顿发明的富有吸引力的题目——搜集关于名人和准名人的遗传珍闻——这个题目,截然不同于对可确切决定的特征,如蓝眼睛、圆脑袋、六脚趾之类,科学地编制完整的家谱。他的方法,与高尔顿的方法类似.是依次逐一选取一定数目的相互区别的“血缘”,然后向我们展示:许多名人之间有着某种同族关系。
冈恩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血缘之一是毫不奇特的一个,但又并不至于陈腐得不值重复——德赖登、斯威夫特和霍勒斯·沃波尔的血缘关系。这三个人都是卡耐斯·阿什比和诺桑普顿·希雷之子约翰·德赖登的后代,迪安·斯威夫特是诗人约翰·德赖登的隔代远房表亲,霍勒斯·沃波尔是他的隔三代表亲(霍勒斯传自其母一方——因此不考虑其父系的问题——从德赖登的姨妈伊丽莎白)。冈恩先生想追踪这壮观的排列一直到最初的约翰·德赖堡的妻子——伊丽莎白·科普,伊拉兹马斯的朋友和拉尔夫·佛尼爵士之大孙女的孩子;她使许多其他人加入了同一个血缘,包括罗伯特·哈利。今天,有关这庞大的佛尼血缘关系的代表是奥托兰·莫雷尔女士。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记得奥托兰女士不仅传自佛尼,这位布匹商,而且传自威廉·皮尔庞特爵士(并通过他的妻子传自亨利七世的恩普森,制筛商恩普森的儿子),我们就建立了他同佛朗西斯·博蒙特、洛德·切斯特菲尔德和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女士的表亲关系。我们的族系失去了自己支脉的踪迹;我们不知道奥托兰自己是否知道她能称博蒙特、德赖登、斯威夫特、沃波尔、哈利和切斯特菲尔德为表亲。一脉相传?大概人们在血缘关系中,能察觉到一种特定的延续性元素?
冈恩先生对1515年捐躯于弗洛登菲尔德这个地方的约翰·里德的后代的分析,更为奇异,至少对当今作家而言如此。这里有一种杰出的多才多艺——也可能是一种平凡的素质?在18世纪,约翰·里德先生对博斯韦尔,历史学家罗伯特森,建筑师罗伯待·亚当和布鲁厄姆负有责任。在他的在世的后代中,有伯特兰·拉塞尔先生,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布鲁斯·洛克哈特先生,以及救世军将军布恩·塔克。
冈恩先生竭力表明,有多少著名的当代作家在他们的血脉中有着古老的血液。他提醒我们想起,G.M.教授和R.C.特里威廉先生以及罗斯·麦考利小姐是苏格兰高地人奥利·麦考利(并因此与T.B.麦考利血缘相近)的后代,关于其子肯尼思的著作,约翰逊博士写道:“除了关于自由与奴隶的某些浮夸外,写得相当好”;他提醒我们想起,休·沃波尔先生,利顿·斯特雷奇先生,康普顿·麦肯奇先生,莫里斯·巴林先生,以及(他确实应该添上)佛吉尼亚·伍尔夫夫人可以几代人要求殊荣;他提醒我们想起,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先生不仅是他祖父的孙子,而且是汉佛莱·沃德——马修·阿诺德的侄女——的外甥女。
要提到的还有所有族系中最杰出的——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从中传下了所有雄心勃勃的魅力之士,他们的面容和声音具有如此难以抵挡的强大魔力,是17世纪我们的君主们和此后议会民主政治的宠儿和娇女。在两百年中,恐怕不曾有一个内阁——或许要除去两任工党内阁——未包含乔治·维利尔斯和圣约翰爵士的后代,他们是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的两位乡绅,前者的儿子与后者的女儿结了婚。这两个家族的著名后裔实在太广泛而无法在此列举完。但一个简要的名单是会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金汉第一公爵,詹姆斯一世的红人;巴巴拉,卡斯尔曼女伯爵和克利夫兰女公爵,查尔斯二世的情妇;阿拉贝拉·丘吉尔,詹姆斯二世的情妇;伊丽莎白,奥克尼伯爵,威廉三世的情妇(斯威夫特称她为“他曾认识的最有智慧的女人”);白金汉第二公爵;洛德·罗彻斯特;洛德·桑威克;贝里克公爵;马尔伯勒公爵;格拉夫顿第三公爵(乔治三世的首相);两个皮茨;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查尔斯·汤森;洛德·卡斯尔雷;内皮尔一家;赫维一家;兰斯多恩一家;卡文迪什一家;德文希尔公爵;赫斯特·斯坦诺普女士;玛丽·沃思利·蒙塔古女士;菲尔丁,以及在很多有同一血缘的在世的当代人中,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法伦的怀康特·格雷。的确,这是英格兰真正的血缘王族。
我们将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如果我们都能追溯我们的族系,那么所有英国人将被发现在400年内是表亲?或者,特定的小“血缘”同其规模相比,能产生甚多的卓越人物,这是真的吗?冈恩先生没有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放下他的书后不带有后一结论的偏见,那他一定是位非常细心的、善于怀疑的读者。
精英的聚会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一位同代人评论该书说:“他用一种伴着沙沙杂音的唱机般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陈辞滥调。”我猜测是托洛茨基口授了这本书。它穿着英国外衣,出现在一条浊流之中,发出威吓的汩汩声;这是译自俄国的现代革命文学的特征。它对于我们的事务的武断腔调——关于我们的事务,甚至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也被他对正在谈论的无知事所障蔽——不可能使一位英国读者对它感兴趣。不过,存在一种与托洛茨基有关的特定风格。透过扭曲的中介物,可以看到人物性格。而且,它也不全是陈辞滥调。
首先,这本书是对英国工党官方领导者们的一个攻击,由于他们的“宗教情感”,由于他们认为: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同时不为革命作准备,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这或许是真的——我们的工党是激进的反传统者和博爱的资产者的直系后裔,没有丝毫的无神论、血气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满感情和智慧地发现,他们极缺乏同情心。可以选择一个简短段落来展示他的思想状态:
“工党领袖们的教条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拼凑,为适应于工会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调整……工党的自由党和半自由党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悲惨失误。”
“‘在感觉和意识的王国,’麦克唐纳宣称,‘在精神的王国,社会主义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些话立即暴露出资产者的慈善和自由党左派——它‘服务’于人民,从一个方面,或更真实地说从上面接近他们——的面目。这种方法的根源,整个存在于迷蒙的往昔,那时激进知识分子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与宗教文学一起,改良主义大概是最为无益的、在任何场合最令人厌恶的辞句发明形式……对胜利纪元的廉价乐观——明天似乎将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似乎又将比明天好一些——在韦伯、斯诺登、麦克唐纳和其他改良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这些大唱高调的权威们、学究们、骄子们和口吐狂言的懦夫们,系统地毒害工党运动,迷惑无产阶级的意识,麻痹他们的意志。改良者们,贸易同盟的保守党官僚们,在这个时刻代表着英国、可能也是世界发展中最为反革命的势力。改良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反战主义,是英帝国主义和欧洲——如果不说世界的话——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观点的集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些自我满足的书呆子,这些闪烁其辞的折衷主义者,这些热衷名利的人,这些穿资产阶级仆从制服的暴发户,必须向工人们现出原形。让他们现出原形,将意味着他们无可挽回的名声上的破坏。”
好,这就是那位严重警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绅士,在文章中发出的攻击。我们一定希望,这发自他内心的文章,感觉起来能更好些。请读者注意,只须变动很少的辞句,就可以便属于我的文章进入权利的哲学拳击。这种相似点的理由是明了的。在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态度,而非终极目标。他恰恰展示了强盗政治家团伙的脾气;对他们来讲,行动即意味着战争,他们被甜美的合理性、博爱、容忍和慈悲的气氛所激怒,在这种气氛中,尽管风在东方或南方呼啸,但鲍德温先生和洛德·奥克斯福德以及麦克唐纳先生却吸着和平的烟斗。“他们在不该有和平的地方吸着和平之烟,”“这是伪善,衰弱的蠢货的象征,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对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于毫不怜悯的斗争精神中。”只要事情是这么容易!只要人能够通过吼叫而取胜、无论他吼叫得像雄狮或一只舐食的鸽子!
咆哮占去了托洛茨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简要说明,值得给予较密切的注意。
第一个假说。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么历史进程就使得向社会主义彻底转变成为必要。“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败的威胁。”
第二个假说。难以想象,这种彻底转变能通过和平争论和自动投降而达到。除了以暴力进行答复外,统治阶级什么也不会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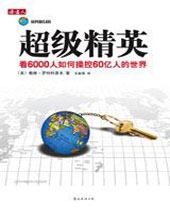



![[hp]我与蛇院有个约会 作者:女狼当道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2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