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道现在喜欢看电影的人还能不能理解“过路片”这个概念,意思是不可能公映或很久以后才公映的影片,突然在某影院临时放一两场,宛若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当时只要一听说有“过路片”要放,那是千方百计也要去看的。美国的《霹雳舞》和香港的《霹雳情》,我都是高三时逃课看的“过路片”。
毛片更是以过路片的形式在我们这些无立锥之地的穷学生中流传。
那是大一的下半学期,一次午饭后,一位大三的师兄说有盘毛片,只能在他手里留半天,问去谁家能看,咣咣提议去他家。他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旁边坐着几个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丢下,或怕我怀恨告密,他们扭脸邀请了我,这使得我对他俩终生都充满了感激,尽管人家觉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如今我的脑海中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在俗套的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的背景音乐下,九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北京蓝天白云下的街道上,要多快有多快。其中唯一一个不戴眼镜的人眼神最好,他警惕地四处扫视;一个膀大腰圆的人横眉立目地守侯在另一个人身边,单看那个被保护者两条跟穿了条毛裤一样的毛茸茸的小腿,就知道他是这帮人中小腿肌肉最发达的,他骑的也是一辆最好的车,以备有人盘问时一骑绝尘。
——他胸前的军挎里,硬硬的横亘着一盘毛片,毛片用报纸包着,又用《中国新闻事业史》跟《大学英语》两本书夹着。
说起来这么诗意,其实当局者迷,那天我就像做梦一样骑了十几公里赶到咣咣家,什么文学性的描述都是扯蛋,唯一的念头是,我就要看上毛片啦!
“这时,灯一黑……”
这是十几年前流行的那种花哨杂志里“警笛声声”类报告文学的惯用手法,套用到这里,用来描述我那次毛片处女观摩。至于片子的内容,看过的人不用我复述,没看过的人不宜我讲述,就算了吧。
幸运的是,我的第一次毛片观影经历还不至于太丢面子。首先,那盘带子的画质非常好,几乎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清晰度最高的毛录象。如果你看过那年头那种类似雪花一样画质的录象带,就会知道我能在自己的第一次摊上那么清楚的带子,简直是一种值得流泪的幸福。其次,我表现得还算镇定从容,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一块审片的都是平时经常探讨社会、哲学等严肃问题的伙伴,刚研究完叔本华舍斯托夫,又在这里肉帛相见,怎么着也得端着点儿;再说,如果表现得太过面瓜,会让别人看不起的,就跟时下一个女孩吹嘘自己失身如何之早一样,所以我就努力做出见多识广的样子,尽管内心紧张得不行,直想亮开嗓子嚎叫几声。
看到后来,重复的活塞运动再次开始时,我已经能让自己站起身来(此时裆部已不那么引人注意),走到书架旁观赏起咣咣家的藏书来。我看的是一本李洪林的《理论风云》,觉得很好,回学校就买了一本,珍藏至今。
我们屋老二就没这么轻松了。他性格内向,不属于江湖上混的人,所以大家有看毛片的机会也不叫他。等他终于放下架子求我们给他安排一次的时候,已经是大四。苦盼七年,其心也诚焉,其性也足焉。
记得那是一盘缩录的录象带,一百八十分钟长的带子录了七八个小时的节目,全是真刀真枪的干。我们这些老江湖看这些东西已经很稀松平常了,并且为了在老二面前显示自己的优势,故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间一度还有人囔囔没意思要换成魂斗罗,但老二端坐在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七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最后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国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轻人格外推崇法国的艺术片一样,法国人的毛片也显得那么卓尔不群。老二终于吐出一句:“这个……挺好。”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处女观摩结束后,我忍住求师兄将那带子重放一遍的欲望,万分留恋地从阿光家出来,两腿松软地走出楼门,心还留在那春光乍泻的活色生香中。我两眼模糊而又漠然地朝四周看看,感觉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男男女女都变得那么不真切,连太阳的颜色也和以前大不一般(此段仿严锋《好玩》一文)。
此时的我尽管还是童子身,但幸亏已约略知道男女间是怎么回事,否则,我坚信毛片对我的刺激将是致命的,不可想像的。
第一次知道人类的性生活常识是上初中时,我看到一本叫《家庭百科》的书,定价0。14元,封面是那时的当红影星陈冲,穿着一件鲜艳的毛衣,身傍花枝俏,胸前戴着“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校徽。书中大多是介绍如何去掉饭菜中的糊味儿之类的生活常识,但有一章是“夫妻性生活指南”,详细讲述了如何让性生活和谐,以及避孕怀孕的知识,看得我血脉贲张醍醐灌顶。
可惜这一章一共才有七页,其中具体的动作指南和场景描写只有两页,让人很不过瘾。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内容也是极保守的。但对于我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那么淫秽下流,那么见不得人。
我认为,如果一个年轻人知道人类的性活动是怎么回事儿以后,能够克服心理动荡依然尊重自己的父母,那就说明这人树立了正常的性观念。
从生到死只有一步
从死到生,却要走
很长很长的路
像我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成绩都是呱呱叫。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了能够把自己从小学顺利到达大学,我必须得把书上那些东西背得烂熟。至今我还记得《生理卫生》课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遗精”这道题的标准答案:一,树立远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宽松的内裤;四,不接触不良读物。如果真的按这个程序来执行,恐怕我的小鸡鸡永远都长不大。
一边背诵着标准答案,一边背叛着标准答案,这就是我们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多么凶险的成长。后怕之余,也对误人生理的《生理卫生》课有了腹诽之情。如果我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一定罚那个教材编写者,让他的脑子里只能思考数理化,累死才能睡觉,说梦话都得用英语,并且只能穿大裤衩,裤裆里宽松得能跑六匹马,看他跑不跑马。
娘的。
从那天以后,《乡村骑士》间奏曲便屡次在我少年的心中响起。那时的北京,没有交通堵塞,没有盗版碟片,没有桑拿小姐,没有网吧酒吧,只有春季漫天的风沙,冬天刺骨的寒风,和一年四季暗潮涌动的毛片。
如今我经常像游魂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逡巡,每当经过一个当年曾潜入看毛片的地段,便会涌起一阵熟悉的暖意,同时会惊讶这么曲折的地方当年竟能执着地找到。
我们的父母们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们的家中有什么在上演吗?
是未来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性成熟。
如今我所在的单位正在搞ISO质量认证工作,我对这一工作非常拥护。只要当年看过毛片的人,都知道制订一个规范的质量标准是多么重要。有多少次,辛辛苦苦情绪饱满地赶到某人的家中,结果发现手中的录象带是NTSC制,而他家的录相机只能看PAL制,或那盘录象带是缩录的超长版本,而他家的录相机也看不了,一腔酝酿好的邪火难以发泄,那个急啊,恨不得罚那孙子立马脱衣服来一段现场秀。
因为难得,所以珍惜,哥几个都是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毛片生涯中。有一天,老蔡一天内连赶三个场子,把同一部毛片连看三次。最后一遍结束后,老蔡脸色发绿地跟哥几个倦鸟知归,320路公共汽车到农业科学院一站时,大伙把他往车下推:“你到站了,快下去快下去。”
“这是农科院啊。”
“是啊,你不是在农科院接受研究吗?”
“研究?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老蔡的脸上焕发出骄傲的羞怯。
“这里的大牲口研究所正在研究你,为什么能跟个大牲口似的性欲旺盛?”
高中时我们在熄灯后的床上畅谈人生理想,有人胸无大志地说是痛痛快快打个喷嚏,有人色迷迷地说是被若干美女轮奸。这种淫贱的理想一说出口,顿时博得满宿舍淫贱的笑声,想得真美。
有机会看到毛片后,一帮小光棍全在性幻想方面未成曲调先有情,个个精力弥漫,冲劲十足,哪口最荤就爱哪口。如今,那帮孩子都已人到中年,却是能不依赖伟哥就不错了,再提起当年的生龙活虎和冒险精神,真是性欲已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
青春啊青春,一定要用最残暴的手法给自己干掉,因为荷尔蒙旺盛的那段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
一个小兄弟跟我说,他最思春的时候,只要看到带女字旁的汉字,都要产生性冲动。他是中文系的,难怪对文字敏感。而我呢?第一次出最远的门去广州,先找了家影院看《老娘够骚》。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翻《羊城晚报》,最眼馋的就是中缝的影剧预告,《老娘够骚》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广州人简直是生活在天堂,结果……从此我恨死了那些爱给片子取个哗众取宠名字的片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喜欢过杜可风。去你的《堕落天使》,去你的《花样年华》,谁让你该够骚时不够骚?
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黄舒骏唱道。
后来跟一个哥们探讨人生,他提出一个论调:古代为什么能出那么多通天地之变晓古今之事的大学问家?是因为他们很早就结婚,不用再为性问题而苦恼压抑,就把一门心思都用在治学上了。仔细想来,确有道理。
现代人性成熟得早了,结婚反倒晚了。整天憋得嗷嗷叫,这当口还能读点儿正经书,简直是在虎口夺食,太不容易了。
向晚婚时代的大学问家致敬,致敬,再致敬。
看毛片的另一种乐趣来自那种禁忌的快感。看毛片的罪恶感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我们的心灵土壤,只要小鸡鸡一硬就觉得谁都对不起就该天诛地灭,就恨不得一盆凉水浇灭自己的欲火,但又管不住自己,欲火仍熊熊。用句文雅点儿的话是,天人交战。
姜文初识啼声的《末代皇后》中,婉容(潘虹饰)平静地用白嫩的玉指按熄汤汤水水的红烛。这个镜头搁到符号学解构学那里,就是最直白的性压抑。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色情片的出口创汇远远高于好莱坞的那些所谓大片,这就说明全世界的人民都离不开毛片。好像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不渴而饮、四季性交。
而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象、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算计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才犯了罪。要按这种逻辑,犯罪的人百分之百长有生殖器,那是不是给这世上的人都咔嚓一刀就此了账?再者说了,那些罪犯没准儿还看《简爱》呢。
一个人引人注目之后,关于他可以有很多定语,比如说那个残害黑熊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心智发展不健全的人、一个没有爱心的畜生、一个清华大学机电系的学生、一个喜欢上网的人,或者就说是一个穿四十二码鞋的人,都行,偏偏我们会把清华大学学生这一身份与残害黑熊这件事儿联系在一起,不知是瞎了眼了犯了贱了还是别有用心。倘若那哥们是淮南煤矿师范学校的学生,恐怕这一身份就没人提起。
毛片也是这样。比如一个进行了性犯罪的人,他也可以有很多身份,如一个荷尔蒙分泌过量的人、一个性欲战胜理智的人、一个蔑视人类道德法律准则的人、一个不知道他母亲姐妹也是女人的人等等,偏偏我们会说他是一个看了毛片才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于是毛片就跟这哥们一块被判了刑。
毛片啊,你替多少做了坏事又不敢担当的人背着沉重的黑锅?
中国超超白金的流行歌手张蔷在她独步歌坛的八十年代出版了一盘又一盘口水歌,其中有一首叫《快乐的星期天》,以一个快乐无邪的小女孩口吻唱道,她和她的妈眯在星期天“逛逛百货公司,又去看场电影,跑到公园遛遛,再去吃点儿东西”,于是“惹得我笑眯眯”。
瞧人家这礼拜天过的。
我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议论说人家的那些周末活动真是人生的几大美事,而我们的人生美事儿是什么呢?过不成还不让憧憬一下啊?想来想去,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还要有足够的烟抽)、看毛片(看毛片的时候最好是图象清晰没人打扰)肯定是其中之二。
大学四年,观摩毛片十几次,都是集体活动。每次看到那些北京同学把一盘路过时间比较长的毛片揣到怀里说要带回家独自享用,都让我们为自己不是北京人而自卑。
这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情是让人民总得听张俊以的歌,比这更不人道的事儿就是让年轻人必须得扎堆看毛茸茸的片。
后来看《白头神探》中的某一集,白头翁莱斯利?尼尔森兴致勃勃地借回家几盘毛片,准备跟娇妻(他老婆真是个粉雕玉琢般的美人)欢渡周末。这段情节令我眼界大开,才知道夫妻生活也可以有这种过法。结果好事多磨,他的如意算盘被同事搅了,被叫去执行任务,那些毛片春心寂寞地摊在床上。我比白头翁更恨那个同事。
那人由棒球明星辛普森客串。后来这小子犯了案子,进了局子,这个消息把我乐坏了:“我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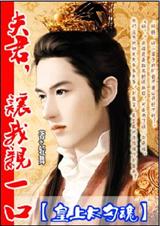
![天凉了,让总裁吃药吧[那个童话故事]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1/21688.jpg)
![[耽美]天凉了,让总裁吃药吧[那个童话故事]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3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