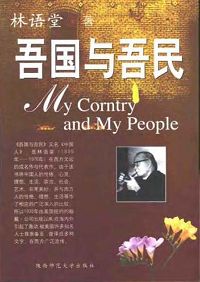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作者:胡辛-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蒋经国恼了:“你——胡说些什么呀?”
“好,我不说。请你仔细看看这份调查材料。”
蒋经国疑惑地接过一叠装订好的材料纸,翻开“封面”,第一页却没有被调查者的姓名。
“1913年春南昌佑营街一书香之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女求学于美国教会创办的宝苓女中,生性活泼,天资聪慧,尤以国文、音乐独领风骚,善唱京剧,爱打篮球,有‘布谷鸟’之称。但思想激进,北伐期间,上街宣传慰劳荣军很是活跃。毕业后仍与激进分子有过交往,曾往狱中探望过……”
他捏着材料纸的手颤抖了。他愤怒他恐惧,他当然知道被调查者是谁!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这个克格勃竟瞒着他对他衷情的女人作秘密调查!他两眼射出寒光,材料纸往茶几上一撂:“谁叫你这么干的?!”
“为了你。”黄中美迎着他的寒光,毫不恐慌,坦然答道。
“胡扯!”他气恼,奇怪的是愤怒竟消退下来。平心而论,黄中美是赤诚忠于他的,而且这位训练有素的克格勃高手,对“她”的调查会是客观的翔实的细致入微的,唉,将“她”的过去“抖出”这使他太难堪!无论如何他得护卫她:“她不是日伪间谍,不是共产党,不是走私犯,你对她刨根究底,就是侵犯人权,就是,哼,卑鄙。”
语言硬语气却不硬。
“卑鄙?”黄中美淡淡一笑:“对你隐瞒了一切的女人怕称不上高洁吧?蒙在鼓中者被人欺骗被人利用,不知人权受到侵犯否?”
“你说谁?!”他勃然大怒,脸色憋涨成紫酱色。这个克各勃在嘲笑他是个被人愚弄的大傻瓜!
黄中美故意装傻:“说谁?或许你确实不知被查者是谁,或许你已猜测到是谁,这并不重要。第一页材料无损她的‘高洁’形象,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她的全部过去,请你把材料看完,那时你自有定夺,什么话也是多余的了。当然,你不用紧张,与政治没啥大关系,是……名声。可这对女人来说至关重要(口伐)。”
蒋经国不由得腾升起反感,他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喋喋不休指手划脚!他得给予反击:“你太自信太武断了。我告诉你——她早告诉了我她的一切、点点滴滴。”
黄中美笑了:“这不可能。她没有这个勇气,更没有这个胆量。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她将自己包裹,不,包装得很好,美丽的凌霄花攀缠上大树,也可凌霄嘛。”
蒋经国直视着他:“她结过婚,上有婆母,下有一双儿子,可丈夫死了,对吗?”
黄中美的喉节上下骨碌,艰难地吞了口唾沫:“可你……你知道她丈夫怎么死的吗?”
“是自杀。因为不能容忍却又无奈妻子的自立。”
“你错了!是因为郭礼伯的插足!她是郭礼伯的小妾!郭礼伯这回领头发难,就是为了报私仇(口伐)。”
“纸怎能包得住火呢?如果她真是大师长的小妾,大师长又何苦转弯抹角、羞羞答答找借口发难呢?”
黄中美一时语塞。
“你这位一向严谨缜密的特工,为什么要模糊实质刻意制造时间差呢?不错,她还是位天真的女学生时,在慰劳军人的活动中认识了比她大十几岁的军官郭礼伯,北伐战争的巨大影响,哪个女孩子不崇敬仰视黄埔军校生呢?以后的寥寥交往亦不过如此,平心而论,郭礼伯也是要面子的人,不至于下作到急不可待地插足。她新寡后,郭礼伯起了心,要强纳她为小妾,她不甘沉沦,抗争不过,只有逃避。她是个自立自强的女子,可终究是弱女子。一个女子为了逃避强权的纠缠也成了罪过?强权者泼在弱女子身上的脏水在你眼中也成了女子本身无法洗刷的污点?这太不公平了!”
原作好了充分准备的黄中美反倒猝不及防!始料未及!他原以为苦心搜集的材料能在这个切口上震惊专员迷途知返,现在倒好,他成了专员情理交融滔滔恢宏演说的听者!看来坠入情河的男女硬是执迷不悟呵。好一会他才嗫嚅着:“这种男女间的事体总是理不清坏名声……”
“请你不要再往她身上泼脏水了,老大哥,泼脏了她,也就是泼脏了我。”
黄中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失败了,垂头丧气立起,却终是忠诚:“这电文,你如何处理呢?”
“容我仔细考虑再定。”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二二 “你也想对她雪上加霜?!”
二二 “你也想对她雪上加霜?!”
“你还没睡?”蒋经国蹑手蹑脚进到卧室,却见黑暗中一对猫眼绿绿蓝蓝的幽光直盯着他,他吓了一跳,哦,是芬娜。于是不无歉意地问了一句。
他行踪不定。桂林重庆、县城山乡辗转不息,即便在赣州城,他也习惯白天察访,晚上在专署办公室处理机要批阅文件,妻子已习惯夜间的等待。太晚了,她会打个电话去公署催问,怕他熬坏了身体;她这里做好了从婆母那学来的宁波汤圆或煨好土芋艿,边编织毛衣边等着经国回来吃夜宵。有时等着等着太乏了,她和衣歪在沙发上,经国回来会悄悄地将她抱上床,她醒了却仍假装睡着,让经国轻轻地给她脱鞋盖被,让幸福的温情荡漾心头。可今夜,没有了温馨。
蒋经揿亮台灯——芬娜哭过!眼圈红红鼻头红红,往常梳理得极有条理的发髻散了,乱蓬蓬搭拉肩头胸前,一件宽大的白色俄罗斯睡袍套着她,她像装在面粉袋中。
“怎么啦?”他吃惊了。打来到中国后,芬娜想念过她的祖国她的家乡,也曾从梦中哭醒,喊着她的乌拉山,可眼光从来不曾这样——忧怨中夹杂着几分凶狠!他这才想起:有些日子了,她似乎神不守舍,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今夜也未给他挂电话,难道……
如果是往常,他一定会说上一、两个笑话,惹得她忍俊不禁,然后一起品尝土芋艿,回顾当年的主菜洋芋艿,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
可此刻,他不能也不愿。与黄中美的一席谈,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另一个女子身上:他懒懒地脱去外衣、鞋子一踢,往床上倒下,双手枕头,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她没想到他会这样漠然视之,委屈得又啜泣起来。
他烦恼极了,一跃而起:“什么事?你直说得了。”
他竟然不同青红皂白,反倒叱责她,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得更响。
躺下、跃起、跃起、躺下……他重复着同一句话,硬梆梆的,没有一丝温情。最后他颓然躺下,拉过枕头压住了额头眼睛。
她于是忍住了哭泣,她得问个明白:“你……你那块苏联表呢?”
他不吭声,也不动弹。
“哦,你和她……她……究竟怎么回事?你把表……给了她?哦。”
他无动于衷。
“你……爱她?哦,你爱她!”
她摇撼他,他岿然不动。
她无法忍受!她疯了般掀掉那该死的枕头,他的眼睛竟是大大地睁着——目光是这样地镇静和冷峻。
他缓缓地坐起、立起,他与她僵僵地对峙着,她应该扑到他宽厚的肩头上,可是她不能!他的目光没有退让没有求饶甚至没有一丝和解的意愿!
良久,他开口了:“你——你也想对她雪上加霜?!”
天!他坦然地完全维护着“她”!
芬娜跌坐在地上:“我真傻,我早应该知道,你爱她!我却在虚假中生活,哦,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不想,也不能够……”心碎的她不知不觉中改用母语倾诉。
“那你——想怎么办?”他已经扭转身子,面向墙壁发问,声调干巴巴的,与其说问妻子,不如说问自己。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忍受没有真诚没有爱的生活……你不爱我了……你心里没有我了……你爱的是她……我真傻、真傻……”
他心烦意乱。外患内忧,骤然爆发于一夜,紧逼着他作出抉择。
悲痛欲绝的芬娜却绝望地喊了起来:“我真傻!你那时是多么爱我!啊,你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全忘了!你忘了乌拉山,忘了白桦林……”
……他跺着脚在白桦林中等待。
唉,爱情来得晚了点,他已经二十五岁!
虽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
今天,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她已来到他的身边,她羞涩又热烈地看着他,他什么也来不及做来不及说时,她已扑进她的胸怀:“我爱你——尼古拉!”
他热烈地拥抱她、亲吻她。在他在她,都是颤栗魂灵的第一次——真正的初恋。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很快有了第一个宝贝——儿子爱伦。然而很快他得到突如其来的回国通知!
他不能割舍芬娜和孩子。回国前他曾惴惴不安地问驻苏大使:“我已结婚,娶的是苏联姑娘,我父亲不会介意吧?”得到肯定的许诺,他才放下心。
他珍惜这初恋。他的急切的初恋包含着太深刻太沉重的内涵:融汇着他对祖国对故乡对母亲的相思,糅和着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的真诚,躁动着积蓄太久的青春的思渴和人的本能的冲动。
或许,正因为这初恋内涵太厚重,反而冲淡甚至混淆了爱的本身。他爱她吗?他爱过吗?这就是爱情?这,在当时无关紧要,甚至毫无意义。
然而,赣江之滨另一个“她”走进他的生命后,在比较鉴别中,那过去潜藏的遗憾越来越清晰了……
他慢慢地回转身,看着哭得瘫软的妻子,他的心软了,他有负于妻!
她却没有读懂他的目光,她突然用俄语绝望地喊叫起来:
“结束!结束这一切!我要回国!明天就回!带着爱伦爱丽——回国!”
五雷轰顶!她在进攻他!威胁他!这在他是决不能容忍的,他得发泄他满心的愤恨!他目光散乱无目的地到处搜寻——小圆桌上放着一尊石膏像:长翅膀的瞎眼男孩丘比特拿着弓箭茫然地对着他。他冲了过去,用力掀翻圆桌,石膏像摔得粉碎,巨大清脆的撞击声震撼静悄悄的花园塘,还有一声狂怒的咆哮:“滚—”
这在花园塘的蒋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都吓醒了,可谁也不敢去探问。姚夫人只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蒋方良惊呆了,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她很难相信这头狂怒的雄狮就是以往的好丈夫好爸爸!赣南人民心中的“蒋青天”!
晨曦中,蒋方良带着爱伦爱丽离开了花园塘。
蒋经国没有挽留也没有送别。
都觉得忍无可忍,超过了极限。
不过,蒋方良没有回苏联,而是去了贡水东北面的虎岗。蒋经国将长岗更名为虎岗,并在那里筹建新中国儿童新村。蒋方良亦是负责人之一,她的离家并未在赣州城搅起轩然大波,都以为她一心为了工作。
送他们去虎岗的车子倒是蒋经国派的,妻子和儿女毕竟还在他的心中占据着。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二三 对未了的“见面”一次公开的了解
二三 对未了的“见面”一次公开的了解
蒋太子来南康赔情罗!
蒋专员到南塘乡认错罗!
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庇尔克轿车几乎被人群簇拥着驶进坪上,捱近祠堂大门口方稳稳刹住,蒋专员陪着披红挂彩的军官温忠韶出了轿车。温军官钻出车门便急不可待向密匝匝看热闹的老(亻表)抱拳致意,风光得像凯旋而归的英雄。
蒋经国却迈上台阶,转身向老(亻表)们笑容可鞠地点头致意,刹那间像风掠过水面,老(亻表)们叽喳一片:“蒋专员就是青天老爷呵!”“是吔,知错认错的大官有几个嘛?”“算不得嘛咯错,催交公粮也是为公啊。”“替乡长受过啊。”
蒋经国变为主角,先赢一筹。
台阶上还立着几位态度傲然的军官,他们是赶来声援温军官的本籍军官代表,见此场面便有几分不是滋味;蒋经国却分外热情,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尔后步入祠堂。里边已摆好几桌丰盛的酒宴,县里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县政府的代表也都到齐,县长因劳累吐血不止在赣州住院,本挣扎着要来,蒋经国不让:“天塌不下来的,相信你这模范县的群众基础嘛。”果然,“开幕式”蛮精彩。
当然,蒋经国认出了军官代表中的一位,正是去年暮春在通天岩旁的凉亭中遇见者。那军官背着一架相机,却没有抢拍镜头,只是怔怔地张大嘴——蒋经国的随员中有位女的,正是章亚若小姐!
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蒋经国针锋相对郭师长的发难,迎头痛击之?军官发了一会愣,只得阴恻恻入席,拍照片的兴致全然没有了。就怕拍回去交给郭师长,他会恨得将嘴里的金牙都咬碎吧。
蒋经国已端起了酒碗,竟有一篇洋洋洒洒情理交融的祝酒辞:
“父老乡亲们!各位军官代表们!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从上至下,包括我这个专员在内,都是民众的公仆,是替你们办事的。公仆中有人态度野蛮,这是错的,不论是对军官还是对老百姓,都不能这样。我身为专员,教育不好,责任由我负,我理应来这里向大家认错赔情。这第一碗酒,为温军官压惊,你受了委屈,我向你诚恳道歉。”
一饮而尽,掌声雷动。温军官就有些头重脚轻,搅不清是挣足了面子还是面皮全给扒拉掉了。
“……这第二碗酒,为军民的团结,干!”
军官们端起酒碗干时,眼中便有了些许歉意,平心而论,对出征军人家属——老人可送百寿堂、子女可免费受教育、疾病可免费就诊……称得上“无微不至”关怀了。
“……这第三碗酒,献给积极完成征购任务的父老乡亲!你们是赣南新经济建设的保证!”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碰杯。温军官们就有“吃了闷棍”之感,挣回来的面子又失掉了,人家都努力完成征购任务,你搅乎什么呢?
蒋经国就是蒋经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