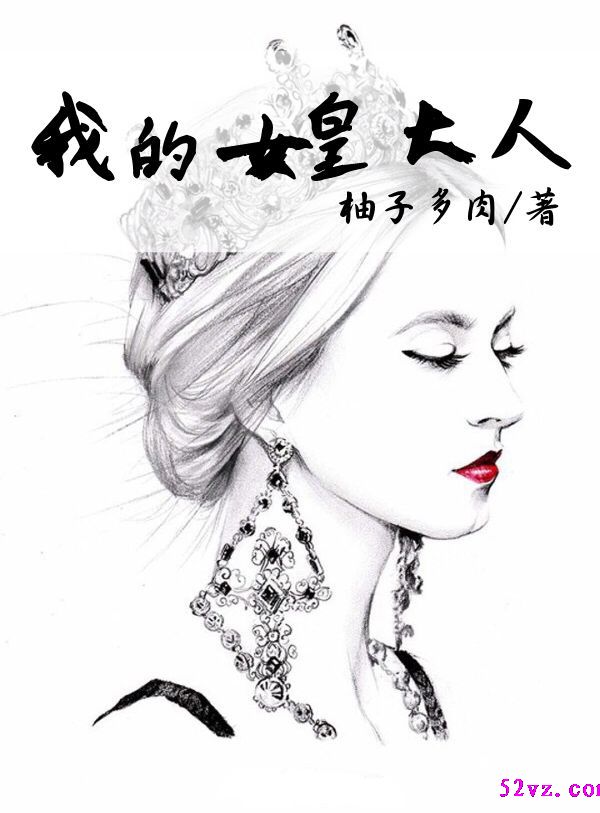4痴人 -王朔-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
一树桃花粉了。从我们这幢孤零零拔地而起的办公楼往下望去,四周皆是低矮环列的青玉平尺,鱼鳞般的瓦脊叠错接搭,犹如微澜初兴便凝住的汪洋大海。
稀稀落落的街树、院树枝桠高山房顶,放眼跳去一簇簇枯干着,唯有天际一隅一树桃花粉盈盈,远远地鲜艳醒目。桃花尚未盛歹,蓬散为一伞,只枝枝布满花蕾,扇骨般翘直,宛古一捧瓶嫩润花,被一只巨手设于天地间,供天眼俯瞰观赏。
在我们这些终年见惯北方冬春之际萧瑟景象,熟谙四季交替规律的人看来,这花委实有些不合节令。
我是偶一登高回首方看到这一株寂寞的花的。
二
当时我正在和同事们边吃着食堂的包子边玩牌。阳光晃着人眼,办公室里暖洋洋,笑语喧喧。我摸了手好牌,举起来给站在我身后的阮琳看。
他进来了,由五短身材、赔了一辈子笑、笑出一脸皱纹的科长领着。谁也没注意他,就连科长大声宣布“这是咱们科新来的同志”后,大家也只是略抬了一下头,继续埋头吃饭、聊天、打牌。我听到科长说的我的名字,让他以就后就跟着我工作,大概他还指了指我告诉新来的那就是你“师傅”。我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生发现他正看着我。我低头看片,旋即再次抬起头,他正凝视着我时不是每个人不都有非凡的相貌的,我也算阅人较广,但我每每发现那些号称不凡或已经不凡的人大都长着一张粗俗平庸的脸,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简直连一眼也没一要然瞧他。有些名望很高的人往往就因为粗暴委琐的相貌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我可头在没法对他无动于衷。他形似骷髅,大大的眼睛占据了部分头和脸颊,那几乎是仅由一双眼睛构成的脸,我不敢说他没有表情肌,即使有也没什么用,他的眼睛完全可以替代它,实际上的眼睛几乎可以替代所有五官的作用,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功能的器官,那不是眼睛,那一一部组合,人怎么可能长成这副样子?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自己全身照,不过有三只手,我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阮琳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倾肩让其滑掉。“你叫什么来着?”上班铃响后,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他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他,并竭力不去看他的眼睛。“司徒聪。”“噢,我叫司马灵——不不,不和您逗趣儿,真是叫这个名字。”我听到全办公室的人的低低笑声,解释道。“你知道谁叫什么名子自个没法作主。父母一朝不慎,真能叫他作儿女的羞愧终生。”“哪里,你的名字很好听”他微笑。
“是吗,哪我踏实多了。嗯,咱们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工作,不过意义很深远。你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喽?对对,只许开花不许结果。我们干的就是统计每个月咱们市少结了多少果,具体数字是从当月本市发的各种式样的工具体数相加得来。”“这个数一定很大吧?”他貌似好奇。
“很大,数以百万计。当然这里一多半也许本来就是无功用,但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无法打折扣。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非得从一开始加,实际上这个数是现成的,我们只需给医药公司打了电话问一下他们的进货量就可以。这种东西总是进多少销多少,一方面需大于供,一方面因为免费……”我忽然没了讲述的兴趣——他的眼睛越过了我,射向我身后的阮琳。“其实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到时候你一看就会——笨蛋都会。”他重又看我。“是呵这工作有些无聊。不过你要这么一想:无聊的工作也得有人干,也就坦然了。”
“我一点没觉着屈才。”他心不在焉地说“我也是来自人民。”
三
“这个人挺有意思是不是?”下班后,我们拥到走廊里,在楼下走,阮琳在人群中问我。
“哪个,你说的是谁?”我磕头草似地边走边到其他科室的熟人点头致意,“谁挺有意思?”“哪个来自人民的家伙。得了,别假装漫不经心了,你看他看得眼睛快直起来了。”
“我一般不太注意男人。”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过去?”
司徒聪走在我们身后的人注中,比别人高出半个头,眼睛垂着。一出楼门我就拉阮琳钻进路边的牛奶店,看着司徒聪从窗外走过去,才出来到街上继续往前走。
“别对他那么感兴趣。”我对阮琳说,“这种人我见多了,刻意显得不凡以期引起别人注意,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哪怕他暗示你他暗示你他杀过人你也别露出惊讶。”“我没想理他,我对他一点也不感光趣,我一点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凡,相反我倒觉他很俗气。”
“就是,摆架子绷块儿谁不会?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不表现自己,总是默默无闻。”“譬如你。”阮琳笑着瞅我。
四
第二天,我一迈进办公室就看到阮琳坐在我的座位上和左右司徒聪脸对脸地说话,双方微笑着,低声细语,十分愉快。“是呵”我干笑着对他们说。
“是。”阮琳回头对我一笑,又继续扭头和司徒聪说话。“你到我们这个单位来真是可惜了,迷儿特没劲,人也没劲。”
朱秀芬满面通红地拖着地板,从那头拖到这头,我侧身给她让开:“今儿你值儿?”
“嗯。”朱秀芬抬起虽已不年轻,但仍油光锃亮的脸,“帮着擦擦灰。劳架。”我拿起门后暖气管子上的一大堆破抹布去水房浇湿,朱秀芬拎着拖把也来水房涮,开着水龙头哗哗冲时偏过头来对我说:“瞧见那一对儿了长?一大氙就来了聊到现在。”
“你管呢大地”我认真洗着抹布,“年轻人的自己爱好。”
“哼。”朱秀芬用力叉拖把,“来个男的她准第一个凑上去,涎着脸,真叫人看不惯。”“我觉得挺正常,小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谁派她了?”我拿着抹布回到办公室,司徒聪和阮琳还在说话,我开始挨个办公桌仔细地擦瓜熟蒂落。
“你说是不是嘛?司马灵!”阮琳不知道和司徒聪说到什么,扭头大声问我。“什么是不是?我头也不抬,继续擦灰。
“咱们办公室表面上大家挺和气,其实背后互相说别人的坏话。”“我不知道。”我低着擦着桌子说,“我没听见谁说过谁。”
“还没听见呢,前几天不是你告诉我朱秀芬那帮老妇女在背后说我?”“我没说过。”我走到他们面前擦着我和司徒聪的办公桌。
“你别不承认,你替她们打什么掩护?”阮琳对司徒聪接着说,“这办公室里我也就和司马还能说到一起,别人台特坏,你别理她们。”司徒聪看著我微笑,我面无表情装作没看见。
陆续有同事进屋,大声说笑,石玉萍叫阮琳过去看她新织的毛衣得在哪儿加针。阮琳满脸带笑地跑过去,殷勤地替她拿过毛衣加针。“这姑娘挺直率。”司徒聪笑着对我说。
我撇嘴一笑:“你别听她的,她也是个背后搬弄是非的主儿。”“她长得挺不错。”我回头看了眼正跟石玉萍边说带笑的阮琳。
“也就一般吧,还有点人样儿,在咱们单位算是一朵花儿,不打扮也没法看。”司徒聪注视着我,我对他诡秘一笑:“你可以勾搭勾搭她。”司徒聪笑了笑:“你已经勾搭过她了吧?”
我暖昧地笑,未置可否。
“谁都有戏,真的,不一定非要娶她,当个情妇她还是蛮够格。你不打算试试?”“试试试试试。”司徒聪深不测地看着我,微笑。
“不用费很大劲儿一顿饭就行,吃完了你爱带她上哪儿就上哪儿。”我避开他的眼睛。“我们今天干什么?”他听上班铃响了,大家纷纷归座,问我。我把抹布扔回暖气管子上,坐好:
“什么也不干,没的可干。下回上班来你可以带本小说来看,但不要放在桌面上,放为抽屉里,懂吗?头儿一进来就把抽屉关上。”我拉开自己的抽屉,低头看里面看了一半的小说,不再说话。
五
工间休息时,我们下楼在院子里做广播体操,我挨着阮琳,笑对她说:“他看上你了。”“别胡说。”她边踢腿边笑。
“真的,他亲口对我说的。他着迷了,你没白忙一早上。”
“我可一点没看上他。我早上只不过到得早点儿和他说了会儿话,都是同事,不理不睬也好。”
“别那么傲慢嘛,他看上你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别太拂人家好意。”“要是谁看上我都满足他,我得会分身法才成。”
“起码你可以吃他一顿,既然人家盛情难却。”
“他说要请我了?”阮琳停住动作,感兴趣地问。
“说了让我转邀你,我想他还挺迫切。”
阮琳笑了,开始做侧身运动:“我不反对别人请我吃饭。”
“我建议你不妨对他热情点儿,人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嘛——哪怕这希望靠不住。”
“这好说。”阮琳笑着做跳跃动作。
“她同意了。”我回到办公室,对司徒聪说。
“同意什么?”“咦,你不是说要请她,阮……”
“噢,”司徒聪笑说着,“我跟你说着玩呢,你当真了。我请她干嘛?我一点没觉得她有什么魅力,甜俗罢了。”
“谁也没叫你真讨她当老婆。我可跟她都说好了。”“那我去告诉她这是一场玩笑。我从没有为女人花钱的习惯。”
“那怎么行,多不好。算了算了,我掏钱吧,算我请。”我作出咄咄逼人的姿态。“咱们谁都别请,干嘛要请客?”他毫无所动。
“别说了,我请就是了,都跟人家说了。”
阮琳容光焕发地进来,瞧我一眼,扮出一逼迷人的样子摇摇摆摆走会司徒聪办公室前,笑着问他:
“你怎么没下去做操,换换空气?老在办公室坐着人会蔫的。”“啊,没事,我喜欢蔫点儿。”
司徒聪看我一眼,我全神贯注着窗外。
六
“你有没有觉得我和一般不一样?”我们三个坐一间二流餐馆不很干净的桌旁,司徒聪问我。
“没有。”我板着脸回答,随便点了几个实惠的菜,把菜单数目给服务员拿走了。“我得过神经病。”“真的!”阮琳果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我不信。
”
“跟谁说谁也不信,不过我确实得过,就为神经病我才从大学到你们单位来。”“神经上的毛病一般人都有,诸如失眼、焦虑、那不算很特别。”“可我的神经病的一般人神经衰弱一样,厉害得多,我有段时间已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
“那就不是神经病,而是精神病,这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不管叫什么吧,反正我得地那样的病,那会儿大家都说我疯了,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疯了。”
“精神病最主要的症补就是精神病患者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司马灵学过医,这方面他懂得很多。”
“一知半解吧。”我白了阮琳一眼,“我懂得不多。”“你为什么得的神经病?”阮琳没注意到我的白眼,问司徒聪。“精神病!”“噢,精神病。”阿琳看我一眼,仍毫无知觉,傻瓜似地看司徒聪。“说来话长,我今天不想说。”司徒聪相当地矜持,“那话说起来很痛苦的,以后……”
“不想说就不要说了。阮琳你也是,老往人家疼杵干嘛?”
“反正我现在也好了。”司徒聪明朗地笑着,“要不我也不会这么安详地和你们坐在一起。”
服务员把菜陆续端上来,我们开始吃起来。
“发神经病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定和正常时截然不同吧?”阮琳边吃边令人访烦地纠缠着这个话题。
“截然不同,对没发过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新鲜的,无法想象的。”“阮琳你烦不烦?你要想发精神病就无所顾忌地发呗,难道这还要步调一致吧?”“我就是想发。”阮琳挺直腰板对我说,“你管得减吗?不爱别听。我有时就是想发发精神病那样也许可以使我不真的得精神病。”“发精神病的滋味并不好受。”司徒聪说,“假发没有效果,真发就不可收拾。那感觉怎么说呢,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如果你常做梦也许可以多少体会一点,一切法则忽然无效了,你不受任何约束了,你变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不怕了,当然你的肉体仍会被现头碰得皮开肉绽,墙仍然是墙,但思想飞驰了。”“所谓飞驰不过是一通胡思乱想,所谓聪明了也不过是不顾客观规律凭主观意态去理解一切事物。”
“当然在你们正常人后来是这样。”
司徒聪尖锐的反驳使我大吃一惊,我不再吭声低吃菜。
“太有意思了。”阮琳吮着筷子着迷地说,“那一定非常快活,怎样才能真发一回精神病呢?”
“你这问得太离谱了。”司徒聪笑着说,“我不能也不愿教你,否则司马灵该说我有意引你入歧途。何况那不快活,不象好梦一样令人留恋,而且别人也不允许你处于那种状态,他们会千方百计治疗你,让你醒过来。醒来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在臆想中骋骋了多远,现实仍象你发作前一样愿封未动,你反倒难以适应了。”“我倒宁肯哪怕自欺欺地自在一回,反正适应现实也不能让更自在。”“不不,我可不能让你这么个可爱的姑娘变得落落寡合,招人讨厌象我一样。”我只是充耳不闻地埋头吃我的菜。
七
“你真的认为我,嗯,还过得去?”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天已经热了,尽管商店都开着灯,一间毗邻一间形成两列明亮,陈列着五光十色商品的长廊,街上仍相当昏暗,人很多。我们夹杂在人群中走,阮琳象个初次受到恭维的年轻姑娘,红着脸,又腼腆又兴奋地盘诘着司徒聪。
“真的,我对你印象很好。”司徒聪笨嘴笨舌地回答,模样很忠厚但毫不掩饰。他们谁也没注意这顿饭是我付的钱,实际上我已经给撇到一边去了,仿佛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们的约会跑前跑后,面他们要干的只是粘在一起互诉衷肠。
“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难道你不照镜子吗?”
“照的,但我知道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一二分姿色,比我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