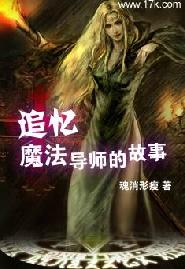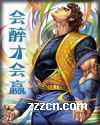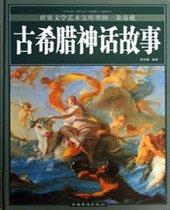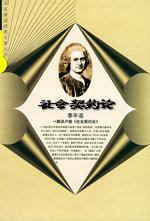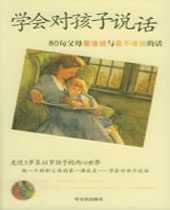������»�-��2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ո�µ���־���¹�����˷ܡ��м���ͬʱ��ҲΪ�༭�dz�ߵľ�ҵ����������ж������������������Ϊ�Ȿֵ�������Ŀ���д��������õ���Ʒ����������
��������������һ����ף������ڶ�ȫ���������ƷͶƱʱ����ƪ���ű༭��Ѫ�ͺ�ˮ����Ʒ���ر��ܵ��˶��ߵĻ�ӭ������ңң���ȵ�ʮ������ŵ�ѡƱ�����������ȵ�������Ʒ������������
���������������¹�������ҵ������нӹ���Ʒ�ͽ���ʱ�������۾�����������ˮ����������
��������
�������������ӵܱ�������3��
���������Ӵˣ��¹����������һ����ͬ�����»ᡷ�����˲���֮Ե����������
�����������������´���������������ʱֻ�������»ᡷд���ӣ��������´������¹�������ǰ���õ���Ʒ�������»ᡷ����������
����������������ô�������ơ��¹��һ�������ڻ��㡢������Ⱥ���е�ʵ���ۺ�ġ��ӵܱ�����һ��һ���֧�����Ȿ��������»ᡷ�ܹ�Խ��Խ��Ҳ���Ǻ���Ȼ�������ˣ���������
������������1994��9���£��¹��ͻȻ�����Ϻ���ס�����ʼ�ҽԺ����������
������������ԭ�����¹������ƴ����д������ͣ�ؼ�ֵ����㿪չ������µ��ռ�������ಡͻ�������������������������
�������������༭������ǰ��ҽԺ��������������
������������ϸ�ĵı༭�Ƿ��֣��¹������Զ��������סԺ�����һЩ����ƷҲû�У���̸����סԺ���Ӫ���ˡ����ǣ���ұ������������ѡ��ڶ����������������������Լ�һ������ҽԺ��ͬѧ��ϵ�����˸������ͼ�����ȥ����������
����������������ʮ�µ�һ���糿�������ˬ���������ģ���Ժ�ij¹��վ���ʼ�ҽԺ�Ĵ���ǰ�������еı༭�Ǹм���˵������һ��Ҫд������õĹ��£������𡶹��»ᡷ�ĸ�λ��ʦ������������
��������������������������ij¹�淴��ű༭����һ�����ӵܱ���ŨŨ�����꣬�ص��˽�������������
������������1995������죬������һ�����겻���ĸ��¼��ڡ��¹��ð�ſ���̿���ֽ��������Ʒ���ġ�����һƪ�����Ϻ�סԺʱ������Ŀ�õ����飬��ʱ���������Ծ��ҵ����¹�淽�����ز�д����һƪ�������µĹ��¡����°�����ʵ��ԭ�ͣ�������һ������ɰ���С��������˳����˵��������֪��ҽ������ӳ�����ĵ����������Լ����Ƕ���Ȼ���������Ρ�������ƪһ����ֵĹ���ȡ���С�ɣ���ᡷ����������
��������������ƪ����ֵ��������ֵ�����ߵĹ��£��������еĹ��»ὲ�л�������㴴��������������
�����������������»ᡷ�༭��Ϊ��ƪ���ºͳ¹�淵ľ������ж�����Ϊ��ƪ���·�����һ�����ڶ����������죬Ϊ���ܹ�ʹ��ƪ��Ʒ���ϵ���ȵ��������༭������������1995��ȵ���Ʒ����ǰϦ��������������
����������������ƪ��Ʒ��ͬ���ŵĸ��һͬ����ӡˢ����ʱ���������벻�������鷢���ˡ���������
�������������¹�����ڹ������ۣ����ಡ�ٴθ���������ܳ���˥�ߣ���ʱ����������¥�ݶ��������ˡ���������
������������������һ���͵��Ϻ�����������
�������������༭����֪�¹�淵���Ϣ������Ϊ���뷨��ҽԺ���γ�ΰ�ֵ���Ϊ����ϵ�������͡���������
���������������еij¹��û�����ǡ����»ᡷ���������µ�һ�ڳ�����û�У�������Щʲô��Ʒ��������ƪ��Ʒ���߶������һЩʲô���죬��һ�ٵ�˵�Լ����ҲҪͬ�ϴ�һ������ȡ��һ�㿵������ȥ��Ϊ�����»ᡷ��дһƪ���õ���Ʒ����������
������������Ϊ�����ò��еij¹�淾�������Լ�����Ʒ���༭��ÿ�춼Ҫ����ӡˢ�������������
��������������һ�ڡ����»ᡷ���ڳ����ˡ��༭�ǽ��Ȿɢ����ī��Ŀ����͵��������ʱ�¹���ò������ֽӹ�ȥ���촽���˺ü��£�����������˵���������ڴ�ʱ�˿�����˷θ����֣���л����л������������
�������������¹��Ҫ��л��Щ�༭��ʲô�أ���������
��������������л���Ƿ����Լ����Ϲ��´����ĵ�·����л���Ǹ��Լ��Ĺ��´����Բ��ϵĹ�������л����������ʱ����Ĺذ����������������ǣ��Լ��������в����˹��£������˷ḻ��ʵľ������磬�Լ�������������˵س�ʵ�����Լ������Ȿ�İ��Ŀ���ֻ���ṩ�˼�ƪ��Ʒ����������������̫��̫���ˡ�����������Ļ�������Ը��Ϊ�Ȿ������д����ƪ����������Ʒ��������������
������������˭���뵽�������ڡ����»ᡷ����ƪ��������ġ�ɣ���ᡷ��������λŮ���ҵľ����أ���������
����������������֮����˫�����š����»ᡷ�����Ȿ��������ź�֧���ŵĿ����Զ������˯���ˡ�����������
�����������������»ᡷ��������ʵ����һ�������ĵ��ƶȣ��༭�����κλ�����Dz��κ��˴������μӵġ���������
���������������ǣ���У������ȴ��һ���������������ż������Ϻ����صĽ�ɽ�������ˡ����»ᡷ�༭������������
��������������У��ͬ�����ơ��¹��һ����ͬ�����ڡ����»ᡷ�������������³ɳ�������һ�����ӵܱ�����ͬʱҲ�ǡ����»ᡷ���Ϻ��Ĵ������ء�����ɽ����ɳ������Ҫ��Ա������������DZ�Ĵ��������ڡ����»ᡷ�Ϸ����˴�������Ʒ������ù����������½����ڡ����»ᡷʵ�����������ƶ�֮��ƸΪ���������Ա����������
��������������ν����Աʵ���Ͼ��ǶԿ�����з���ǰ�����������ƪ�����ܲ����ã������Ŀ����Ƿ�������������һЩ���ʶ�ԵĶ�����û�в����Ҫ��Ҫ�Ը��ӽ������ĵȵȣ�������������������϶��塣����һ�����ս�ԵĹ�������������ˡ����»ᡷ�쿯��Ⱥ���ԣ������˱༭����ÿһλ����Ա�ĸ߶����Ρ���������
������������Ϊ�˺ܺõ�������������У��������æ��ÿ�¶��ý���ȥһ�Σ��������衣��������
�������������������һ����ʥ��ְ������һ����������ꡣ��������
������������Ϊ�˸��õ������������ǰ�����У��������������£���Ȼ���������ƣ�ͣ�����ҵ��ʱ�俴������ȥ�����и��ӡ�������Щ���ӣ���ÿһƪ��������������Լ������������Ϊ�˽�һ����߸�����������������һЩ���˵������������������������������༭������Ա�Dzο�����������
���������������ǣ����Ƕ��ڸ�У�������������������μ������Ļ��飬���е���Щ���⡣��������
������������������֮�����Dzŷ��֣���У������ȥ�����еĸ���ʱ����ֻ��ȴ��ô������ʹ������������ֻ���߹����������ȥ���������ӡ���������
��������������Ҷ���Լ��ͬ�����������ϸɣ���ô��������������
��������������û�а취������У��ҡҡͷ��ֻ�á���ʵ�������Լ���δ���������ԭ��������
������������ԭ������У����֪��ôǰ��ʱ�����һ������һ�鼡����ִ����ή�����������������·������ܴ�����������ȥ�������ӣ�����ȴ���ڱ��������Ƶġ�����ҽ��������Ҫ�ڼ���Ϣ�����ʱҪע�ⰲȫ����У����ҽ��˵��ȥ���ˣ����������ͻ�����ٲμӡ����⡶���»ᡷ�����飬��ȴ��ôҲ�������£���ôҲ���ܲ��μӡ�����������μ������Ļ����������������һ��һ�ε���������������������һ�����ڼ��ﶼ���Բ�����������������Ŵ�ң��ɼ������ŸϽ��������μ�����������
������������һ�����á����»ᡷһ��Ǯ������Ա����Ȼ�������ضԴ��༭�������Լ����Ƿݷ���Ĺ�����ȭȭ֮�ģ����˸ж�����������
����������������������������У��һ�����ˣ����Ƹ���������ʱʱ�̵̿������Ȿ��������»ᡷ�����ڽ϶̵�ʱ���ڵõ����ٷ�չ����������
��������������У�����������ӻص���ɽ���þͲ����ˣ���Ҳû������������������
������������˵���У������뿪����ʱ���龰���滹��Щ���档�����ڲ����ϣ�˫Ŀ���գ������Ѿ���ʮ�����ˡ����ǣ���ȴ�����������ţ�ʼ��δ����������������
�����������������»ᡷ�༭���ڸ�У������֮�������˶��ȥ����������֪�����Ѿ���ȫ������ʱ������Ҧ�Ժ����˻��ٸ�����ɽ����������
��������������У���Ѿ���ȫ��֪���ˣ�����ֻ���������Ķ��䣬�����ظ��������������»ᡷ���˿������ˣ�����������
��������������У��ͻȻ�������벻�����������۾������Ƿ�������ò������ݵ�˫��һ����������Ȼ����������һ��������ʱ���ڳ��������˶�Ŀ������һ�С���������
���������������ǿ�ѧ���������Ҳ�֪��������ȴ����ʵ��������ʵʵ��֤���ˡ��ӵܱ������Ȿ�����Լ����ı༭�������ѷֵĹ���֮�顣��������
��������
�������������ӵܱ�������4��
����������2��ۏ����ʷ֮�ӡ�������
�����������������»ᡷ�¹����������ߣ����Ͻ����Լ������߶��飬���������㴫ͳ�ġ���������
������������������ۏ����ʷ֮�ӣ�������Щ���������¡���������
������������1983�������һ��ϸ�����������ӣ�һ�������˶��Գ���һ����ɡ��Ҹ�¼���һֻ�����С�����ͷ��Ե��ҵ�������·74���Ϻ����ճ����硣��̧ͷ���˿������������۵�С��¥���м��ֵ��ӵض�����˵������һ�¡����»ᡷ�ı༭����������
������������������ʱ��һ�����������ѵ��˴��������˳���������æ˵���������ɣ������»ᡷ��ͷͷ�������������������
�������������Ǹ��������ѵ���æ����ǰ�������Ǹ�������ǫ�͵�˵�����Ҿ��ǡ����»ᡷ�ģ�����������ʲô���𣿡���������
���������������˼�æ����������ֻ����������������ȡ��һ�����������ô��ż��ּ�����ͬʱ���м��ֵֻ̿�����˵��������һ�����ˣ�ƽʱ�ر𰮶����ǰ�ġ����»ᡷ�����д��һ�����£��������ǰ�æ����һ�¡�����������
�������������Ǹ��������ѵ��˽ӹ����ӣ�˳�ַ���һ�£�����ض���˵�������ǹ������ߣ���ӭ��ӭ��лл������ǵ�֧�֡�������������������ǿ����Ժ��ٸ�����ϵ������������
��������������λ���ӵ������˼��༭û�м��ӣ���ƽ���ˣ�����ʱ��˵�����鷳���DZ༭�ˣ���������ã��Ͳ��������ң�����Ҳ���������ˡ�����������
�������������Ǹ����ӵ���������˭�أ���������
�����������������Ǻ�����Ϊ�����»ᡷ��Լ�༭����Ԫ�٣���ʱ�������Ϻ�һ�ҹ������ְ��������λ���������ѵı༭���ǵ�ʱ�����»ᡷ�ı༭�鳤�γ�ΰ����������
������������һλ�༭�����߾���������ˡ���ʱ˭Ҳû���뵽�������»ᡷ�Ȿ����ȴ��������ǵ�һ������������һ��Ϊ���Ȿ����ķ�չ�����Ƕ���ע���Լ���ȫ���ǻۡ���������
��������������Ԫ�ٶ����Լ��ĵ�һƪ��Ʒ����ֵ�����ߡ����˵�������ϣ�������λ���ո��ӵı༭��ӡ��һ��������һ��һ�ٰ�ʮ�ȵĴ�ת�䣬�����Լ��ɱ��������˱���Ŀ����Ի�ȫ��Ͷ���������ô�࣬˵�����Լ����ߣ��༭�ͻὫ�Լ���ƪ�������Ķ����ӽ���¨���ˡ���������
���������������ǣ��������벻�����ǣ����������磬�����յ��ˡ����»ᡷ�˻����ĸ��ӣ���岢����һ���š�����˵������Щ��Ц����Ԫ����ƪֻ����ǧ���ֵĸ��ӣ����༭�ĵĵط������ʮ����֮�࣬ʮ�˸������֣��ߴ���Dz���������⡣���༭�����ж�������ƪ�������ȴ�����˿϶���˵�Ǻ������⡣�������Щ����༭��������ϣ����ȥ��ڹ��˾��ֲ�����һ������������ˣ���������ָ���ġ���ĩ���༭���������������пϵĽ��飺��������
�������������뿼�Ǹ���Ϊ��808�����ˡ�����������
��������������������⣬������ۼ�̫�أ���������
��������������ѧ����Ҫ���ϣ���������
���������������鵽��ס�ظ����ĺ�������˾��ֲ����մ�����ѧϰ�ͼӹ�����������
������������һ����ѧд�����µ��ˣ��ܵõ������ϸ�����ָ�㣬��Ԫ�����Ǹ��˵����������ˡ���������
�����������������ǹ��˾��ֲ����´�������鳤�����ͻ����ֶ��������ָ���Ͱ�����Ԫ�٣��Ⱥ����ƪ�������˰˴��ġ����ǣ�������Ԫ�ٵ�ʱ��д��ˮƽ̫�ͣ���ƪ������Ȼδ���ĺá���������
������������1981�꡶���»ᡷ���Ϻ�ݷׯ���бʻᣬר��֪ͨ��Ԫ�ٲμӡ���������
��������������Ԫ�����ζ�û���뵽���Լ���һ���ֶ�δ�����������ˣ���Ȼ��֪ͨȥ�μӱʻᡣ��������ƪһֱδ���ij����ĸ��ӣ����˷��ֲ����زμ��˱ʻᡣ���������һ�������йع��´����ķ��������ۣ�����һ���������ˡ��ڱ༭��ָ���£�������ض���ƪ���С�808�����ˡ��Ĺ�����һ�ν������ġ���������
����������������αʻ������ʱ����Ԫ�ٵ���ƪ��Ʒ����Ϊ��αʻ�����Ʒ�����Ƚ����������Ӧ�Ľ��𡣡�������
��������������Ʒ��Ȼ��δ�ﵽ��ʽ������Ҫ����ȴ�õ��˱༭����ͬ���ǵĿ϶�����Ԫ������˵�����ĸ��ˣ����ᶨ������־���¹��´����ľ��ġ���������
��������������������»ᡷ�ٰ����ʻᣬ�ٴ�������Ԫ�ٲμӡ���������
����������������αʻ��ϣ�������һ���ĵ���ƪ���½������г��������г�������Ϊ��һƪ�ܺõĹ��£��㽫���ĺ�ĸ�����ȥ�ٴν��������ģ���������ij��ˡ����ص�̦��˿�����ܿ����1988��ڶ��ڡ����»ᡷ�Ϸ����ˡ���������
�������������ⷢ���Ŀ�����Ԫ���ڱ༭��ָ���£����Լ���Ʒ���еĵ�ʮ�Ĵ��ĸ尡����������
��������������ƪ���·���ʱֻ�м�ǧ�֣������ĵĵ徹��ʮ����֮�࣡��������
��������������Ԫ�ٵı�ְ������æ���ڳ����������ʱ��������������ڸ���ҹ��������С������˯֮�����Լ��ľ�������ƴ�����ġ����⼸�������ƪ���ӵ����У��༭�Dz�����ɫ�ؽ���Щ��Ϊһʱ�嶯��д���µġ����顱һһĥȥ������һ����������������߱���������̿����������һ��δ�����Ĺ������ң��������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