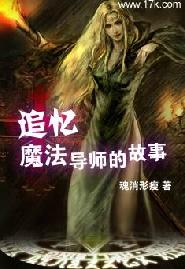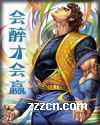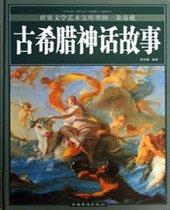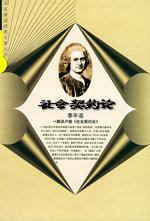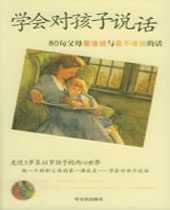解读故事会-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1。 老总们为何总上厕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告已相继在全国的部分杂志上出现。这些广告不但使刊物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些期刊开始在依靠广告获利的同时,逐渐地摆脱了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窘况,走出了一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路子,立刻受到了许多刊物的关注。
《故事会》自1987年开始利用一定的版面刊登广告。
这时的广告显得零星而不成规模,也没有具体的指标与相对固定的版面。主要内容从开始的日用化妆品逐渐地扩大到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食品机械、玩具以及各种技术转让等等,其广告经营额也从开始的十万元逐渐地升到数百万元。
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一个拥有庞大发行量的媒体上适度、适量地开辟广告是正确的。
此时的广告虽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故事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期刊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客户找上门来。编辑部的编辑人手本来就少,而且大都是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秀才”,对于这种全新的经济行为都不太了解,更不熟悉,经常为此要花很大的精力。
编辑部在正常的编辑工作之外,面临着一个创刊以来的全新问题——除了因在刊物上刊登广告带来比较丰厚回报的老客户,一些需要在刊物上刊登广告的新客户也不断地涌现,忙碌的编辑工作使得编辑们无法应对这种新的变化。
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抽调一名编辑来兼管这件事情。
当时编辑部的人员结构,大部分编辑都是创刊初期就从事编辑工作的老同志,考虑到年龄的关系,最后决定让最年轻的编辑冯杰来担任这项工作。
冯杰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在从事了近十年的编辑之后来兼搞广告业务,从事一项完全陌生的经济工作,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人生面临着的一种新的挑战。可是,他年轻,有精力,对于新生事物也容易接受。加之他勤于钻研,在上大学时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也学得比较好,担任编辑后,平时又喜欢看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研究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在兼管的这几年中,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路子,使《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首家广告公司。
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将冯杰调出《故事会》编辑部,到广告公司从事广告工作。为了提高广告效益,《故事会》在这一年结束了近三十多年的套色印刷封面,改用彩色印刷。
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机构改制中,正式成立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冯杰担任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个编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冯杰从大学毕业走进《故事会》编辑部,在这里埋头一干就是十个年头,在这些年里,他勤奋工作,认真编辑稿子,与一个个故事作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经手编辑了许多优秀的故事作品。他热爱编辑工作,为此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在这个编辑部里,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正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现在却一下子就要离开编辑部了,心里真还有些舍不得。
面对着新的选择,他也曾思考过。自己要是离开编辑岗位,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编辑部这个集体,今后在评职称、晋级升职等方面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会失去到手的许多东西。而广告对于自己来说,几乎就是一件全新的事情。过去做编辑时只是兼管,没有压力,不用管太多的经济效益,而现在却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广告业务中去,肩上不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在广告传播中心有很大一块是《故事会》的广告,经常还会来往于这个自己熟悉的编辑部。
就这样,冯杰恋恋不舍地离开《故事会》编辑部,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冯杰上任后才发现,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现在与过去自己做兼职的时候却完全不同。
那时,由于刊物的广告才刚刚起步,未形成一定的“气候”,整个管理与运作都相对比较粗糙。既用不着调查市场,又用不着与外面联系,更不用管客户之间的交流。发行量如此巨大的刊物,做广告就如同医院里的医生坐诊,只要在办公室一坐,广告客户就会排着队前来“候诊”,排着顺序等着自己的版面。现在做了专职的广告工作之后,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就再不能做“坐堂医生”了,你必须得了解广告市场的行情和走向,这本刊物在全国同类刊物广告中的地位和影响,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得与编辑、印刷等方面联系,还得善于与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接受他们的管理与监督。同时,还得学习必要的法律法规,做到合法经营。
这是一种阳光下的利润。
为了使《故事会》的广告获得更大的效益,同时也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冯杰接手后采用了委托代理的方式,将其广告业务委托给一家可靠的广告公司来进行具体的操作,每年由广告公司上交一定的经费。
这种办法相对于《故事会》过去“坐诊”的广告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将过去坐等广告的被动局面变成了主动的形式。
可是,这种方法实行不到一年,冯杰便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独家经营着《故事会》的广告业务,使原本处于竞争的广告业变成了一种独家垄断的局面。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负责代理的广告分司可以任意提高广告价格,在造成广告市场混乱的同时,损害了刊物的利益,也无形地损害了刊物在读者中的形象。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了做活《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在得到出版社领导的同意之后,《故事会》实行全国招标的形式,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经营的先河。
1998年7月18日,对于《故事会》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在上海郊外的美丽华度假村,一场全新的广告竞标会议正在进行。这是《故事会》创刊以来所从未实践过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故事会》从过去单纯依靠发行来增加效益的办刊模式,开始走向了依靠发行拉动广告,完全面向市场化的运作新形式。
会议由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副主任冯杰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故事会》副主编吴伦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公证处的公正员到现场负责公正。
招标采用暗标的形式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事实再一次说明,只有竞争,才能获得发展。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2)
2。 “放水养鱼”为上策
1999年,《故事会》根据在1998年招标的情况,开始进行广告的具体操作。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时的广告已先后经历了由自主经营到委托经营,再到招标经营的过程。而这种过去从未见过的招标方式,虽然给《故事会》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广告收入,但最终的效果如何,这都得有赖于在实践中检验。
上半年,整个形势都比较好。中标的广告公司按质按量地将他们所得到的广告投放在刊物上。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各种原因,广告质量相对有所下降,就其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招标时竞标的价格过高,致使中标公司在完成广告业务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中标的广告公司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完成任务,只要不违反国家颁布的广告法,来了就刊登,这就无形中造成了广告质量的下降。
冯杰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认为,合法经营不能带来合法的利润,这就是广告质量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
1999年中国杂志年广告经营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民航》,其月发行量为三十七万册。第二梯队的为《时尚》《ELLE》等,其月发行量均在五十万册以下。第三梯队为《家庭》《读者》《知音》《家庭医生》等,其发行量均在百万以上。从《故事会》本身的定位来看,当属第三梯队。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故事会》当年广告费的绝对值相比之下是最高的,这当然与这本刊物目前巨大的发行量有关。
为了提高广告质量,《故事会》在其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