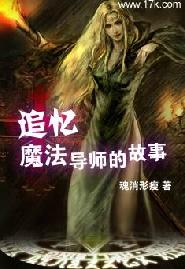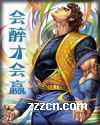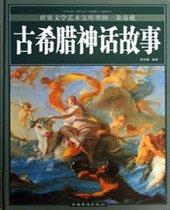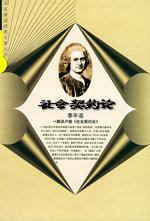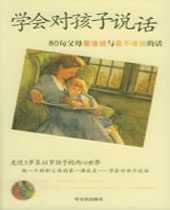解读故事会-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故事会》的未来之路是什么?
何承伟心中早已画出了一幅蓝图。
他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仍感到很不满足。在新世纪,刊物竞争日趋激烈,仅凭以往的经验,不可能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难题。《故事会》要取得新的发展,必须有新的发展目标。在产业建设方面,必须走好两步‘棋’,一是向基层发展,深入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二是走向世界,引进世界故事的精华,为己所有,然后再推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读者共同享受故事美学,实现‘故事的世界,世界的故事’的目标。”
好一个宏伟的目标!
经过1979年那次由《故事会》发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研究专家和作者的研讨会后,《故事会》有了一个模式,而且事实证明已是读者乐于接受的模式。以后声誉卓著,基础日固,只要照此萧规曹随,刊物也同样会“稳步前进”。可是,这不适合何承伟的性格,他要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故事会》更大的进步。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现在虽然已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社长了,但他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故事会》,因为这本刊物同时也是出版社的“拳头产品”。他已将自己的大半生心血,融入了这本期刊的字里行间,融入了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成长的历程,融入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满意的心灵。他生命的年轮也在这一月一本的《故事会》中增长着,这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追求,有他的事业,有他乐意献出整个生命的激情。
正是由于他和两代编辑的忘我工作,这本小小的刊物,才能够在中国百年期刊的历史上,创造出如此令人神往的神话。
为了将这本刊物引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这本刊物走向世界,让世界来了解这本刊物,何承伟围绕这个宏伟的目标,已经开始了运作。
作为一本刊物,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要想使刊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必须让其所代表的文化走向世界。
为此,围绕何承伟所提出的宏伟目标,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重打通和架设两座文化桥梁——“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传统便是一种继承,一种文化的发扬,这是“根”。只有“根”深才会干壮、叶茂,才能有生命力。但是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一味的“传统”,就会使一本刊物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而“民族”与“世界”本来就是一对统一体。因为在人类的文化发展中,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具有世界性,才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
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期刊的发展,也曾经有过许多想“走向世界”的刊物,与《故事会》不同的是,这些刊物将一些外来的东西,进行了毫无选择的移植,有的甚至是完全“西化”。可是,这些被“舶来品”由于水土不服,不但没有达到的预期的目标,反而圈子越做越小,不久便关门大吉,连编辑部那间小小的房门都未曾迈出去。
事实一再地向我们证明,抛弃了民族传统的期刊,走向世界只能是一句空话。
《故事会》则牢牢地抓住了“民族性”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地架设起“两座桥梁”,脚踏实地地在继承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挖掘民族文化有意义的东西。同时,又根据现代生活的特征,不断地开发有时代气息的新故事。在此基础上,从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欣赏习惯出发,在不断培育民族文化的同时,有目的地引进外来文化,并通过“嫁接”,使其能够为中国的老百姓所接受,所喜爱。
《故事会》有目的地向海外的读者打开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窗户的同时,又向国内的读者打开了外来文化的另一扇窗户。
《故事会》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以民族文化为支点的:通俗、易懂、易记、易讲,便于流传,就是从外国引进的“苹果”,到了《故事会》这棵中国的“树”上,也要将其培育出一种中国文化的味道来,然后奉献给读者。
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高雅与流行的结合,使这本刊物在海内外赢得很好的声誉。
在这本薄薄的刊物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将中外古今融会贯通的大手笔。原有的“民间故事金库”“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已成为《故事会》的长期保留栏目。这里的故事大都是从中国民间传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学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作品,经过作者加工,用通俗易懂、明白如画的语言重新进行了改编,使中国的读者不仅爱看,也使外国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文化的滋润。
为了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使刊物真正地走向世界,《故事会》始终坚持民族性、大众性和现代性的结合,坚持追求通俗文学的高品位。作品坚持清新明快,诙谐幽默,接近群众的品味和民族审美需求。近来还不断地推出一些中外读者都能接受的新栏目,如“中国新传说”、“情节聚焦”、“谈古说今”“传闻逸事”等等。这些栏目的故事,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一种令人神往的中华民族文化,这是一座从本民族的土地上向外延伸的世界之桥。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8)
1998年,何承伟一行数人来到台湾。他们是受台湾出版界的友好邀请来访的。
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出版界的同行和专家们,对《故事会》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交谈中,台湾同行们对于《故事会》在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令人吃惊的发行数量,一个个都听得入了神。
在台湾,一本期刊能够发行到上万册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听到《故事会》上百万册的发行量,就如同在听一部天书一样。这些同行们对这本刊物进行仔细研究后终于发现,这是一本以本土文化为主的期刊。
台湾之行,《故事会》的名刊效应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同时也拓展了刊物的海外空间。台湾的同行们都希望以后能加强联系,相互交流办刊经验,使《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在海外的华人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故事是没有国界的。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讲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一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保留到现代。进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曾掀起过“故事热”。据美国著名故事大王、儿童文学作家 、诗人珍妮·约伦女士说:“今天 ,美国重又迎来了讲故事的‘文艺复兴’时期。”
珍妮·海伦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她说:“1974年,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乔尼斯波罗镇上,举办了一次毫不起眼的故事节,当时有二百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好奇的听众。今天,乔尼斯波罗10月的故事节,能够吸引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故事讲述者、学讲故事者和听众。在全美国的二十多个州里,也有了各自的故事节,故事研讨会,故事晚会或者故事周末,连加拿大和英国也开始举行了此类活动。”
珍妮·约伦女士的这些话,被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一书。这充分地说明,好的故事都应该没有国界,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样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对故事进行研究的刊物,名叫《口头理论》,由美国口头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以故事和传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正是这样,《故事会》走向世界也是顺应了时代和历史潮流的。
由于《故事会》坚持“世界的故事”,以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空间,不断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1997年月11月24日,以吉米·纳尔·史密斯为团长的美国故事代表团一行四十人,专程来到上海,来到《故事会》编辑部,与编辑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
对于《故事会》的办刊思路以及在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老外们听得是津津有味。
她是谁?她来自何方?
要了解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她所发表的文章——
“为了了解目前新故事的流传状况,首先介绍一下堪称无所不包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月刊《故事会》……
“《故事会》是三十二开百页不到的小册子。每期目录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新故事’栏目,接着就是笑话、各种传说、谚语故事、外国故事以及面向儿童的‘妈妈讲故事’。再就是章回小说式的‘中篇小说连载’,自1983年第五期至1984年第八期,五次连载了《蔷薇花案件》。最后在‘故事编讲辅导’栏中,刊有关于新故事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新故事写作方法等文章,内容的确丰富多彩,读起来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个珍宝箱。
“这本小册子在日本的名声虽然刚刚开始,但在中国,到去年发行量已达六百万册。这个发行量居全国期刊第一位。……《故事会》是个人花钱买的。据读者来信中反映,这本杂志每到书摊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若不预先订阅,临时很难买到手的。可见这迫切需要逐步扩大发行量。这六百万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居全国首位的呢?而且他们在(去年)年末公布的数字还是三百万册,一年之间竟增加了一倍。从1984年起,又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发展得简直没有止境。
“那么,声望如此之高的秘密何在呢……”
这是一篇对于故事进行研究专著中的一节,作者名叫加藤千代,是一位日本学者。
加藤千代的这部专著后来被译成了中文,发表在1985年9月出版的《今天的中国民间文艺特辑》中,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是杂志的通俗读物化;二是《故事会》月刊;三是最近的新故事;四是关于新故事概念的讨论;五是民间的创作空间;最后是结语。
为了完成这部专著,加藤千代飞跃日本海峡,从中国的东北一直采访到上海,对这本刊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搜集了大量资料。
《故事会》的发展引起了加藤千代极大的兴趣,吸引了这位外国学者,她回到日本之后,曾专门地向日本的读者做过推荐,使这本刊物很快传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
最近几年来,《故事会》不仅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在北美、欧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海外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这些远涉重洋的学子,将这本他们所喜爱的刊物带向了世界各地,不但在华人社区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在一些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位女作家曾经谈起过这样一件事情,她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每月都要她定期地给邮去一本当月新出版的《故事会》。这本刊物到了那里以后,很快就会被一些华裔学生抢着阅读,最后连一些其他国家的同学都来争着要她们给讲一讲刊物上面故事,这些外国学生听完后有时就会开心地大笑起来。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9)
《故事会》在这所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国际性的刊物”。
《故事会》时常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措。
2003年国庆前夕,我突然听说这本刊物从明年开始就要改成半月刊。
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期刊界有一股“改刊热”,许多较有影响的期刊都相继完成了自己的改刊任务,将过去的月刊改成了周期较强的半月刊,加快了期刊的节奏,纷纷“抢滩”市场,占领市场份额。
在此期间许多作者和读者也曾给编辑部来信,要求《故事会》同中国其他有影响的期刊一样,尽快改成半月刊。
可是,几年下来,编辑部仍然按兵不动。
原因何在?
主要是怕改刊影响作品的质量,怕读者掏钱却买不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因为《故事会》是一本以原创为主的期刊,其作品的成熟期比较长,编辑部在作品上所花的精力与时间也相对较多,如果跟着改刊的潮流走,将一本刊物一分为二,势必会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何承伟和所有编辑的观点都很明确,改刊并不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应该是质量的再一次提高。让故事的世界真正地走向世界的故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辑部不盲从潮流,而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准备,在提高刊物质量上下功夫。
为了保证稿件质量,对于稿件的终审,《故事会》独创了一个新的审稿制度,即实行由主编主持下的特约编辑和编辑一同“三堂会审”的办法,及时发现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从而使作品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由于提高了作品质量,在2003年5月前后,全国许多刊物受“非典”影响发行下滑的情况下,《故事会》的发行反而有所增加,码洋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三百万元。
当然,为了培养刊物的后备力量,从上海高校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拔了马峡、褚潇白两个年轻人进入编辑部。在选拔录用编辑时除了学历和文字能力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外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故事会》是一本依靠市场运作的刊物,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改刊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3年月11月份,《故事会》将开始试刊,2004年正式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为“红版”,下半月刊为“绿版”。
改版后的《故事会》不单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刊物将强化作品的个性,从而实现“人无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