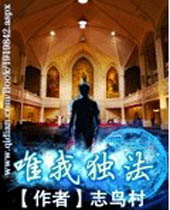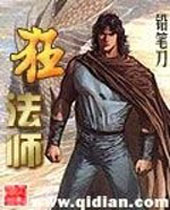懒人懒办法-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异样:它忽然生龙活虎,似乎想要翻个大筋斗。我们拼命摁住餐桌,努力使它维持在一个水平位置。这样一来,他以为我们阴谋跟他作对,便愤起反抗。结局通常是这样一幅场景:一张翻倒的餐桌,一摊溃不成军的晚餐散落在两排四仰八叉、狂怒不息的男男女女之间。 今天早晨,他以惯常的风度走进我的房间,看派头像是乘着一股美洲飓风。头一件事,就是用它的尾巴把我的咖啡杯从餐桌上扫掉,将里面的内容点滴不剩地全都打发到我胸前的马甲上。 我慌张地从椅子里站起身,嘴里骂骂咧咧,迅速向他逼近。他比我抢先一步到了门口,撞上了伊莱莎端着鸡蛋正要进门,伊莱莎“啊唷”一声跌坐在地,几个鸡蛋滚落到地板上不同的位置,就地把自己摊开。随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离开了房间。我跟在后面大喊大叫,厉声警告他:快些滚到楼下去,一小时之内不要让我再见到他。看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绕过煤铲,走了。我这才回到房间,先把自己弄干,接着再吃完早餐。我料定他已经到院子里去了,但十分钟后,我一眼瞥见过道里,这家伙正坐在楼梯口上。我喝令他马上下去,可他只是一个劲的狂吠跳跃。我只好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原来是提图斯。她坐在楼梯口的次一级台阶上,不让古斯塔夫过去。 提图斯是我们家的小猫。其块头跟一个价值一便士的面包圈大致相当。她弓着背,骂骂咧咧,活像个医学院的学生。 她的确骂得很起劲。老实说我自己偶尔也这么干,但比起她来,我只能算是业余水平。实话告诉你(请当心,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之间说说而已,我可不想让你们的夫人知道我说的话。女人不懂这些事,但你和我,你知道,男人之间就不一样啦),我认为骂人对于男人益处多多。“骂人”是安全阀,恶劣心情通过无毒无害的胡言乱语得以宣泄,从而避免了以另外的方式对你的心智造成严重的内在伤害。当一个男人说:“上帝保佑,我亲爱的好先生。太阳、月亮、星星,究竟是什么使您如此大意(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以至于让您费这么大劲把您光洁灵巧的脚落在我的粗鄙的脚趾上?是不是您没有领悟到行进中你身体的移动方向?你这个聪明正派的年轻人,你呀!”或者类似效果的措辞时,他当然感觉更好。在我们暴怒的时候,骂人会起到同样的平息效果,和众所周知的打碎家具及猛摔房门之类的方法相比,效果亦颇相当。再者说,骂人这种方法也更便宜一些嘛。骂人消除一个男人的火气,就像用火药清理洗衣房的烟囱一样有效。隔三差五地爆那么一下,无论对男人,还是对烟囱,均有益处。对那种从不骂人,也不猛踢板凳,又不狂暴地乱捅火炉的家伙,我实在不敢抱持信任。没有相当的出口,由生活的无尽烦恼所引发的愤怒,就容易在我们体内发炎并溃烂。轻微的烦忧,若不被我们随手抛弃,而是和我们并肩而坐,就会变为悲痛;少许的冒犯,若在反刍的温床上被我们反复思量,就会生长成巨大的伤害。仇恨和报复的种子也就会在恶毒的阴影下,生根发芽。 骂人缓解情绪,这就是骂人的作用。有一回我向姑妈解释这个道理,但她不以为然。她说我与这种情绪之间,理当无甚瓜葛。 我也是这样跟提图斯说。我对她说:像她这样一只生长于基督教家庭里的猫,应当对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我并不在乎从一只老猫那儿听到这些骂人的话,但看到一只小猫,这么年轻就会骂人,我恐怕不能袖手旁观。 我把提图斯装进我的口袋里,回到书桌旁。一会儿就忘了她的存在。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从我的口袋里爬到了桌子上,正在试图吞下那支钢笔。接着她把腿伸进了墨水瓶,弄翻了它。跟着又舔起那条腿来。再接下来,她又骂开了,当然,这回是在骂我。 我把她放到地板上,迪姆便和她吵起架来。我真希望迪姆这家伙少管闲事,提图斯做什么都与他不相干。何况,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圣徒,只是一只两岁大的猎狐犬,但他却喜欢什么事都插一杠,那作派就像是个白发苍苍的苏格兰牧羊犬。 此时,提图斯的妈妈也加入了进来,迪姆的鼻子被抓伤了,为此我非常开心。我把他们三个放到过道里,这会儿他们还在战斗。我被打翻的墨水搞得心烦意乱,气急败坏。今天上午,如果再有任何一个猫狗之辈敢来捣乱的话,最好带上它的殡葬师一起来。 话说回来,我的确很喜欢猫和狗。他们是些多么快乐无忧的家伙!作为同伴,他们比人出色多了。他们不会跟你反目成仇,也不会和你争吵辩论。他们从不谈论自己,而是在你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时候,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并且始终保持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们从不发表愚蠢的评论。他们从不隔着餐桌观察布朗小姐,虽然他们老早就知道她和琼斯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他前不久才刚刚和罗宾逊小姐结婚)。他们决不会把你老婆的表弟错认作她的丈夫,而把你当成她的公爹。而且,他们更不会要求一个年轻的作者把十四部悲剧、十六部喜剧、七部闹剧和两部滑稽剧放到他的案头,而他自己压根就没写过一部戏。 他们从不说刻薄话,也从不会先是挑剔我们的过错,然后又假惺惺地说“这全是为了你好”。在我们困难的时刻,他们不会婉转地提及我们过去的蠢行和过失,也不会语含讥讽地说:“噢,是的,假如你从前志向远大,如今必定有所作为。”他们从不会告诉我们(就像我们的情人经常所干的那样),说我们远不如从前那样好。在他们眼里,我们始终如一。 他们见到我们总是很开心。他们和我们休戚与共,哀乐同当。我们高兴时,他们快乐;我们严肃时,他们谨慎;我们悲哀时,他们忧伤。 “嗨!快乐吗,想寻开心吗?你算找对了,我就是你的玩伴。我就在这儿,活蹦乱跳地围着你转,跳跳蹦蹦,哼哼唧唧,用脚尖旋转,随时准备陪你玩闹。如果你不相信,就看着我的眼睛吧。还会是什么呢?一个客厅里的捣蛋鬼,并且从来用不着留心家具;或是一个在清新凉爽的空气里蹦蹦跳跳的野孩子;一个跑过田野、奔下山岗的小精灵。难道我们没有让老农夫加弗·高戈尔家的鹅尝过我们的厉害吗!哈,来吧。” 或者,你喜欢安静地思考。很好。小猫帕西可以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低声哼哼;大狗蒙特莫伦西蜷缩在地毯上,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炉火,不过有一只眼睛始终停留在你的身上,万一你突然发现老鼠的踪迹,那他就可以大显身手啦。 当我们把脸深埋在自己的双手里,心里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时,他们不会正襟危坐地发表高论,说我们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也不会幸灾乐祸地希望那是对我们的警告。相反,他们会静悄悄地走过来,用头轻轻抵着我们。如果是只猫,她会站在你的肩头,撩乱你的头发,说:“天啊,我真为你伤心,老伙计。”明白如话,绝无虚言。如果是只狗的话,他会瞪着真诚的大眼睛,望着你,仿佛是说:“得了,不管怎样还有我呢,我们并肩携手,闯荡世界,不是吗?” 狗非常粗心。他处理事情从来不问你是对是错,从不操心你在生活的阶梯上是升是降,从不打听你是富是贫,是愚是智,是无赖还是圣徒。你是他的伙伴,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幸运倒霉,荣辱毁誉,非所计也,他反正是铁了心地跟着你、安慰你、守护你,只要需要,他可以把命也交给你——这缺心少肺、痴头傻脑、失魂落魄的狗啊。 噢,我忠诚的老友,你深邃清澈的双眸,你明亮敏锐的目光,在人们没来得及用言辞表达之前,你用眼睛说出了一切。你是否清楚?你只是个没有思维的牲灵。你可曾知道?那个靠在电线杆子上、目光呆滞、一身酒气的笨蛋,他的智商不知比你高出多少。你更不会明白,那一个个自私狭隘的无赖,是怎样靠欺诈为生,他们向乏善举,从无良言,思无不鄙,想无不俗,行无不诡,言无不诈。你可知道这些蝇营狗苟偷偷摸摸的家伙(世界上这种东西有好几百万),他们可比你这个诚实、勇敢、无私的畜牲高级得多,就像太阳之于烛光。他们是人啊,你知道,在整个广袤永恒的宇宙中,人是最伟大、最高贵、最聪明、最高级的生命。任何人都会这样告诉你啊。 是的,可怜的小狗,你太蠢,和我们这些聪明的人类比起来,你真是太蠢了。我们懂得政治,还懂得哲学,简单说吧,除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之外,除了这个小小世界外面的所有事和里面的大部分事之外,我们无所不知。 不过,没有关系,小猫小狗们,正是因为你们愚蠢,我反倒更喜欢你们。我们都喜欢愚蠢的东西。男人不能忍受聪明的女人;而女人,她最理想的男人应该是一个可以被她称作“亲爱的老傻瓜”的人。偶然遇见一个比自己更傻的家伙,是何等令人愉快,我们会立刻爱上他们。对于聪明之辈,这世界必是个崎岖险恶的所在。庸碌之徒讨厌他们,至于他们自己,他们发自肺腑地相互憎恨。 话说回来,聪明人只不过是无足挂齿的一小撮,即使他们有什么不痛快,也还不至于真的会出什么问题。只要蠢人能够活得轻松自在,这个世界总归还算不赖。
第二章与猫狗同行(2)
在通达世故方面,猫比狗有着更好的名声——他们更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待朋友也不会过于盲目。我们这些世俗男女,对于猫的如此势利深感震惊。的确,猫喜欢一个厨房里铺有地毯的家庭,要甚于没铺地毯的。倘若家里的孩子多,他们恐怕更愿意到邻居家去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不过总的来说,猫是冤枉的。你和一只猫交上朋友,她将忠诚地跟随你,荣辱与共,甘苦同尝。我养过的猫,全都是我最坚定的同志。曾经有那么一只,我走到哪她跟到哪,几乎叫人颇为难堪,以至于我不得不央求她,务必帮帮忙,千万别再跟着我到大街上去了。当我回家迟了,她总是坐在那儿等我,跑到过道里迎接我。此情此景,让我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像个已婚男人,只是她从来不会先是盘问我去了哪儿,继而对我的老实交代一概不信。 我的另一只猫的习惯是,每天很有规律地把自己灌醉。她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在地窖门外游游荡荡,目的是逮机会溜进去,舔那些从啤酒桶上滴下来的酒。我提及她的这一习性,并非以此来夸颂此辈,而只是想表明:他们中的某些家伙和人类实在并无不同。假如灵魂转世之说果真属实的话,这些小家伙的确有资格迅速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他对虚荣的爱好仅次于对酒的爱好。无论何时,只要逮到了一只特别大的老鼠,她就会把它带到我们大家正坐在里面的屋子,将老鼠的尸体摆放在我们中间,等待我们的夸奖。天啊!姑娘们总是大呼小叫。 可怜的鼠辈!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让猫狗之徒因捕杀它们而获得荣耀,为了使化学家因发明消灭它们的毒药而财源滚滚。不过,关于老鼠也还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它的身上有几分诡异和神秘。它们那么狡猾,那么强大,数量惊人,残酷而诡秘。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废弃的房子里——破窗烂壁,残砖颓瓦,房门在生锈的合页上吱吱嘎嘎地摇晃。它们知道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及时逃离,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搞不懂它们去了哪里。它们在藏身之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厄运即将降临大厅,那些伟大的名字,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它们在阴森森的停尸房里神出鬼没。 没有老鼠,恐怖故事就不完整。在鬼魂和凶手的故事里,它们静悄悄地跑过空荡荡的房间,壁板的后面能听到它们磨牙的声音,它们贼亮贼亮的眼睛,透过破旧挂毯的小孔,凝视着。它们尖利的叫声,在这个死亡之夜显得神秘可怖。这时候,阵阵悲风呜咽着扫过坍塌的城堡,像一个哀泣的女人穿过无人居住的空房间。 濒死的囚徒,在他们阴森的地牢里,穿透恐怖的黑暗,看见老鼠猩红的小眼睛,如同明明灭灭的煤火。在死亡般的寂静中,听见老鼠的脚爪子疾速走过的声音。他们尖叫着在黑暗中坐起身来,注视着这可怕的夜晚。 我喜欢读那些关于老鼠的故事,哪怕读得心惊肉跳。我尤其喜欢那个哈托主教与老鼠的故事。正如你所知道的,那邪恶的主教将大量玉米屯积在谷仓里,不准那些饿得快死的人沾边。当饥民向他乞讨食物时,他把他们召集到谷仓,突然关上大门,放火把饥民全部烧死。第二天,来了成千上万只老鼠,它们是被派来审判主教的。哈托主教逃到了他坚固的城堡里,它位于莱茵河当中。封好大门,主教设想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再看看老鼠大军吧!它们游过莱茵河,啮穿厚厚的石墙,愣是把坐在塔里的主教给活活吃掉了。 它们在石头上磨就它们的利齿, 它们此时正将主教的骨头啃吃; 它们是被派来审判主教的罪行, 它们这就要啃完那主教的四肢。⑴ 哦,这真是个有趣的故事。 还有哈梅林的彩衣笛手的传说。一开始,彩衣笛手用笛声引走了那些老鼠,后来,当镇长失信于他,笛手就把全镇的小孩引到自己身边,带着他们走进了深山。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古老传说!我很想知道它的寓意是什么,或者,它真的有什么寓意吗?在行云流水般的韵律之下,像是深藏着某种奇妙的东西。这个画面长时间在我心头萦绕:离奇而神秘的老笛手,吹着笛子,走过哈梅林狭窄的街道,孩子们跟随着他,手舞足蹈,脸上浮现出沉思和热切的表情。镇上的老人们想拦住他们,但孩子们毫不理会。他们听着那神秘奇幻的笛声,不由自主地跟着它。正在玩耍的孩子,游戏尚未结束,玩具就从漫不经心的手里悄然掉落。他们并不知道这样急急匆匆,到底是去哪里。神秘的音乐在召唤他们,他们紧紧跟随。至于目的地,他们既不关心,更不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