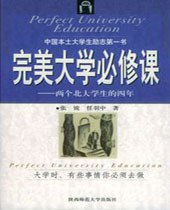大学教授隐秘情欲剖白:非色-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还是没有说明白,评论家说,他们凭什么要相信你?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太清,作家之一说,也许他们觉得,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
文章,会有一种类似于发表的满足感吧。
痖白的朋友们(7 )
我想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吧,女作家说,可能是收养,或者是继母什么的。
我想也是,女诗人说,要不然太恐怖了。
其实,赵耳说,有没有血缘关系,在这个事件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活已经突破了某种底线,这才是最可怕的。
唉,诗人之一长叹一声说,我们还在写诗,还希望在诗里建立一个美丽的乌
托邦,你说,我们写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我靠,我靠,诗人之二说,你总算说了一句人话。
所以,痖白说,有些人在我的小说里寻找到猎奇的快感,我觉得这很奇怪,
也许在小说里,我们已经把许多生活美化了呢!
此言大大的有理,作家之二说,依老朽之见,写作在本质上是虚构美好生活,
而不是要反映生活啊!
为你的精彩发言干杯,赵耳说。
大家举杯,饮了杯中的酒。
接着继续讲笑话。他们要我讲一个。我平时待在学校里,孤陋寡闻,哪有什
么笑话,但是他们不同意,一定要让我讲一个。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一个来。
我就给他们讲了。可能我的笑话本来就没有什么趣味,也可能我不善于讲笑话,
总之,等我讲完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发出笑声来;他们看着我,个个显得一本
正经。我不免有些窘迫,脸都有些红了,结果,我的这种狼狈的样子把他们逗笑
了。他们持续不断的大笑下去,比刚才的任何一个笑话都令他们开心。按照事先
的约定,我只好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很快就喝得有些高了。当然,我自己也很愿
意这样喝酒。我感觉跟他们在一起很高兴。我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他们虽然看
起来非常粗俗,但是我并不反感这种粗俗。他们丑态百出,放浪形骸,也许正是
像我这样的人生活里缺少的。我喜欢他们。如果有机会,我实际上很愿意和他们
一起,到达下流和无所顾忌的境界。
那天我们玩到很晚的时候,痖白忽然接到徐思菲的电话。不知道徐思菲说了
什么,痖白的神色紧张而且激动。痖白接完电话,告诉我们说,徐思菲有事,需
要他过去一趟,他建议本次聚会到此为止。诗人之一说,这么晚了,还能有什么
事,无非就是上床嘛!诗人之二说,靠,难道上床不是事情吗?痖白说,肯定有
什么事,要不然,她不会这么晚打电话来的。评论家用尖细的嗓子说,你不是还
要请我们找小姐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作家之二也附和说,就是就是,你挣
那么多版税,我们要是不帮你花一花,怎么好意思!痖白说,改天一定请大家,
今晚失陪,不好意思。
实际上,大家玩得已经很是尽兴;不过开开玩笑而已。很快,大家各奔东西。
痖白要我和他一起去见徐思菲。我说,你去约会,我去干什么,我不去。
痖白说,你陪我去吧――我担心她那里有什么事。
痖白喝了不少的酒,说话的时候老是摇摇晃晃;他比我喝得多多了。我看着
他的样子,心里琢磨,陪他去也好,一个人路上不太安全;要是徐思菲没有什么
事情,我回来便是。痖白很在乎徐思菲,在乎得让人惊奇;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
他就会很失望。
我们站在酒吧外面的马路上等车。他们早已经作鸟兽散了。除了我和痖白,
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确定有多晚了,也许有12点了吧。我们站在那里。痖
白没有说话,只是在地上走来走去。空气里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我看着他,忍
不住想笑。他那种激动的样子,看上去很滑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可笑的缺点,
他那么在乎徐思菲,在我看来,正是他的缺点。
柳小颖(1 )
徐思菲住在城市中心的一栋高层建筑上。建筑底层有一家以出售昂贵服饰闻
名的大型商场,还有一家夜总会,同样也在城市享有大名,它聚集各类先锋人士、
流浪艺术家、地下音乐工作者、高级妓女、摇头丸服用者,以及到本地走穴的影
视明星等等;某一次在全城造成巨大恐慌的黑帮火并事件也在这里发生。而最具
影响力的则是在此地举行的色情表演,据说有俄罗斯和美国美女不定期进行脱衣
舞表演,这些金发美女并非草台班子出身,都是夜总会空运而来的优质美貌舞女。
虽然门票昂贵,仍然观者如堵。
我没有去过这家夜总会,所以我无法详细描述其间的盛况。在好莱坞和欧洲
的某些色情DVD 里,我倒是看过许多类型的色情表演和舞会,我想,应该和此地
的情景仿佛吧。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男人而言,色情总是蛊惑人心,那些裸露的
肉体,满足了多少平庸男人的想象和虚荣啊。
我和痖白到达这座建筑跟前的时候,夜总会里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一
些衣装暴露的女人进进出出,空气里充满荷尔蒙的气味。我们走进楼道,电梯已
经关了。我们就顺着黑暗的楼梯爬上去。徐思菲住在22层。大约到8 层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楼梯口哭泣,他的手里还有一个酒瓶。他哭得很伤心,看
样子喝多了。我们出了一身的汗,总算爬到了22楼。
柳小颖打开了房门。我看见灯光里的柳小颖,心里忽然就那么咯噔了一下。
柳小颖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我心脏里的某个阀门。我听见血液在自己的身体里迅速
的奔流。真是很奇怪啊。我原先就根本没有见过这个名叫柳小颖的女人。我们其
实是第一次。我看着她。有一会我只是看着她,不知所措。
进来吧,她说。
我们走进去。
客厅很宽阔,靠窗户的一面被红色的落地窗帘完全笼罩。我看见柳小颖被红
色光影漫过的脸。我们像是置身于一间摄影暗房里。我们坐下来。柳小颖给我们
倒水。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瘦。
徐思菲呢?痖白说,她怎么了?
她睡着了,柳小颖说,其实现在没什么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给你打电话之前,我们在喝酒,柳小颖说。这时她坐下来,在我身旁的沙
发上。有一些头发滑到她的脸上,她把它们捋到后边去。我看着她。她对我笑了
一下。我的心又跳起来了。我听见它通通通的声音。
本来我们都很高兴,柳小颖说,我们还说要玩一个游戏呢;我们喝了一大瓶
红酒,喝完之后,她又拿来一瓶,我说,我们玩游戏吧,酒别喝了。徐思菲不同
意,我们就接着喝。她其实已经喝的很多了,我还以为她是高兴才这样的,本来
她就是高兴嘛。然后她告诉我说,她想见你。我说太晚了,她说,没关系,他知
道你会来。她就给你打电话。我说那我就回去吧。她说不行,要我还在这里。我
想等着你过来,我就回去。突然,她哭起来了。她突然变得很伤心。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伤心,我甚至
还没见过她哭呢。我就去拿毛巾,结果看见她倒到地上了,在地上爬来爬去,手
里还拿着酒瓶子。我在地上拉她,想把她弄到沙发上,她还在哭,等到我把她弄
到沙发上,她睡着了。她的衣服弄得很脏,扣子也掉了,我就想干脆把她弄到床
上去吧,这样她会舒服一些。我就把她弄到床上去了。她睡着了。现在她还在睡。
――你去看看她吗?
痖白到徐思菲的卧室里去了。我坐在那里,为柳小颖的讲述着了迷。对于我
来说,也许我根本不关心徐思菲为什么要这么悲伤。我关心的是柳小颖迷人的讲
述。她就像是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人其实原本悲伤,他们
从来就没有快乐过;他们的快乐是假装的。我看见她的那对小小的嘴唇,她的眼
睛里那种轻盈的忧郁。我看着她,我有点神思恍惚。她看着我笑了。她说,你是
痖白的朋友吗?
柳小颖(2 )
是的,我说,我在哪里见过你。
是吗,在哪里?
路上,我说,在路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她又笑起来了。她说,你们写作的人,总是富于想象力,――你是写什么的?
诗歌,散文,小说?
我什么都不写。我是痖白的朋友,在××大学教书,教现代文学课,有时候
还上一点写作课或者文学欣赏课,每周大约上十几节课;我在做一项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叫虚隐的作家,非常优秀,你没有听说过?你当然没有听说过,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没什么好惊奇的。他写得比痖白还要好呢,可是他没
有痖白这么幸运。我的名字叫式牧,就是方式的式,放牧的牧。我没有结婚。我
有一套房子,不过比徐思菲的小多了。我喜欢读书,有时候听听音乐,看看盗版
的DVD。我的电话是――柳小颖看着我,表情非常惊奇。后来她大笑起来了。她坐
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
她说,式牧,你这是在发征婚广告吗?
我只是说我见过你,我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来不会说谎的。
可是我还是很奇怪,我们见面还不到十分钟。
你放心,我是个好人。
这跟你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柳小颖又笑起来了,她说,再说,我也没有
必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啊。
痖白这时从徐思菲的卧室里出来了。他看起来比刚才好多了。他甚至还有点
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坐到我跟前。他看着我们,他说,你们认识吗?
是的,我说,我们原先见过。
式牧在说谎呢,柳小颖说,他大概把我当成别的什么女人了。
我的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女人真是太厉害了。她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可
是那也不是我的错,这个世界太神奇了。许多事情总是那么凑巧。看起来总是那
样相像。
式牧是我最好的朋友,痖白说。他边说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亲昵得
有一点肉麻。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就一定会嫁给他;他是我的兄弟。我
的哥哥。你不知道他有多好。
好肉麻,柳小颖说,你们俩该不是
同性恋吧?
我们大笑。
我们三个人又说了一些别的。这期间,我一直在滔滔不绝。我发现我很喜欢
说话,甚至还变得有些
幽默。比方我对他们说,酒是一种绯红色的翅膀;
迪斯尼的《猫和老鼠》其实表达的是男女关系;诗人写诗的过程类似于手淫,
等等。我自己都还没有想好的时候,这些词语就从我的嘴里蹦出来了,连我自己
都感觉到惊奇。柳小颖一直在笑,她高兴极了,就像是在看一场顶尖的魔术表演
那样。痖白却有一点敷衍的意思了。他故意一个接一个的打哈欠。我当然知道他
的心思。我假装没有看见。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估计应该超过午夜12点了。
柳小颖说,我要回去了。
痖白说,要不,我们就在这里聊天吧,你看,式牧多高兴。
我看着痖白。他的挽留实在是很勉强。他巴不得我们赶紧离去呢。
我也要回去了,我说。
那好吧,痖白说,式牧你要送送柳小颖。
很乐意,我说。
不用,不用,柳小颖说,我离这里不远,一会就到了。
一定要送,痖白说,式牧,你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我说。我看着柳小颖。我说,我是个好人,你放心;我只是送你
到你家门口,——你家里我不去,我保证不去。
你喝多了吧,柳小颖说,我也没有邀请你去我家呀。
痖白哈哈大笑。他一点都不准备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他这么高兴,倒不是
因为我和柳小颖轻佻的言语,而是,他终于得到一次完美的机会。作为投机主义
者的痖白,也许他渴望的就是如此。
我们和痖白就此别过。我们走出楼道,顺着楼梯往下走。
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灯光忽明忽暗。柳小颖的脸一会不见了,一会
又出现了。她的脸看上去毛茸茸的。我闻见她身体上的一种气味。她走得很小心,
好像故意要让我忽略她的存在那样。也许她对于我还缺乏某种信任吧。对于她来
说,我是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我感觉到她的紧张,这恰好形成了一种暗示。
因为这种暗示,我自己居然也有点慌张了,就好像我真的会利用这种黑暗和空虚
一样。这有点可笑。楼道里的风吹过我的眼睛,我发现自己在此前其实有一些醉
意。等到我明白这一点,我又不会说话了。柳小颖的气味传过来,我听见自己的
心脏又跳起来了。通-通-通,它要从我的胸口蹦出来。
柳小颖(3 )
你有点紧张,我说。
有一点,柳小颖说,不过你是好人,对不对?――你自己说过的。
她的这句话把我逗笑了。我站在那里,放声大笑。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我
对自己说,她只是柳小颖,不是别人;也许我真的没有见过她。
楼道里太黑了,我还是拉着你的手吧。
我感觉柳小颖迟疑了片刻;之后,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我抓住她的手。非常
小。手心里出了汗,很湿。我在前面走,她在我身后,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还
是有点紧张。
你见过余楠吗?
余楠是谁?
一个女人,她原先就在这座城市里。
你真是好玩,这座城市里至少有200 万个女人呢。
就一个女人嘛,我说,名字叫余楠,不过我有几年没有见到她了。
几年了?
三年了,我说,准确的说,是三年零三个月十一天。
我明白了,柳小颖说。这时候我们快要走到下边了,街上的灯光透过窗户流
进来,楼梯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