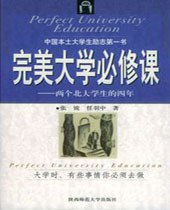大学教授隐秘情欲剖白:非色-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一直在好好说话呢,我有什么不好好说的?我高兴得不得了。
奶奶的,还吹牛,你以为我不知道――大前天是不是嫖妓被警察逮住了?
谁说的?看起来的确是人言可畏,哪里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这时躺到沙发上,点起烟卷,开始舒舒服服的抽起
来,他的一条腿又放到沙发上了。
你又把沙发弄脏了,我说,你就不能好好坐着吗?
他没理我。他说,说说你的事吧。
我就告诉他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当然,我这次的叙述和面对梅若夷的时候
又有所不同。我把女主角换成了沈易欣,因为痖白知道我和沈易欣的故事;所以
我现在的叙述更接近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不过我还是杜撰了一些情节,比方说
我把对手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成为六个,另外,我还延长了搏斗的时间,我告诉
痖白,有一个黑社会身受重伤,如果夜总会的光线更好一些,我还会打到一个。
等等。总之,为了尊严,我真是勇敢过人,无所畏惧。
显然,对于我的叙述,痖白并不相信。至于个中真伪,他好像也缺少兴趣。
他换了个话题说,学校里怎么样?
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事情。
我说,这件事情就更简单了――我根本不会把它当回事:他们爱怎么说就让
他们说去吧。我要好好写一部《虚隐评传》,写得和你老人家的《迷》一样好,
我才不在乎职称什么的呢――教授比驴还要多,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写
《虚隐评传》的可就我一个了,你说是不是?
佩服佩服,痖白说,大学里有你这样的人,也就多少还有点希望了。
别那么肉麻,我说,说说你的事吧。
我们就这样互相嘲讽,插科打诨,但是我能看得出来,痖白几乎有些焦头烂
额;他被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反复纠缠。作为被告,他必须出庭参加诉讼;作为
名人,他还要躲避报纸花边记者的追逐;更加可笑的地方在于,在他供职的研究
所里,有人居然列出一张非常详细的人物对照表,标明作品中的某某就是现实中
的某某,并且把同样的表格到处张贴。他接到很多个恐吓电话,其中一个电话要
求他在某时某地送出人民币若干元;有一次他差一点被车撞死;他宿舍的玻璃某
一天被突然飞来的一块石头砸碎;有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女人来向他索要青春损
失费,等等。总之,他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这些事情他都可以忍受,也可以等
闲视之,令他倍感无聊的地方在于,他的汉语文学奖的评审资格忽然被取消,原
计划进行的下一部小说的写作无法继续;在媒体评论中,他原本小说家的身份被
重新命名为色情
纪实文学作家。另外,他被告知要实行坐班制度,他的领导建议他到某地去
进行一项为期一年的、关于基层文化馆建设的课题研究。
真他妈无聊,我说。
痖白(2 )
奶奶的,痖白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要走啦。
去哪?
北京,或者广州,那边有好多朋友呢,我准备做自由撰稿人,吃饭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我最近就过去看看,奶奶的,先弄一套房子再说。
能走就走,这么个破地方确实没什么好待的。
可是我舍不得你,干脆我们一起走算了。
别拿这好听的蒙我,你是名流,我是什么呀?一个学术骗子,连教授都不是,
我跟你去混,还不饿死?再说,你哪里舍不得我?你是舍不得女人吧?
高明。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我要是女人,我一定嫁给你。
你就不要遮遮掩掩的了,你上次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是不是和
徐思菲有关啊?你还是有屁就放的好,你没看我在忙吗?
他看着我,看上去疲倦极了。
是有点事,他说,这事只有跟你说了。
我听着呢,我说,你就别吭哧吭哧的了。
徐思菲怀孕了。
我看着他。
我说,好事啊,那你们就结婚吧。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明白了,我说,她怀孕了,不是你的种,是不是?
是。
那你瞎操什么心?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不想要,他说,她想做掉。
那跟你更没有关系了,是哪个男人的,她就去找哪个嘛。
她跟那男人分手了。
他们分手了,你就有机会了是不是?那谁知道啊?她那种人就跟婊子一样―
―痖白突然跳起来,就像一根刺刺着了他的骨头那样。他瞪着我,眼睛里全是愤
怒。他说,你简直胡说八道。
好好,我说,就算我没说好了――可是那也不是你的事,她应该――她在哭,
痖白说,哭得很厉害,我是担心会出什么事。
哦,那你就带她去
医院嘛。
我本来是这样想的,我想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帮帮她吧。可是,可是她不愿
意见我――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她就一直在电话里哭;我说我来看你吧,她说
不行,她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那天我想告诉你这事,又一想,也许我自己能解
决,所以没有说;可是这两天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干脆不接我的电话了。我用
别的机子打过去,她一听我的声音就挂掉了。后来就干脆关机,她把家里的电话
线也拔掉了;我去了她那里,她就在房子里,可不管我怎么敲门,她就是不开―
―我想她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你说,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看着他。他吃吃艾艾、惊惶失措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狼狈。唉,他遇到的事
情本来已经够多的了,又加上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
严重;也许比其他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不会的,我说,还能有什么事?你就让她自己安安静静待上几天,也许她自
己就会好起来。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他说。他在那里拼命地摇头,就像是吃了摇头丸那样。
他说,她已经把自己关房子里三天了,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出事的。
我看着他。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你跟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你可以的,他说,这种事我也只有对你说了。
可笑,她连你都不见,我算老几?你也太抬举我了――她总共就见过我一两
次,说过三四句话,就算她肯见我,也未必能认出我来呢――你要是去砸她的门,
我倒愿意帮忙,干这个我还行。
我说真的呢,痖白说,她也许会听你的劝――就算你帮我的忙,好不好?
这事情真他妈荒唐,我说,你是她什么人啊,就这么屁颠屁颠地替她张罗?
人家既然不愿意见你,你又何必勉强自己呢?你就干脆别理这事了成不成?天下
好女人多得是,你又何必――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我忽然看见,痖白的红眼睛居然显得湿漉漉的了。说实话,我的心里也不免
有点伤感。
痖白(3 )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哭哭啼啼的干什么?
他看着我,笑起来了。他站起来,伸出两条手臂,抱住我。
奶奶的,他说,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我不喜欢徐思菲我答应了痖白去找徐思菲,就好像我就是救世主,可以挽救
他的爱情。实际上很可能于事无补。我不过是在虚应风景。一切都已经发生,流
水一样远去的东西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忍受不了痖白
的忧郁。我一直都不明白,痖白为什么会喜欢徐思菲这样的女人。但是人世间的
许多事情往往不可理喻,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原因呢。比如我自己,一直在等待一
个名叫余楠的女人归来,也自以为庄严、宿命、不可改变,可这与别人何干?他
们甚至会认为荒唐呢。痖白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要紧,超过他生活里的许多事物,
我当然愿意尽力而为;如果我可以让痖白稍感欣慰,可以让他纷乱的念头归于平
静,又何须惮于精力和时间?
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徐思菲。无论她有多么风流妩媚,也无论她与痖白走得
有多近;即使她真的爱上痖白,我还是不会喜欢。我喜欢简单的女人。她们放浪
也罢,羞涩也罢,每当她们从我的生活里出现,我都可以闻得见她们的身体所散
发的干净的芳香;她们带来的和带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徐思菲则与我所见过
的女人截然不同。她过于复杂了。她把生活里的许多事物都当作是舞台上的表演,
她是导演,也是演员。她仿佛很多时候都在观赏自己的演出。她好像从头至尾都
把自己放置于一出剧本中。生活里盛装演出的女人也许很多,但是徐思菲的高明
之处在于,当她表演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出其中的破绽。她扮演的就跟
真的一模一样。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徐思菲也许喜欢我,至少不会觉得我讨厌。但是那也不表示我们可以有多亲
近,只不过是由于我们彼此毫不相同的生活,以及我们彼此感觉到的陌生。
现在,我要面对徐思菲,这个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女人。如果我见到她,我
该怎么说?我会说些什么呢?
式牧和保安(1 )
我乘电梯上楼,到22层之后,出了电梯,来到楼道里。我曾经和痖白一起到
过这里,那是深夜时分,我只是感觉到黑暗和幽深;现在,楼道里光线明媚,空
气里浮现某些花朵与香水的味道,安静而且奢靡,仿佛某种暗示,令人对于那些
坚固华美的金属门里所隐藏的生活,想入非非。
我沿着楼道里的气味走到2208号门口。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自己的
脚步声。我站到门口之后,点了一颗烟卷,我听见烟丝燃烧的声响,看见烟雾在
空气中冉冉上升。徐思菲就在她的房子里,我能够感觉得到。但是,我忽然有一
点紧张和不安。这里的一切气味都显得可疑,而我自己看上去一定非常可笑。
等到一支烟卷烧得干干净净,我按响门铃。
我等了有两分钟左右。没有人来开门。但是我知道,徐思菲就在房子里。我
又按了一次门铃。
我又等了两分钟。我于是第三次按了门铃。
两分钟之后,我对着门说,徐思菲,开门吧――我是式牧。
我是式牧,我说,就是╳╳大学的式牧,我们原先见过一两次,你还记得吗?
就那个胖子,痖白的朋友,你应该还有点印象吧。我今天来完全是受人之托,自
己是不想来的――你打开门好不好?我好歹也是你的朋友嘛。
我知道你在里边,我说,你打开门好不好?
徐思菲还是不肯开门,这让我有点生气。我就又点了一支烟,在门口走来走
去。我在想用什么办法可以让徐思菲开门;有一会我甚至有一走了之的念头。她
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又能怎么样呢?她的房子里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即使一个人
足不出户两周,也一点都不会饿着;难道她会自杀吗?那就更不可能了,只有愚
蠢的女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徐思菲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她才不会拿自己
的身体开玩笑呢。但是,我要是就这么离开,我该怎么向痖白交代呢?痖白可以
不在乎很多事情,他对待它们可以像一条鱼那样游弋自如,但是唯有这件事,他
愚蠢固执得仿佛一头牛。何况,我已经答应了痖白,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弃。
等到我手里的烟卷抽完,我伸出一只拳头,用力敲起了门。这次我不想按门
铃了。门铃里响的居然是著名的《婚礼进行曲》,因此我每按一次门铃,就会觉
得滑稽,就好像自己在演戏。
我用拳头敲了六下。之后我说,徐思菲,你开不开门?你要是再不开门,我
就要把门撞开了――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见一张巨大的脸。
本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胖子了,但是这家伙的块头更吓人,简直有我两个这
么粗。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有发现。他就跟恐怖片里的鬼一
样。他穿了一身警察一样的衣服,另一只手里提着一根电棒。
我盯了你好长时间了,他说,你是干什么的?
他一说话,我就忍不住要笑;他的身躯如此庞大,声音却像是一个有气无力
的女人。
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盯我干嘛?
我是干什么的,你真看不出来?他说。他看起来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伸出
一根指头指了指自己的胳膊,示意我往他那里看。那里有保安两个字。其实我早
就看见了,只是装作没有看见而已。
我找徐思菲,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他说。他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电棒晃来晃去,看上去特别滑
稽。
我是她什么人你管得着吗?
你还挺牛,他说。他有点生气,往前走了一步,大肚皮几乎蹭到我身上来了。
他说,我当然管得着,我要为每一位住户负责,你刚才嚷嚷什么?你要撞门?你
凭什么要撞人家的门?
看着他这么牛逼哄哄的样子,我也有些生气。我说,我想撞就撞,关你什么
事?
越说越不象话了,他说,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最好老实一
点,要不然,你知道我会怎么收拾你吗?
式牧和保安(2 )
不知道,我说,也不想知道。
胖子很生气。他摇着手里的电棒,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还呼哧呼哧的喘气。
他说,你有本事你就撞门,你撞呀,撞呀。
本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撞门,再说,那么结实的门,我撞了也是白撞。但是
我看不惯胖子神气活现的样子,他简直就像是徐思菲养的一条狗。于是我想,我
就偏偏撞给你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朝着门冲上去。
我还没撞到门,胖子的一只手就把我抓住了,差一点就把我拎到空气里去。
他说,跟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