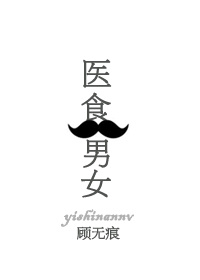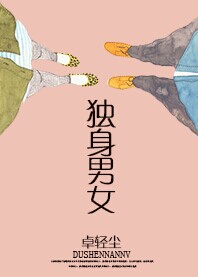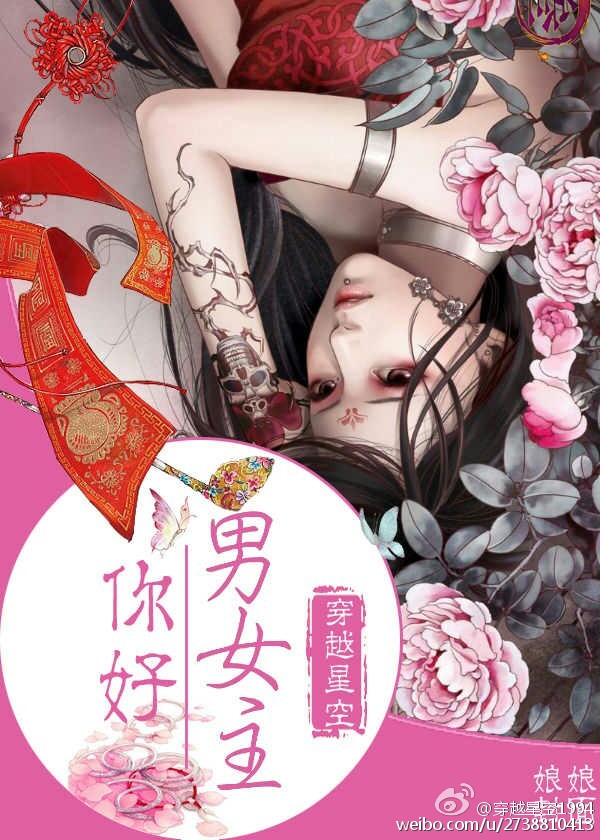饮食男女-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论是茶或咖啡,咖啡馆或茶馆或茶餐厅,其实都表达着同样的生活态度,只是〃姿态〃或道具不同罢了。茶就是广州人的咖啡,或者说,用对待茶的态度去对待一杯咖啡,得到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广州人从来不说〃咖啡〃,而是习惯于像〃茶〃那样说成单音节的〃啡〃,黑咖啡是〃斋啡〃,咖啡色叫做〃啡色〃,喝咖啡自然就是〃饮啡〃,潜意识里已把〃饮啡〃等同于〃饮茶〃。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广州人把喝净了的咖啡壶盖仰天打开待续,然后在服务生替他的咖啡续杯时伸出并拢的食指和中指礼貌地在桌面上敲敲这一切,似乎一点也不妨碍〃壶中岁月长〃这种流逝着的幸福。
惹火尤物
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里奉荔枝为〃果中尤物〃,比之于〃蔬中笋,水族中之蟹,饮食中之酒,天文中之月,山水中之西湖,文字中之词曲〃。
林是漳州人,该地自唐代起便盛产荔枝,故其说便多少有些〃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的意思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经学家或道学家也好,才子还是革命者也罢,只要他是广州人,相见的第一反应,必定是口水泉涌,紧接着便有一把禁欲之火由丹田而咽喉〃呼〃地蹿至全身,使他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煎熬和焦虑之中。
荔枝美味,吃多了却容易上火,算是个顶级的〃惹火尤物〃。这种反应在岭南的水土环境中尤为显著。故〃上火〃和〃灭火〃、〃中毒〃和〃解毒〃,就是广东人与荔枝之间最基本最身体的关系。徐志摩在1931年7月4日写给〃眉眉至爱〃的信中介绍了广东人的降火经验:〃卢经理推荐了家乡生熟地汤,黑乎乎的汤上来了,我一连喝了两碗,果真是解腻……卢经理说广州人吃什么总是热气,就说荔枝,'一颗荔枝三把火',吃多了就上火,可在东莞没听说热气不能吃的东西,荔枝无论吃多少一点事也没有,这是什么道理呢?想来想去,关键在于家中老人代代相传的家乡汤。〃(《爱眉小札》)
所以广州人对于荔枝向来是爱恨交加的。这种态度,与中国文人就荔枝所达成意识形态共识倒是不谋而合。一骑红尘,祸水红颜,大唐江山竟毁于一炬情欲和荔枝的毒火,妃子一笑,可怜焦土。《隋唐》第九十一回甚至还有一段更煽情的演义:〃杨妃既死……玄宗命高力士速具棺,草草的葬之于西郊之外,道北坎下。才葬毕,适南方进荔枝到来。玄宗触物思人,放声大哭,即命以荔枝祭于冢前。〃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想那李隆基彼时的处境,定不是〃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所能道尽。睹的是物,思的是人,缺的仍是对荔枝的反省。克尔恺郭尔说过这样的话:〃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其实对于人体来说,荔枝既属于先天性的〃高度易燃物品〃,同时也具备了一种反省及自我反省的天赋异秉:荔枝之〃热〃,之〃上火〃,肇事者乃是其肉,它的皮、核,却是大大地〃清热解毒〃,也就是说,每一粒荔枝也〃都是辩证的〃,人欲灭其火解其毒,其实用不着喝汤饮凉茶,在那个〃反省的海洋上〃,可以直接向纵火者请求救火:以荔枝核煎水服用,可散寒祛湿,〃配橘核焙焦为末,开水冲服〃,还可治疗胃及睾丸肿痛(《滇南本草》)。如果你吃的是无核荔枝,不妨以荔枝壳煮水,饮之亦可降火无碍。假如有一天创意无限的广东荔农育出了无核无壳的新品种,你就认命罢了。
呜呼!灭荔枝之火者,荔枝也。在荔枝的娇躯之上,一发体现了生火和灭火,中毒及解毒,反省或辩证。万物如此,荔枝如此,男女亦无出其右。至少,对于像程灵素这样的女人来说,爱有多么铭心,下毒就有多么刻骨。男欢女爱结出的果实,从来就是这么一颗〃抱阴负阳,相生相克〃的荔枝。如果小杜的《过华清宫》和女姐的首本名曲《荔枝颂》应属荔枝之通行证,那么,圆性在程灵素坟前轻声念出的八句佛偈,是不是可以借来做墓志铭一用?偈曰:〃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十八春(1)
生煎馒头是上海的一种市井小食。我只要听到这个词或者见到这四个字,就好像闻到了弄堂的味道。犹如爱晕船的人,一旦把船票拿在手里,明明还在陆地之上的身子以及明明还在身子上的脑袋,便如那不系之舟,飘摇并晕眩起来。
凡是市井的东西,第一不登大雅之堂(据我所知,在某些大雅之堂里,生煎馒头其实是老板或主厨的私淑),多在弄堂口的摊子上现煎现卖。第二必须便宜,二十年前生煎馒头卖一毛八一两,二十年后涨到一块八一两,已经算是同类产品中的名牌,通常的售价是一块五一两,贱不过一块二,贵不过两块二,价格上差异不大,分量上却一律都是四个一两。两三块钱,就能填饱自己的肚皮;花五块,全家不饿,拍下十块,便可以做东请客了。
古龙在小说里写到,胡铁花坐在小茶馆里等楚留香,一次能吃下两笼蟹粉汤包,二十个生煎馒头,〃又就着一碟麻糖喝了两壶茶〃,纯属小说家言,而且是男小说家言。较为〃在地〃而市井的小说家言,终究还得看张爱玲的。《十八春》里写到做舞女的曼璐〃是有吃宵夜的习惯的〃,一天深夜回家后正吃着翻热过的生煎馒头,忽然听见楼上的母亲还没有睡,〃当时就端着一碟子生煎馒头,披着一件黑缎子绣着黄龙的浴衣上楼来了。〃〃曼璐让她母亲吃生煎馒头,她自己在一只馒头上咬了一口,忽然怀疑地在灯下左看右看,那肉馅子红红的。她说:'该死!这肉还是生的!'再看看,连那白色的面皮子也染红了,方才知道是她嘴上的唇膏。〃
张爱玲笔下的红色,肉感而不祥,市井而荒凉,华美而蚤子。除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以及胸膛上的一颗朱砂痣,张迷们可能还未发现这染红了生煎馒头的肉馅和面皮的唇膏。在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电影《半生缘》里面,梅艳芳扮演的女二号曼璐真真切切地表演过吃生煎馒头,算是港产片里难得一次的忠于原著。虽然〃十八春〃这三个字不合拍电影的时宜,倒是很适合用来做一间生煎店的名号,〃半生缘〃就免了,开间牛排馆还差不多。其实〃十八春〃也好,〃半生缘〃也罢,跟生煎馒头都不怎么搭界,我拉的这个皮条,主要是替我那些热心好客的上海朋友们的荷包计,希望从今往后,只一二碟生煎便可打发三五个专程来吊膀子的小资游客。
上海话称包子为馒头,故生煎馒头实为生煎包子。(北包南下,自动降了一格,似有拿豆包不当粮食,拿村长不当干部之意。但一想到他们拿白开水叫〃茶〃,天底下也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梁子了。)是包也,大小若高尔夫球,观之憨态可掬,〃生煎〃之名听起来却像一种传说中的酷刑,其实也就是先用半发酵(小发酵)的面皮包了肉馅,放在平底煎锅上油煎,喷水若干次即熟,与锅贴浑似。起锅时,还要洒上白芝麻和葱花。香港的上海馆子里有一种先蒸后煎之法,实属邪道歪门。生煎生煎,要的就是〃生〃,也就是现场直播,现煎现卖的那种感觉,Live。不管是先蒸后煎还是先煎后蒸,乃不专业并且蒙事儿的〃较早前录影〃,皆了无生趣。
对于一只优秀生煎馒头的评价标准有三:现煎现卖;肉馅鲜嫩并有汤汁;底部黄脆不焦,且不可过厚。
欲摸高,先探底。对于生煎馒头在筑底方面的特殊要求,形成了它与锅贴之间的一个重大分野。此底断不同于比萨饼,厚薄各有所爱。一个好底,须得硬香带脆,黄脆不焦。除了面粉之外,它的形成直接和火候有关。过了便厚而枯焦,不足则软而塌塌,也就是北京人说的〃底儿潮〃。急火油煎时若始终使生煎馒头的底部着锅,则大面积焦斑生矣。故生煎馒头在生煎工艺上讲究的是〃底朝天〃,或者在生煎的途中帮助馒头改变一下体位,至少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但是为了效率或者偷懒,现在已很少有人这么干了。
在生煎馒头的内部,汤汁是成败的关键。鲜美无比的汤汁,主要源自肉馅,其次是拌馅时邀适量肉皮冻作为外援加盟。面皮之所以非半发酵不可,目的也是不欲因发酵而吸尽了馅内的汤汁。
十八春(2)
按此标准,据说吴江路小吃街东段的〃小杨生煎馆〃是全上海生煎界的〃三好〃楷模。我一个人踅到店门口,正是晚饭时间,一片〃煎声〃之中,已排了十几米长的人龙。附近的〃王家沙〃,号称出品上海最好最贵的生煎馒头,刚才经过时却见它门庭冷落,小猫两三只,莫非这姓杨的比那姓王的确实有点花头?难怪最近连《华尔街日报》也赶来捧场凑热闹。
刚起锅的生煎要了二两,端着搪瓷盘子,挤进脏兮兮的店里面壁而食。嗯,皮薄,底子也恰到好处,至于汤汁,有,不仅有,而且大大地有,分外地多,有到不仅可啜,可吸,而且多到可饮,甚至可喷,可射。我的意思是,这些汤汁在保障供给了我之食用之外,富裕出来的部分尤可作游戏之用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一小口下去,一股又浓又热的汤汁破皮而出,飞流直上,命中吾眼。用手一擦,又觉手指似已粘满胶水,遂眨眼不迭,以防眼皮粘住。对付第二个时便有了经验,用不着温习流体力学的理论,只需先将此即将被引爆物品置于危险距离之外,再使筷子尖小心挑开一洞,抓住时机,扑上去连续大口吸吮三至四次,待确认汤汁已尽,不会射己,更不至喷人,才可放心大嚼。
前面已经说过,以我之所见,汤汁宜从肉馅和调味中自然而出,除了增加黏稠度之外,肉皮冻只是辅助或引子。广东话形容一个人风骚,有所谓〃出汁〃的说法,其实不管是〃出汁〃还是〃入骨〃,意思都只能是自然的流露和渗透,汩汩然溢润于齿颊之间,一种和〃分泌〃相似的现象。〃出汁〃和〃分泌〃都是有来由的,以和馅时绝不手软的肉皮冻投入而导致的汪洋恣肆,已经不能算内分泌而是外分泌,即使算它是内分泌,也肯定严重失调的。好不容易摆脱了锅贴,却又主动向汤包看齐。早知道汤汁多到走火入魔,那碗劳什子咖喱牛肉汤便越看越显得多余。
不过这种事也不能全怪店家,由于现在市面上的劣等生煎馒头通常以干涸著称,那么生煎对汤汁的要求就是食客对生煎的要求。人欲既已横流,汤汁能不滥觞?我在〃小杨生煎馆〃门口排队时,曾见一女熟练地先用筷子戳破生煎,挑肉出,再把生煎内的汤汁一滴不剩地倒掉。此种行为,有行家痛心疾首地斥之为〃洋盘〃,而今看来,亦不失为女子防身术之一种。
胡兰成认为,张爱玲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即〃处理事情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今生今世之民国女子》里提到她有一次在上海街头遇到瘪三抢她手里的生煎馒头,一半落地,另一半她还是连纸包一道〃紧紧的〃抢了回来。设若张爱玲时代沪上生煎馒头名店如〃大壶春〃或〃萝春阁〃的出品也是如此多汁,瘪三依然要抢,淑女必然会争,但是〃小馒头〃们却断然经受不起,汤汁四射,一塌糊涂。张爱玲即使免遭颜射,素手还是很有机会和瘪三的手粘在一起,世俗是够世俗的了,〃清洁〃却无从谈起。
吃醋(1)
如果要在四才子书里寻找味觉,《三国演义》乏味至极,《水浒传》则酒气冲天,《西游记》的每一回里都飘荡着水果、斋食以及期待中的人肉之味,而把吃食铺陈得最为丰富的虽然非《红楼梦》莫属,钟鸣鼎食,百味杂陈之中,却有挡不住的酸味逼人。
这阵子酸味直接来自于醋。这醋也并不指的是菊花蟹会里的那种,彼醋,实醋也,《红楼梦》里最酸最精彩的醋,乃是男女间互相吃来吃去的醋,属于虚醋。曹雪芹先生并没有在字里行间掉书袋的习惯,却刻意地打翻了许许多多的醋瓶子。正是因为这些被打翻在地的醋,才令《红楼梦》这本书在味觉上愈发地错综复杂起来。
虽然〃吃醋〃的典故出自《朝野佥载》,但是据学者考证,第一次把〃嫉妒〃与〃醋意〃合用者却始自《红楼梦》的第三十一回:〃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
晴雯在大观园里当然算不上最能吃醋的,真正的〃醋后〃是林黛玉,虽然林黛玉自称〃从会吃饮食就会吃药〃,照我看,她不仅〃从会吃饮食就会吃药〃,而且很有可能是〃从会吃饮食就会吃醋〃的。
古龙说:〃看来女人若是有了吃醋的机会,她也是绝不肯放过的。一个女人若已开始为男人吃醋,那就表示她对这男人至少并不讨厌。可是你如果想要一个女人不吃醋,那简直是做梦。〃男女间的醋皆由爱而吃,其实与性别与个性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像林黛玉这样在公众场合一贯是想说就说的女人,也只有在宝玉的面前才会突然转了性,把好好的一句大白话偏要扭成八截来说,〃吃醋使性的闹〃。
假摔
吃醋的典故,出自唐人张之《朝野佥载》:唐太宗有意赐宰相房玄龄几名美女为妾,房不敢受,只因夫人嫉妒心重。唐太宗得知后,便召玄龄夫人前来,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意思是说,要玩嫉妒的话,就得饮毒酒而死。谁知房夫人面无惧色,接过毒酒,当场一饮而尽,以示其〃宁死而妒〃的决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李世民所赐的毒酒其实只是一壶醋。从今天的政治标准来看,玩笑开得是大了点,不过以中古时代的君臣关系,依然算是一个甜蜜的玩笑。
适当的吃醋,有助于男女间亲密关系之调剂,能使感情游戏的娱乐性更加丰富;过分的吃醋,后果其实与毒酒无异。什么是〃适当的吃醋〃呢?我们还是要把最善于吃醋的林黛玉拿出来举例。欲精确拿捏吃醋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