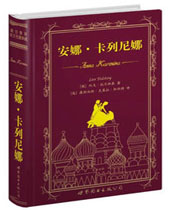安娜.卡列宁娜(上)〔俄〕列夫.托尔斯泰-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50
841安娜。 卡列宁娜(上)
“这有什么要紧呢?
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
哦,那有什么呢?
难道在我与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可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 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了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 她感觉到她的神经好像是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越拉越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与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半暗的灯光里面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 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楚火车是在往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 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
“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个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的思维正处于完全的混乱状态,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 但是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顺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 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 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可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令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与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好似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
151
安娜。 卡列宁娜(上)941
切都遮住了。 安娜感觉到好像自己在沉下去。 但是这并不可怕,可是愉快的。 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 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 她让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朝门口走去。“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是,我想透透气。 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了门。 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可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 风在踏板上是很强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 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到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与灯火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叫着,冲击着。 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 风暴平静了片刻,以不可抵挡
152
051安娜。 卡列宁娜(上)
的风势猛烈地刮起来。可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他们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见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面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八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喊叫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 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了她身边,遮住了路灯的摇曳的灯光。 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 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注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与眼睛的表情。 那崇敬的狂喜的表情是那么地打动她。 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便是刚刚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以遇见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叫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 她无须问他为何来到这里。 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我不知道您也去。 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制不住的欢喜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里去,”他说。“我没有别的法子呢。您是那亲样地吸引我。”
153
安娜。 卡列宁娜(上)151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掉了的什么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的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惋而又阴郁地鸣叫着。 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可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 她没有回答,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他很矛盾。“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便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是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许久答不出话来。“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如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说了。“您的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它们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注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 可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像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令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 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上坐下。 从前苦恼过她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睡。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像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
154
251安娜。 卡列宁娜(上)
方;相反地,而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 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儿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 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即袭上了她的心头。到达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
他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令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 他的嘴唇挂着他时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满眼疲惫地看看他。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悦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 特别令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 那种情绪,在她同她丈夫的关系中她是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似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又痛苦地意识到了。”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看你都快望穿秋水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语的人的声调。”谢廖沙十分好吗?“她问。”这便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
连一句问候我的话都没有,“他说,”他很好,很好……“
155
安娜。 卡列宁娜(上)351
三十一
弗龙斯基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要睡觉。 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候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的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而自满了。 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厌恨他的这副神气。 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龙斯基凝视着他,正象他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做了个鬼脸,感觉到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作人对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弗龙斯基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 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结局会怎样,他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 他感觉得他从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 他为这感到幸福。 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她: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
156
451安娜。 卡列宁娜(上)
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到她和听她说话。 当他在博洛戈沃车站走下车去喝矿泉水,一看见安娜就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便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了。 他把这个告诉了她,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这个了,他觉得很高兴。他整夜没有入睡。 当他回到车厢的时候,他尽在回忆着他看到她时的一切情景,她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他的想像里浮现出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他的心激动得要停止跳动了。当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的失眠症状一扫而空。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她出来。“再看看她,”他自言自语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说,“我要再看看她的步态、她的面貌,她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可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见了她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他穿过人群。“噢,是的!丈夫!”这时弗龙斯基才头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深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到了他本人,看见了他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者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看见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与严峻的自信的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这样一种不快之感,就好似一个渴得要死的人走到泉水边,却发见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在饮水,把水搅浑了的时候感觉到的心情一样。 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龙斯基难受。 他以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
157
安娜。 卡列宁娜(上)551
利。 但是她还是那样,她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令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里充满了狂喜。 他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她跟前。 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景,并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她对他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他心里断然了。在他从后头走近安娜。 阿尔卡季耶夫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她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可是认出他来,却就又转向她丈夫。“您昨晚睡得十分好吗?”他说,朝她和她丈夫一并鞠躬,让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他认不认得他,就随他的便了。“谢谢您,很好呢,”她回答冰。她的脸色露出倦容,脸上那股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神里面流露的生气,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一刹那间,当她瞥见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那闪光转眼就消逝了,可是他在那一瞬间却感到了幸福。 她瞟了丈夫一眼,想弄清楚他认不认识弗龙斯基。 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满意地看了弗龙斯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个人是谁。 在这里,弗龙斯基的平静与自信,好像镰刀砍在石头上一样,碰在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过分自信上。“弗龙斯基伯爵,”安娜说道。“噢!我想我们认得的,”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伸出手来。“你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
158
651安娜。 卡列宁娜(上)
他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似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说,不等到他回答,他就用戏谑的语调对他的妻子说:“哦,离开莫斯科的进修你恐怕很难过吧!”
他这样向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她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他,他触了触帽边;可是弗龙斯基却对安娜。 阿尔卡季耶夫娜说:“期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倦的眼睛看了弗龙斯基一眼。“欢迎,”他冷淡地说。“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随后,完全撇开弗龙斯基,他向他妻子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他用同样戏谑的口吻继续说。“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啰,”
她用同样的戏谑口吻说,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在他们后面的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吗?”她暗自说,于是开口问她丈夫她不在候时谢廖沙可好。“啊,好得很呢!
Mariete说他很可爱,并且……很抱歉,我说这话可能会让你有点伤心……他可并没有由于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 但
![(安娜·卡列尼娜同人)名流之家[安娜]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0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