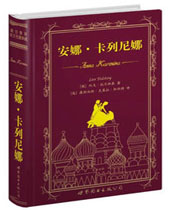安娜.卡列宁娜(上)〔俄〕列夫.托尔斯泰-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咱们别再谈尼尔生了!
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位穿着旧绸服、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 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与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可怕的娃娃“。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儿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
197
安娜。 卡列宁娜(上)591
样喜欢那句话。“
讲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
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smaltalk那类文雅的谈话艺术的。 她这话是对那个外交官出的,他此刻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可是我来试试看。 给我一个题目吧。 关键全在题目。 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 我经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语来的。 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了他。谈话开始得很文雅,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 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LouisXV的风度吗?”
他说,朝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的青年男子看了一眼。“啊,对啦!
他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响应,原来他暗示的在这个客厅里是不能直说的——那便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新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便是恶意的诽谤上。“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定制了一件diablerose衣裳吗?”
“不会的!要不那真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
198
691安娜。 卡列宁娜(上)
她竟然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悦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如燃烧着的篝火一般。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的男子,一个酷爱搜集版画的人,听到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以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您喜欢尼尔松吗?”他问。“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
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讲您的陶器和版画。 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些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但是您在这方面是外行。”
“啊,给我看看吧!
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
……
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着精美的版画。 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
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道。”是的,machère。他们请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饭,而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会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全都很满意。 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她真是了不起呢!”女主人说。“真了不得呢!”又有谁说。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总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
199
安娜。 卡列宁娜(上)791
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 在她所处的社会里面,她的这种话语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的效果。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并且利用它。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往公使夫人说:“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儿很好,”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经谈开了的话题。这是很愉快的谈话。 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 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道。“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的阿列克谢。 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哦,那有什么?
格林有个童话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 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 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 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呢。“
“是的,可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烂掉您的舌头!”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忽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 我不喜欢她丈夫,但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何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 “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如他那样的政治家
200
891安娜。 卡列宁娜(上)
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可是我不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设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傻瓜。 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到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不以为是我自己笨,所以看不出来;可是我一说,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便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儿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 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可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
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格言。“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 她是那么可爱,那么魅人。 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的时候,那她有何办法呢?”
“我可不想说谁的坏话呀?”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假设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十分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儿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201
安娜。 卡列宁娜(上)991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道。“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了一番鉴定,”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边坐下说。“可惜我们没有听见。”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天天同大家见面;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如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哦,没有法子了,我只好自白了。 看滑稽歌剧来哩。 我深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 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可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收场,而且津津有味。 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可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那种可怕的交情您不要再讲了。”
“好的,我不说,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要是它象歌剧一样流行,我们就都会去看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202
02安娜。 卡列宁娜(上)
七
可以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 他向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 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欠起身。 安娜走进了客厅。 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快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并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 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她只微微地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 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往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可是被她给留住了。 约翰爵士在那儿。 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个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味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又打断了的谈话就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203
安娜。 卡列宁娜(上)102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 我见过他。 他非常健谈。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地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听说这是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纯粹说感情?
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
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道。”有何办法呢?
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但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时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但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 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取得免疫力。”
“那么恋爱跟生活一样,也可以用人工接种咯。”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却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掉,”贝特西公爵夫人说。“甚至在结了婚之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改邪归正从不嫌晚。”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
204
202安娜。 卡列宁娜(上)
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道,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简直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我想,“安娜说,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设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便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 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如脱了险似的叹了一口气。安娜忽然对他说:“啊,我收到了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 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十分重呢。”
“当真吗?”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安娜严厉地看着他。“您不关心吗?”
“不,我很关心。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设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安娜站起身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了安娜面前。“信上说了些什么呀?”他重复说。“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边坐下。“我完全不懂您这话的意思,”他说,递给她一杯茶。她瞄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205
安娜。 卡列宁娜(上)302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看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不好吗?但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何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又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发窘的不是他,而是她。“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 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因此害怕他的缘故。“您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
“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道,发抖了。 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并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定地望着他的眼睛,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儿可以遇到您。 我来告诉您说,这应该结束了。 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您要我怎么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我要您到莫斯科去,请求基蒂的宽恕,”她说道。“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他看她说这话很勉强,不是出于内心。“假设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206
402安娜。 卡列宁娜(上)
他喜笑颜开了。“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
但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 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 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 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 我看出将来不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 我看只有绝望和不
![(安娜·卡列尼娜同人)名流之家[安娜]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0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