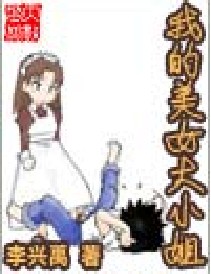女大当嫁 作者:唐清-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凌云一拍额头,大叫不妙。
她,根本忘了安必新对她的拜托,她没有告诉羽裳,闹到这个地儿,安必新是会尴尬的,凌云也会尴尬,而且罪过。
羽裳对安必新说了什么,看样子有丛狠。
安必新低头,依他的性子,也忖不出什么道理。姿态黯然,一甩头,绕过心仪的女孩,跑得飞快,到底惹来了不该的注目,他却不顾,连擦过了凌云和兰娇,也没有察觉。凌云只看得他幽幽的一个侧面,也被洒洒的黑发拢住了太半,眉目怎么转,神色怎么伤,一概是不清楚的。凌云盯着他拉开舞厅的玻璃大门,往外面更广落的院子里冲去,便想也没想,跟了上去。
一出门,却找不着他了,这么文艺腔的男孩子,凌云也是第一次瞧着。
凌云站在阶台上深呼吸,秋凉带桂香,那爽洌甘甜的空气,顺着凌云鼻腔而入,走得欢,也不寻头撞尾的,一下子就掉到了凌云心底深处。凌云仿佛散了气,不愿意重新进去了。
她就地而坐,手肘撑在膝盖头,回望里面折射出的光影行色,处处是一对,影子也是一对,地面上的相拥映射成地板上的浪漫。凌云转头自望,要么是自己坐得静,太零落孤僻了一点,自己的影子,竟然不随着自己。那家伙也是个势利眼,自私鬼,她出来的时候,它留恋在声色场里,没有跟出来。她是壁花,那家伙也找不到影子男友和它配对,寥寥地贴住在墙壁上,呆呆望,只是羡慕。久了,怕也觉着没劲,便委着身子,从玻璃大门下的缝隙里飘忽出来,淌到了她的身边。她问它:怎么不玩了?它说:形单影只,不是你们人类说的?我也觉着尴尬。凌云拍拍身旁的地面,邀它同看明月。它挨着她的身子,只是彼此温暖彼此,让他人看了,会笑,好一对自欺的小娘们。影子叹道:看我的写法,右面三道撇,一道是手,用来挽爱人的手,一道是脚,用来碰爱人的脚,一道是心,用来慰爱人的心,三管齐下,才成悠然的好风景。凌云想,是啊,她的旁边,手,脚,心,一样都没有。她的旁边,只剩阑珊的灯火,古典意境里是用来伤怀的,不能算好风景。
凌云也不理影子了,让它发着牢骚,闲躺在她身侧。
她往前看,看两桂之间,疏落着妩媚的风景。泠泠的月光调和了夜,漫漫的夜色洗净了树,抖抖的叶尖乘着风,幽幽的晚风碾碎了花,零零的花瓣搅合着影,一地生香。云动,月华颤,风和歌,叶支愣响,花簌簌着,影点子列队般地跑,仿佛配合着《胡桃夹子》里的进行曲,戏里的天真。
凌云念起刚才舞厅里唯一现场弹奏的曲,出自“猪麦兜”的手,她恰恰是唱得很熟的。
等她自我意识的时候,她在这条歌路上走得很远很远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爱情到底是可轻易转移的表演,还是老来相伴坚固难忘的承诺?
她刚才和影子讨论过孤独,爱情的命题是更复杂的,不只是她,有人比她更弄不懂。
她支起耳朵,仿佛听到细细簌簌戏里般的声音,仿若哭,仿若憋闷,仿若——只是心底随便走走的半支残词。
她细瞧,前面桂树后真藏有什么。
蜿蜒到树前面的是一条长长的影子,本来就长得极瘦,被树干子斜下里一剪,分成两半,一半突兀在凌云眼里,一半暗默在树后。那单单零零出来的半条,尽头处像是人的肩子在动。
凌云心喊要命,那只唤名伤心的动物,原来撂在了这儿。
凌云缓缓踱过去,脚步轻柔如绵。
安必新站在小喷泉边,背对这面。
凌云不打招呼,自顾走到他身旁,与他一直线,看风景不看,听晚音不听,隐心事倒隐。安必新没有出声赶她,当然,也不会照顾她。
凌云的影子倒友好,跟着凌云的脚步,蹭上了安必新的影子,似乎展着胳膊拍拍对方的肩:哥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凌云悄悄出两个手指,碰碰安必新的衬衫。
他竟倔倔扭头,侬侬着他未曾开花便已夭折的恋情。像个不大的孩子。
凌云心底叹息,他的影踩不到羽裳的裙摆,她的影却在这儿自找麻烦。
她和他前面的浅水池,关了喷泉子,承了白天的积水,随风微微地荡,池畔桂花落入塘,湿着香着,飘着静着,不惊来人,善意调情。
凌云说了一句老掉牙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安必新生硬回道,“要你管。”
凌云说,“哦。”
安必新赶她,“你走吧。”
凌云摇头,“不。”
安必新反而皱眉,“你走吧!”
凌云瞟水池子一眼,“你确定你不会跳水?”
安必新咕咕哝哝,“傻瓜。”也不知是强调他自己呢,还是骂着凌云。
凌云伸伸胳膊展展腰,突然觉得很轻松,“我陪陪你。”
安必新一捏鼻头,“我,要进去了。”
凌云说,“哦。”想到什么,将手里的阿福面具递出去,“这个借你。”
安必新怪怪看她,“你怎么想的!”
凌云说,“那么,你呢……你面对羽裳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戴面具?”连她的慕容都对她戴了面具。
安必新说,“对喜欢的人,当然要真了,好看的要给她看,难堪的也要给她看。”
还是酸不溜秋的文艺腔,有丝肉麻。凌云却当真的来听,沉入其中,咂摸良久,没能跳开。
凌云木木地将面具塞进安必新怀里。
必新拿着,看她一眼,“你是好……”走开了。
凌云回到台阶上,依然陪影子坐,厅里飘出的音乐,浓浓着,又淡淡着,很近着,又很远着。
她的肩头被轻轻敲了一记,有人要引起她的注意,急切着,又羞怯着。
凌云转头,云磊背光朝她而站,在在凝她,暗色笼笼中,能看到他微微的笑,他的手自然下垂,捏着一个猪麦兜面具。
他拿空出的手,对她伸来。
凌云站起,没有去接,慢慢蹭脚步,移到能看清他的方向。
他眼睛的味道一向优美,夜气葱茏里,更像洗净的琉璃般清澈,往里深入,缓缓地随着他的心情似展开了一卷写意山水画: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
他往前踏过一步,更朝她伸手,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凌云没有叹息,只听到心里一个浅浅素素的声音:你盼这样的一只手,很久很久了。
凌云一个凑去,被云磊接着,在他唇色笑意中,她和他对握在一起,慢慢地走。
凌云说,“没有音乐啊。”
云磊说,“里面有的。”
凌云说,“没有你刚才弹的音乐。”
云磊说,“对呀。我正和你在一起。”
凌云说,“我们是不是在作很白痴的对话?”
云磊说,“嘘。这样的景境里,白痴是可以被原谅的。”
云磊将凌云拉近一些,他的头一点一寸地俯下,衬在凌云的肩头。他一定在后面观察了她好久,他的角度找得刚好,不偏也不忸,让他舒服,让凌云也不重负。
凌云说,“我还是喜欢配着你的音乐慢慢走。”
“嗯。”
“那么,我来唱好了。”
“嗯……”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云磊放开凌云的手,自个儿手渐渐往上攀,走过凌云的臂膀,延过她的肩头,温存在颈项处。他用手指像只按住两个琴键般,捏骨恰到好处,让姑娘紧张在不知不觉里,也忘了躲避。姑娘只是睁大眼,看他溶溶软软一点笑,唇角却硬邦邦地欠着,似乎心底也牵动紧张,而且一点儿也不少于姑娘。姑娘于是倩然翩首,将男孩子的灼热轻描淡写地处理,当成一种趣味,直直地看。姑娘不晓得这是危险的,这样互相贴着,拿捏着,双方正掂量着由谁更进一步时,姑娘的天真笑颜无疑就是对男孩子的鼓励。云磊喉底咕哝一声,“傻姑娘……”到底将头重重一俯,要去找那个地方。
姑娘的手简直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揪小伙儿的胸襟。他要过来逼去她鼻里喉里胸腔里的全部气息,她也没有放过他,不知不觉施与同样的压力。云磊想,这种事情当真要不得半点不认真,别想对对方开玩笑,若闹闹着,恼了对方,也会懊了自己的。云磊看凌云紧闭的双眼,颤颤的睫毛,是别扭着畏惧着,却又是那么乖。云磊叹息,只鼻尖擦过她的,偏过了那个地方。
等好久,凌云面前只是轻而微烫的空气,或许混了几分男孩子的呼吸,睁眼,对方正沉醉芳然地笑。
云磊的手停在凌云脖颈处,扯出里面的细项链,并不带目的地看。
凌云,只听到云磊喃喃几个字。
凌云的脖子间松了,走了他的手,一刻便凉了。
他退后着,神色惚惚,极不好看地对着她。
云磊说,“这条项链,是浩云的。”
他不是在问,而是结论。
凌云是个实事求是的孩子,“嗯,刚刚,他帮我戴的。”
凌云心底念叨:不该撒谎,不很严重……
云磊扭头了,涩涩难难的一句,“你,早就有了啊。”
云磊这么离开她,回到里面。
凌云想,有了什么?有了项链?有了她的影子告诉她的能造悠然好风景的手,脚,心?
凌云对自己说:都是你们结论的,我,怎么不知道。
凌云从颈后解下项链,放在手中,链子中间有个小鸡心,端端正正刻着俩字:慕容。
慕容自以为是地给了她这么个标记,云磊自以为是地做了解读。
剩下凌云,回望自己的脚后跟,她不能随随便便,自以为是,她的影子正瞪着她,怪她蠢怪她呆怪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怪她……不,寻了半天,只是它伴着她,幽零幽零,只得罢了。
凌云从镜子般的玻璃门里看过去,镜子男孩匆匆漠漠地远去,穿过人群,没有值得流连的理由。斜旮旯里窜出另一个好看姑娘,跟在男孩后面。
李羽裳,跟着齐云磊,离去了。
(歌词引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九 女儿心
凌云不小心生了偷针眼,这几天,每当对过风一大,她的眼睛便干涩得难受,有时会流泪。这会子,她将膝盖伸进课桌下面,手儿靠在膝盖头,向上翘起个恰好的角度,掌心半藏半摊了一面小圆镜子,镜头能照见她一大一小两只眼睛,她仔细比对,看那左眼的肿是否有所消退,却,未能如愿。她轻轻叹口气,右手不自觉抬起,伸去旁边,将豁开的大窗户拉小一点儿,风却顽固得很,踢着脚子不让女孩把窗户关紧,凌云试了几次,只得作罢,任由窗隙淌进光彩云影了。
下午三点钟,剧社没有活动,空空的旧教室只静坐她一人,有的没的想一通,倒也不显寂寞。镜子再往上翘过一些角度,从镜面反射中瞧见这样一幅情景:刚进门的梅兰娇转身将半进门的李羽裳堵住了,然后,一瞬间的事,前者甩了后者一个巴掌,狠狠恨恨的。
凌云有一霎时的恍惚:这排的是哪一出新戏?
及至看到梅兰娇毫不犹豫,伸手要出第二掌时,凌云兔子一般从座位上窜起,冲了过去,抱住了兰娇的小蛮腰,更拿右手去抓兰娇高抬的手腕子。
与此同时,兰娇咬牙切齿憋出一句:“你,凭什么和云磊交往!”
兰娇没有问问自己,她凭什么对李羽裳问这样的话,她在气头上,没有意识到话语的不合理。
凌云在心底说:哦,对的,李羽裳和齐云磊被传为校对,已过半个月了。
也不是传说,凌云自己就亲眼看过几回,校园小径上,那两人不遮不讳,只是,齐云磊每每在前头快快地走,李羽裳小登皮鞋在侧旁尽量着跟,他们的恋爱倒是谈得匆匆,来时忽如,行进如风。凌云不晓得其他人的爱情是怎么谈的,她也没有经验,只是悄悄忖断,羽裳和云磊之间的方式,特别。
凌云老老远看到那一前一侧,一白一绿的两条影子时,心里也不是痛着,不是扭着,只是尴里尴尬,说不出滋味。
可想,作为前女友的梅兰娇,得知确实时,会有怎样的激烈反应了。
兰娇火爆脾气烈性子,在爱情上吃亏时,倒不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只会强硬地想要拧烂那偷葡萄的另一张嘴。
兰娇被拦在凌云手臂里,鼻头依旧唬唬嗤嗤,像被抢走了嘴边肉的小老虎,心所不甘哪!
凌云的劝说就显得有些虚弱,“梅大小姐,冤冤相报何时了。”
兰娇回头一句,“去死!”
兰娇抽出能动的手,要去补那第二巴掌,没想——“啪”!兰娇的脸上率先得了李羽裳一巴掌。兰娇是愣住了,凌云也没有反应。李羽裳,左手指揉捏着甩疼的右掌心,安安在在。
兰娇大吼一声,胳膊肘向凌云胸口一撞,撞开了后者,拼了命地要扑过去。
凌云跌倒在地,顺势拿手在面前摇了摇,“算了,算了。”
兰娇这次进攻也中途失势,跌进了对面一个宽阔的胸怀。
凌云亮目一瞪,想也没想就喊,“必新,拦住她。”只是胸口紧着般的疼,言词弱弱。
安必新傻头傻冒,镜框子掉鼻尖上,半栏眼珠在框子里,半栏兀在框子上,瞠瞠惊诧,看样子不是要着急拉住发飙的兰娇,仿佛要过来扶凌云,更关心这边似的。
凌云摸着胸口,又压压一句,“拦住她!”
安必新人高,耳朵里受了凌云的命令,手儿本能一抓,扭住了兰娇的胳膊,李羽裳却恰恰被藏在他身后。兰娇这会子的意识里,是人人都与她做对,她恨人人。她身小力蛮,却还是脱不开必新的掌握,只在他怀里挣扎,像是毫毛竖起,尖利嗓子的小小鸟,嘶叫罢了,撒气罢了,只是被男孩当成过家家的游戏,无视无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