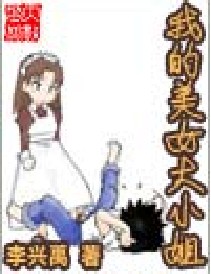女大当嫁 作者:唐清-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凌云垂脸,想磕上膝盖头的,想来想去遮不住,就用上了双手,从两边挡住自己,却,挡不住那丛声音。
人为什么要长大。
长大后一天天只认识到伤害,而失去童真的纯蜜,那为什么还要长大。
无解。
人为什么小时候会简单的笑,长大后成了复杂的“戏子”。
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拥有的只是不够,费尽心思要去得到更多。
人为什么除了自己的幸福,旁人的灵魂就不用去顾。
——铃铛,和我一起长大哎,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是来找能匹配得的“甘兰士”。
——有,缘,无,分,我喜欢这个说法。
人为什么觉得倒出假话这么容易,藏住真话那么难呢。
无解。
真有些冷呢。外套脱给康妮了,自己的肩头有些受不了了。
树声真有些怪呢。沙沙不沙沙,呼呼不呼呼,簌簌不簌簌,傻瓜蛋一样。
月光真有些丑呢。什么地方都钻,康妮的脖子也钻,钻了还把“好东西”承给她看。
宴会真不想来呢。说了不来的,出事了吧。
世界真有些不可理解呢。厚重又浮华的,冷寂又喧嚣的,温情又残酷的。
“康妮,进去穿衣服吧。”
“嗯,是要拾落一下了。这个样子出现,我那个“爸爸”,会杀了我。”
凌云看康妮悄悄掩上楼,快到二楼转角口时,康妮回身,对楼下的小妹妹举一个OK的手势,笑笑便不见了。剩凌云一个在这清静的后房,作安静的呼吸。她手搭木漆扶梯,触手滑而光润,凉而舒爽,用久了的东西就是好,摸来摸去都不会刺手。她慢慢俯头,磕上扶手,下巴来回蹭着,无意识地想着。前头隐隐闹闹的声音,对她一点也不合宜。她弯腰着累,就势在楼墙下的一张小椅子上坐,然后她听到这阵簌簌的脚步声上楼。她等,它“嗒嗒嗒”地往上走,她估摸着,然后探头看,看到她父亲的背影,掩而恹恹,行而窃窃,看不清全副的脸色表情,只看到个惘惘的侧面,嘴巴线条僵硬而不祥,内心作着危险的准备,眼儿眯缝着,一直不知道父亲眼角有这样深的窝子,窝子口是复杂的皱纹——半老了。
她的眼睛半条在扶手面上,半条隐在下,她觉得她这样偷看,不好。
父亲在找什么。
结果迎着他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双脚。
齐修缘看到她父亲,先是一愣,继而微笑,神色浮动收放自如。
她觉得自己父亲,到底不如他。
父亲是戴面具的人,选好了公共场合的面具,私下场合的面具,笑的面具,矛盾的面具。虽能运用自如,可“换来换去”总是露了形迹。
齐修缘不是,他,已经把自己的脸变成是真正的面具。
“傲然!怎么,不在大厅,跑这儿来——”
“没,没什么。”
“哦?看样子,你在找什么。”
“你若不藏起来,我犯得着找吗?”
“啧啧!你性急了,待会儿宴会上就能看到她。”
“齐修缘!这和我们当初讲好的不一样!”
“一样的,一样的,我又没有亏待她。”
“怎么没有!我说我把我的女儿给你的儿子,把我的医院给你,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我只有一个要求,要你放走她,让她出国学音乐,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弥补我应该给她却没能给得了的东西。你呢,你出尔反尔!”
宋傲然大步踏三阶,戳过齐修缘下巴处,手往上一竖,提住了对方的领口,用上十成的力气,恨不得箍死他的样子。眼神更是火而灼烈,有丛不可忍受的暴躁。
什么……父亲,他在说什么……
齐修缘拍拍紧扣着他的宋傲然的手背,“是她不愿意出去的。”
“你说得轻松!是你不让她走的!”
“我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你呆会儿可以自己问她。”
“我怎么问她?你明明晓得她并不知晓我的存在。”
宋傲然啐了一口,足足懊恼。
齐修缘咂然摇头,“那现在怎么办?你的凌云和我大儿子好上了,你的“那个女孩”必然要嫁给我小儿子。你说个转变的方法,能行的话我全依你,嗯?”
“我!”
“算了,傲然,亲上加亲不是很好吗?来,振作一点。”
齐修缘搭上宋傲然的肩,抚慰而拍。
“你这个卑鄙的东西。”
“你也不要这么说我嘛。你自己呢,还不是把亲生女儿当货物卖,你拿你的凌云作筹码,来换取我投资的资金,好让自己的医院起死回生,这事儿凌云那小傻瓜还不知道呢。要不要告诉她,她一心爱护着想的父亲,竟是这么算计亲情的,你想她知道了会怎么样?嗬嗬。”
父亲回答了吗?哦,他在说话,说些什么呢?奇怪,怎么耳蜗里嗡嗡鸣鸣的,什么也听不清呢?掏耳朵,赶紧掏耳朵,呦,好痛,是不是把耳朵都挖出血来了?没关系,能听到他怎么回答就好,能听到——他哪怕说出一个温情的字,就好。哦,是自己傻了,他都没有温情的心,怎么能说出柔款的话。他都把父女亲眷之情作了买卖,还有什么不能放在物欲的天平上。他的心里平衡着呢,她幸不幸福,他顶多关心二分,剩八分扔到漠漠长流的人生旅途上,任之自散自灭。他唯一有不爽的,是的,他有“一个女孩”,却不是她。一直以来她“自作多情”。兰娇说“连最多余的浪漫也不是属于她”,兰娇错了。这份景境应该按在凌云身上才对——青梅竹马的情谊,老父亲的口口关怀,什么嘛,骗人的,都不是对她的!
她恐恐地睁大一双眼,只看到父亲“吧拉吧拉”不停动着的嘴。
许是她挖耳朵力道过大了,血流清了,竟“吱吱唔唔”能进来一些声音了,像收听调频并不恰到好处的电台,有些杂音。
可是,她已经,不想听了。
她机械地抬起一双手,靠近耳朵,再靠近耳朵,空着一段距离,没有决绝地放上去。
“叭”,后面伸过来一只手,捂住了她的一只耳。
她泪眼模糊地回头,看到允堂痴儿般的笑。
“你在干什么。”她问。
“姐姐,你不是要捂耳朵吗?姐姐这么胆小,连这都不会。我来替你做。嘻嘻。”
那两个男人同时惊望过来,彼此撤开桎梏住彼此的手。
她父亲看到她的脸,极度不安了。
“噔噔噔”跑下来,从允堂身旁拉过女儿,捂住她的手,这么凉。
“凌云,爸爸……”
“我不是“你的女孩”。”凌云结论。
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很清楚。
这四下里,局外人的只是那个小痴儿。
怀抱花盆,又是一株还没长盛的小白花。花儿柔弱怜怜着,偏头端详人类自造的局,觉得很不可思议,花头在小主人胸口蹭了蹭,自睡它的大觉去,给了人类八个字的评价“自欺欺人,自作自受”。
齐修缘走到小儿子身旁,帮他掸了掸小西装肩头的灰,摆正那只闪亮的丝光面的黑领结,抚平西装的襟口,拉直西装的下摆,表情祥和融融得不得了,“不错。”
“嘻嘻。”
“姐姐呢?”
“姐姐就是花,花就是姐姐。姐姐保护我,姐姐做我的老婆。嘻嘻。”
“咝”,是宋傲然禁不住倒抽气的声音,看样子,他想连这小的也揍。
凌云漠极了,从父亲手中将手抽出,率先走入前面的宴会去。
原来,还是这种叫奢靡,浮华,燥热,繁丽的东西,最有用,别看它们一寸一寸的,可强悍坚硬了,一鳞一鳞,排排齐整地往人类心上累,成了不可抠剥的厚盔甲,用在任何场合,都能为主人遮盖心绪,美丽的,丑陋的,遮盖本是最真实最柔软的东西,然后将人人都打造得“坚强”。人人,都不是个人。地球上跑的,都一样。
凌云坐到吧台边,随手握住一个杯子,大口一啜,辣极了,从喉口一直烫到胃底,她眯着眼睛看手中物,红红的艳丽的颜色,以为是无害的饮料,却,还是捉弄人的鬼玩意儿。
突然想笑,真的大笑。
她爸爸踟蹰在后面,不敢靠近她。
她眼里朦朦胧胧的,只看到前面走过来的男孩身影。
她虚糜一唤,“慕容?”
他笑而不答。
她嘻嘻开了,“真是慕容。”
他朝她凑过来。
她顺势将两手揽住他的脖颈,彼此贴上很紧。
“云云。”他濡濡道,将脸微微蹭着她。
“我们有缘无分哎,嘻嘻。”
“云云,回到我身边。”他将唇微微蹭着她。
“你做的金链子,太长了。”
“嗯?”他抱着她,醉然在氛围里。
“我说,一条链子,绕了康妮,不能来绕我了。对,不,对。”她一字一顿。
她双手仍然环着他,眼儿亮而凶,逼出可怕。
他用从没有过的悚然神情回答了她,一下将她的手拉下,撤开与她的距离。
他远远着慌慌着道,“你!”
她收正身子,抬抬颊肉,肃而狠狠,“慕容,记住:女孩子是用心来爱,不是用心来骗的。”
他落荒而逃。
她撩撩头发,回身朝吧台,手下还放着那杯红糊糊的酒,再抿一口,吁,不难喝了。
允堂正和康妮同坐在大厅壁角的休闲椅上,他们上头是一盏蝴蝶外罩的壁灯,灯色宁馨,是这个喧嚣场合唯一静安的所在。椅子旁边竖着一个小高架,架头插着三脚烛灯,三星烛光,与前头大幅的烂烂明耀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是为显品位,是为摆个性,才安装了它,纯粹是个陪衬的小东西。那靠在椅子里的一姐一弟呢,是否也是大人戏剧里的陪衬角色。他们自知?他们不自知?康妮,端着一个蛋糕小碟,对允堂耐心着用心着。来,吃一口,甜糯糯的,很好吃哦,姐姐不会骗你的。康妮拿勺子去凑允堂的嘴。那家伙可不安分,摇头摇脑,优游得晃,似乎故意和中意的女孩子开着玩笑,如一般正常情爱的男生一样,心眼儿里窝着一份俏致的调皮,让女孩子麻烦着疲累着,又不能对他发狠脾气,只得叹口气,继续装点甜甜的微笑,劝着他骗着他。他眉眼弯弯,得意极了,躲得太猛,一下子撞翻了康妮手中的勺子,勺子一小跳,掉在了康妮的大腿上。康妮是打扮得宜后下来的,低胸曳地的红色长裙,华丽高贵,展平日难得一露的风情。纤细敏瘦的脖子里——少了那条细金项链,只是一落大珠子的普通挂件。那神色慧而端庄,如常。蘸满油腻蛋糕的勺子扣在她裙子上,摊了一幅如半个狗屁股的白色图画,丑陋又刺目。有小惊吓的是允堂,不再逃头逃脑,脸色僵僵,还没有学会体贴他人,这种情形下,他不知道是该为女孩擦掉,还是脱下外套掩盖女孩的尴尬。康妮鼻头微微翕动,不是叹息似叹息,神色,如常。允堂朝她呆呆地伸过手,她用一只握住他,善意抚慰,另一只手抽出手提袋里的纸巾,一点一抹地擦着。没有生气,怎么会生气,怎么能生气。拾起了勺子,擦掉了奶油,还是留下糟糕的痕迹。康妮撇嘴,抬眉,就好了,不去管它。她抬头对不知所措的允堂一笑。这痴儿更痴了,原来自己中意的女人,是怎么样也舍不得打骂自己的,嘻嘻。一秒后,他就忘记尴尬,还要和她玩。他把怀里的花盆子往旁边一放,两手对搓着,凑去康妮脸颊,指头拨弄,要在她脸上放飞“纸蜻蜓”。这是他从小和她玩惯的游戏,她一定会配合他。他不认识场合,可她认得。她已经察觉到前面左右,有客人对他们侧目而笑,哪个不懂收束的人,甚或还把鼻头的嗤嗤音肆无忌惮地发弄出来。她的脸微微一红,轻轻拍掉允堂的指头,脸儿一侧,不着痕迹地要躲开他。他以为她同他刚才躲蛋糕一样,只是对对方欲擒故纵,于是更加不依不饶。他又不懂得力道轻重,指头一翻,弹着了她的眼珠。“哎呦”!她不可避免地一叫,用手遮眼,露在手外的半张脸,作痛苦的扭曲。
“嘻嘻,妮子还玩,妮子还玩。”他要去扒拉开她的手。
他的手臂被人狠狠地揪住。
他回头一看,更笑,“又一个姐姐,属于哥哥的姐姐。”
凌云对着这张咧白牙,弯眉毛的脸,这会子只看到一丛涎皮和流氓。
她再看康妮,后者还没从痛苦中缓过来。她更咬牙切齿,脑中只充斥这位姑娘刚才卑微、委屈、辱怠的情态。
她更恨了。
她的头顶在烧,额角在烧,眉眼在烧,鼻腔在烧,喉头在烧。
她不晓得是否是那杯艳色如血的酒的作用,还是,原本她就计划好到这里来发脾气的。
她重重攥着允堂的手臂,指甲抠下,不自觉地掐到了他的肉。
他五官纠紧,一霎那的疼,还没有叫出声来,看到凌云的眼睛,那里面的颜色——
“哇”!他不是疼哭的,而是吓哭的。
他的西装裤裆里,隐隐有水色。
凌云摇头,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这个世界啊。
她也疯狂一叫,将痴儿的身子摔向一边,他自己不小心带落了椅面上的花盆。
“哐啷”——
她住声住手,慢慢后退。他缓缓而起,呆望地面。
他抬头,直眼,对上她的脸。她心中一寒,起了颤栗。
他,朝她扑过来。把她推倒在地面,手,掐上她的脖子。往死里掐,要她的命是一分两分钟的事。
她白眼朝上,看到宴会厅堂顶头的一盏大玻璃灯,粹色缤纷,琳琅耀眼,一球一球照着底下各张脸,惊叫的,捧脸的,抖舌的,傻呆的,凝望的,伫立的,挪移的,飞跑的,焦急的,愤怒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情色映在琉璃深处,仿佛都往中心光点深入进去,跳进那簇火里,都被烧着一样。这个“天堂”般的热闹地方,被烧着了。
她是被谁救起的?一定,有个人救起她。在允堂恐怖如鬼的脸旁,似乎排挤过来男人们的脸,云磊的,她爸爸的,不知名的客人的。也有女人们的妆容,齐伯母的,眼角流血的康妮的,不认得的客人的。
她从沙发上醒过来,绵延在她旁边的,只是齐修缘的脸。
她不要这一个救她。
她不认得这个房间。小而雅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