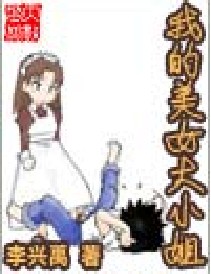女大当嫁 作者:唐清-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从沙发上醒过来,绵延在她旁边的,只是齐修缘的脸。
她不要这一个救她。
她不认得这个房间。小而雅致,分寸得当,靠壁一排极顶的深黄色橱柜,木门头,里面放了什么,不知道,或许空的,什么也没有。中央如小客厅般也是几张沙发,包括她横躺得这张,竟是印花的布面,有温情的味道。粉色流连,几分像她喜欢的草莓颜色。她出奇地静心了。脖颈里火辣辣地疼,那东西不是掐她,简直是要扒她的皮。她不敢用指尖去碰,怕受菌发炎,也怕更疼。她的手凑了凑,被齐修缘转头看到了。
他弯腰将她头旁的罩灯拧亮一些,她的手转而半遮眼,似乎闭目太久,不习惯这突如的麻亮。他笑了笑,手头捏着酒精罐,蘸了棉签,过来帮她消毒。
她推推他,张口要说话,却忒般吃力,好像声带都被掐断了。
她只能逼出难听如鸭子的声音,“我爸爸?”
“安排在楼下花厅。”
“云磊?”
“他和他母亲,陪着你父亲。”
“康妮?”
“当然陪着……”
“不要说了。那你?”
“我说我来看看你。”
“为什么是你。”
“我比较冷静。”
她阖上眼睛,突感眼皮上有光影跳动,从旁去看,是他的手指伸到灯罩里,捏死了那只正扑扑扇翅的蛾子。他杀死虫子的过程,映照在灯罩面上,活生生的一出独幕剧。
“你这么躺着,会不会无聊,要不要看……”
他递过来一个本子,陈旧斑陋,是“手抄本”的第三出,最后一幕,也是结局。
她摇摇头,“我们的戏,不排了。”
不知她是指她自写的话剧,还是其他。
他笑笑,放在茶几上,“随便你。”
廿一 《女大当嫁》(选摘)
7
齐修缘去招待所拿了我的行李,一并拿了我,带去他家。
这路上,往返之间,我的挣扎踢伤了他的腿,弄痛了他的手。他扭攥强悍,眼神凶落,不容分说,不容改变。我静默下来时,已经站在这座公房楼下了。他语音有些兴奋,捏住我下巴朝上,“瞧,我家在四楼。”这大楼外表也是漆墙斑驳,用了些年月,很不受爱惜的样子。往楼下总门洞子里望进去,一片暗黑,不知待会儿该落脚何处。他继续牵我走,我跟进去,不适应黑暗,显得傻傻慌慌的,总是左绊到一个大大硬硬的,右踢到一只小小斜斜的,似乎道子两旁乱放着纸物箱,不用的家具,小凳小桌,小几子小煤炉,另有些看不清模样的无名垃圾。这么往两旁墙角子里捂着,腾腾生生地走出了一股怪味,酸不酸,烂不烂,霉不霉,臭不臭。城里人最讲究卫生的对不对,如何此处啊。听慕容说过,齐修缘是为数几个留城工作的学生。我以为没有关系,他是办不到的。进而以为,他家条件适当,至少是个明媚健康的场所。我磕碰着随他上楼,已经怀疑了。楼道窄小,弯子又多,阶梯危险,一不留神,踏空的苦头等着你。我格外紧张着,空胃又不舒服起来。竟然到了他家大门前,就着门旁,“呕”地一下又吐开了。
那门打开,我抚胸斜眼睛看,是一位五十左右的妇人。
齐修缘喊,“妈。”
“出去那么久。礼拜天也找不到你的人,你爸找你修镜框子呢。”妇人啰啰。
然后噤声。我晓得她看到了我。
我强压住恶心,打着自己心口,往死里用力,我知道没有办法,压不住也得压。我走到妇人面前,我对自己说,柳云容,抬颊肉快笑。我不知道面对她的我,最终有没有笑。我舌苔粘着酸酸浆浆的唾沫,不能用再高的声音了,我喊了一声,“阿姨。”
“嗯,嗯。”
换了我从那扇门里走出,看到这么狼狈苍白的年轻女子跟自己打招呼,也会无所适从。
妇人灰裤灰衬衫,衫子外加一件土黄色毛背心。短发,右面卡着两只荷花牌钢丝黑发夹。头发四六分开,一绺一绺梳得整齐,有些微湿,蘸过水整理的痕迹。装扮朴素,表情朴素,是慈祥居家的母亲,不是精明落落的女人。
这种场合,我害怕见到晶亮眼神,寻根究底的家长。
我努力朝她再一笑,这次开朗两分,真心八分。
“哦,哦,”她说,“修缘,这位女同志……”
齐修缘提着行李包率先从他母亲旁挤过去,回头朝我示意,我不敢走进去。
他过来用力拉我,我定着步子,停在原处,一昧瞟那妇人。对方讶然张嘴,神色惑然。
“修缘,她……”
“妈,容我们进去再说。”
他要说什么?他准备说什么?他怎么介绍我?他介绍我后我怎么自处?
大门进去是一条一米长的堂子,堂子连着半大不小的客厅。客厅的左面是一间长窄厨房,客厅右面有两大一小三个房间,两大是睡觉的,一小是搞卫生的。客厅尽头靠着墙壁处放了一张八仙桌,用来吃饭,也用来干别的事。桌头一个小圆罩子,内里模糊糊的,是两三只菜碗,早饭用来配粥的吧,隐隐晾出酱黄瓜,酱豇豆的气味。我舔舔嘴唇。桌旁站着一个中年式落的男人,服色旧陋,洗得干净,不像那个妈妈那么畏凉,只是一件白衬衫,往臂弯子里挽卷袖口。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已经铺开了宣纸,压好镇垫,端毛笔在一角砚台里缓缓掭着。他收回手,落一点墨渍在纸上方,没有写下去,惊讶地回头看着同进来的我们。那个妈妈,稳当心情,最后一个进来,关门,接过齐修缘手里的我的包,往门角落里放,没有多余的问,侧身过去,进了厨房,听闻开锅“听嘡”的声音,那炉灶上正煮着什么,她进去后又用勺搅着什么。慢慢地,透过来一阵浓郁的香甜味。枣子?糖冬瓜?莲藕?我舔舔嘴唇。
那个爸爸看看儿子,看看儿子身后的我。
“修缘,这位是——”
“妈!端一碗红枣汤出来!云容饿了。”
中年男人,神色便不好看了。
“修缘。”
“爸,呆会儿再说。”
他牵住我的手,向大桌子走去,从桌底拉出一张椅子,将手按住了我。我没心没肝,没魂没灵了,蔫蔫歪歪地只是由他。他顾不得他父母,这点面子我却要,我是“来路不明”吧,却该死地还硬端住三分酸酸的自尊。我坐着朝中年男子喊,“伯伯。”那父亲没理我,连头都没抬一下,神色不是凶狠的,如夕阳般匀匀而默默,是个讲道理的家长。齐修缘的一父一母,都让我看了很有好感,可惜呢——不是在“正常”状态下见他们。这才咂摸到那份虚拟的氛围,懊恼中带着羡慕。那父亲拾落他的书写工具,腾开了桌面。这时候那母亲端着盘子出来,放下一小碗红枣汤。深色甜腻,香气扑鼻。这两位家长,绝对不是顾及我,喜欢我,只是出于修养的良好,与习惯的礼貌。可是,我半湿着心,愿意假想着体会这种“关怀”。我从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呆呆地说,“不用了,阿姨……”眼神却直杀到碗底深处,手也不自觉地捧上碗边沿。齐修缘带笑着温柔着说,“吃吧。”我看到两位家长听了儿子的口气,双双撩眼儿看他,浮现浅淡的不可思议的神色,那母亲甚至嘴角儿嵌一点不自觉的微笑。我心口一松,端起碗也不用勺子,咕嘟咕嘟就喝了,枣泥细腻,入嘴即化,这是我吃过的城里的第一顿东西。曾经想象过无数次在城里的第一次,第一次住城里房子会怎么样,第一次走城里公园会怎么样,第一次谈城里恋爱会怎么样,第一次生城里小孩会怎么样。无数个第一次,都是我要向天堂里的妈妈和外婆“炫耀”的资本。如今,我真的走进城里公房,坐上城里桌旁,喊城里人伯伯阿姨,吃城里煮的一碗极香极香的红枣汤——为什么,这么悲哀呢……有一寸枣子皮卡在我的齿缝里,光光只是皮儿的它,细嚼起来这般苦涩,不要去剔除它了,让它留着提醒我——红枣汤的温馨和甜美,只是这么一瞬的事。就像每每做梦,梦有两摊,一摊是美梦,一摊是恶梦,有没有发现美梦在第二天醒来时总是忘却的,噩梦却能记得很牢,很深。
我端着空碗起身,“我去洗了吧。”
“你放下吧。”那母亲说。
“你坐下来。”那父亲说。
任何长辈对任何后辈,都有行使命令的权利。我虽不羁古怪,也听话。
那父母,口气极漠。
“修缘,该说说了。”那母亲说。
“这位女同志——”那父亲问。
“爸,妈,我要和她结婚。”齐修缘说。
我双手对扭着指关节,嘎嘎作响。
齐修缘推了我一把,牵我去右边其中一个房间,门开,塞我进去,门关,剩我一人。
我无暇去注意这是谁的房间,怎样的布置。我就朝着那扇紧闭的门,呼吸空廖,心堂挖开,就听到里面悬着的那颗东西,发出吊死鬼般“吱”——“吱”——“吱”的声音!
“她叫柳云容。是石滩县搪瓷厂的女工。和我的同学宋傲然,慕容谨一个单位。六月份,我受傲然母亲嘱托下乡去找他,在那里碰到云容。我爱她。爸,妈,我要和她结婚。”
齐修缘说。
他是这重脾气,连请求这种事情都是毫无温情,肃色穆穆。
“修缘!”那父亲骂。
“修缘。”那母亲求。
“她怀了我的孩子。”齐修缘说。
那只吊死鬼已经从我的心里慢慢忖忖爬到我的脑子里了,盘踞在我的额头,先时蜷缩,后来不安分,一下一下踢着我的脑门,越加激烈,仿佛要从那里踹个洞,跳出来,然后是那魔鬼般不变的嚎叫,“吱”——“吱”——“吱”!
有摔掉塑料罩子和瓷盘子的声音,有老父亲掴儿子的巴掌声。
“不要脸!”
我觉得那巴掌是在掴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糊涂的东西!”
若我妈妈和外婆在世,会否这样骂我。
有不由自主掉汤碗的声音,有老母亲恳求儿子的声音。
“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在门口动嘴型:没有办法。
我是个残忍,畸形的东西。
我的梦折在了十八岁的地窖里,二十五岁后,有“神”从天上飞下来,那般温暖那般款款,抚着我的脸庞对我说:我来拯救你。我相信了,追着“神”开始跑。“神”却随性地甩开我,把我一个人仍在荒原上,那地方从来唱不出诗,只有纷纷的野草和冷漠的落照,连西下的太阳都吐着如血的红舌,要去靠近它,寻求它的抚慰,它只会吃了你。天上抛下来一个答案,给我的,用麻袋装着,发出腐朽的味道,里面只一句话:你不够资格!我有比天高的心,却是一副残翅,所以我不够资格。我是石滩镇那漂浮垃圾的水汪子里,惨惨游游的一只水老鼠,对光明华丽的城市来说,没有资格!我不安现状,求着不属于我的东西,对挑剔文明的城里人来说,没有资格!好吧,我骨子里天生有一重凶恶。既然现在有人“甘愿献身”,不管为着什么理由,拯救?善心?假意的爱?征服?不管怎样也好,我知道——他,不是天使。我把我的“报复”,倾倒在不是天使的人身上,应该的,是吧。
“修缘,求求你,不要折磨妈妈……”
求求你,不要哭了,不要喊了,不要折磨我。
我对着门,摇头,拼命而用力,把这颗愚蠢残忍自私无助的脑袋摇下来也好。
我缓缓抬手,到两耳旁边,隔开一定距离,没有放下去。
那空隙之间,装进了门外的喧闹,一个家庭的绝望。
太沉重了,我无法把它们压进去。
门,呼拉一开,齐修缘停在我面前。
我模糊着眼,看到他身后地板上的瓷碗碎屑,坐地发呆的老母亲,疲软靠桌的老父亲。
然后,看他。
雾里看花,他的眼睛同我一样,是走红了的,淋漓着的。
我说,“对不起,本不干你的事。”
他向前一步,狠命箍住我,我喘不过气来。
耳旁依稀着那父母的喃喃,“不相信,不相信……”
是啊,我也不相信。他说——“爱”。
他的呼吸里混着咽声。这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窗台上不知何时撂下一片落叶,筛掉夏天的肥腻,只是枯黄和扁瘦。残叶上踏来一只雀鸟,叫不出名堂,只看毛色稀黄,身姿憔憔,有些营养不良。小鸟儿装着三叉子的脚丫,在叶垫上自畅地走,仿佛并不畏惧外面世界的逐日寒凉,不怕那飒飒而走的劲风,不怕那疏疏冷冷的空气,不怕掉光了叶子枝杈朝天的枯树,不怕没有花没有绿色的天地,它已经深知年月流转,四季更换的道理,它许若已经历过一春一冬的代替过程,它比人理智,坚强,从而更容色定心,玩转自由。那么,关在房间里,不出大门,只日日扭头对窗,望夕阳叹息的我,连这种小生物都不如,对未来没有畅想,只是虚弱,无用。
小鸟儿眼神不好,本是膀子背在身后,潇洒往返,突然一下子撞到了窗棱上,“吱喳”一唤,懊恼地疼。我看它可爱而可怜,从床头伸手过去,用食指和中指推着紧闭的窗户,力气不够,只能开出一条缝,让小鸟儿塞进一个脑袋,骨碌着两只晶晶亮的小豆眼,只是好奇地看我的肚子。
——这个姑娘的肚子和别的姑娘不一样,有些鼓出来哎。
——这个姑娘的脸色恁得苍白,比我还吃不饱似的。
——这个姑娘不开心啊,靠着浅薄的枕头,歪斜在床壁,倒不像在意她肚子里的东西,而是其他。
它,一定一定是对我转着这些念头。
我试图对它一笑,它“呀”地惊呼,扑楞开翅膀飞掉了。
我端起床头柜上的镜子自看,原来,如鬼。
这一天,又这么过去了。早饭,中饭,是那个伟大隐忍的母亲送进来的,他们外面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有时还能加两个鸡蛋,一些肉,待我不薄。
修缘要上班的,剩我一人在他的房间,从日头起到日儿落,一昧地躺坐。
这刻,窗台上寸寸铺开落霞余晖,那光条儿排列紧密,彼此并不让着距离。光线是斜拉下来的,因此窗台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