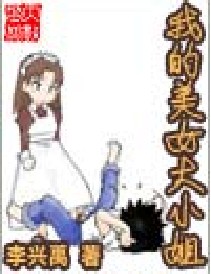女大当嫁 作者:唐清-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云磊到底看到了凌云,凌云不怪自己受着这样的委屈。
凌云蹭到那对男孩身边,想坐,又不敢过分。
云磊低头看了一下怀中这张俊美的脸,像说给她听,也许只是回忆一个自己的故事。
“我的弟弟,允堂,出生时,好好的,出生时,让疼着他宠着他的人以为,他将长成一个最优秀的少年。三岁时,得病,来势汹汹,发高烧半个月,病去,便成了这副样子。”
云磊舔了舔嘴唇,出语艰难,“你,可千万别怪着他。”
凌云叹气,“应该被责怪的人,只怕是我,是我摔碎了他的……”
云磊撅起嘴,“嘘,别说了,他睡着了,醒后什么都会忘记,也不会记得刚才对你的恨……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反过来也如是。让人疼让人宠,只是他三岁前的梦,假如,他有梦的话。他寂寞十八年,身边无人,除了我这个不算称职的哥哥。有时同他静静地走,侧眼看,能从他张大好奇的眼睛里看到七彩的光。我就会想,他对这个世界,许若比我们这些正常感受着的人还更有信心。所以,即使旁人全弃了他,我的家族,我的亲戚,我的父母……我也不该弃了他,对不对?”他抬眼看了凌云,茫而蒙蒙,也不是真要听凌云的答案,他忽而又低头,只对怀中的这个作承诺,柔色纷纷,文雅彬彬,“我不会弃了你。”
他自己,好像也只是个刚刚长成的孩子。他自己在她家偷露时,也悄悄泻出这么一丛哀默无声的神色。原来,一切不是秘密,有理由的。哦,一切都是秘密,让人撕开了,想要欲盖弥彰,只怕不能。于是,赤裸裸地面对,一次又一次将伤口掂起,坚强给人看,在在表明自己的轻松与不在乎。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黄昏用轻轻的画笔,点缀周围的宁静。树影氤氲,仿佛染着宝石的绿色调,又因浸着暮气,更抹上一份深红。有浅浅的月钩轮廓,钻出了树丛,茂密的树叶使寂寞更浓。一个蜘蛛用它的丝线,迷人地编织着苍穹,穹隆中有鸟儿扇翅归巢,宛如唐代的屏风。①
凌云靠了半棵树,云磊抱着弟弟也靠了半棵树。
凌云手儿自然垂下,摸着了泥土和碎叶,实诚。
云磊抬头,半闭目,睫毛颤颤,受着风的影响,像小湾子里的水,有潺潺清清的味道。
“要是——给我一棵树就好了。”
“嗯?”凌云回神,看身边的他。
“我说,我只要一棵树就好了。”
“哦。”
“在树上造一间不大的房子,够住我和父母……不,够住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他。脚低着脚,伸不直也没有关系,手碰着手,不小心打到彼此也没有关系,衣服简陋,粗茶淡饭也没有关系,清贫没有享乐的手段也没有关系。在这个小小空间里,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就好,能把一天下来的心里话瓣开来真实地讲讲就好,能体顾全家,不冷漠算计就好,能像——真正的一家人就好。”
“哦……唉……”
“是不是和你的阳台很像?”
“什么……”
“你要一个阳台,我只要一个树屋——能和我们的父母体验全份的爱,就好。”
“什么!”
凌云惊而坐直,去搜寻他的眼睛,他还在朝上看,他还半闭着,他有淡淡息,眼角沾着似乎是画里滴下的水渍。
他那天,把她全然听去了啊。
原来,他的心底和她有一样的浅浅愿望,那被慕容称之为可能会成为这个圈子笑柄的小小愿望。
人们都把她和他这样的,称作不切实际的孩子。
他们自我满足,就好。
至少,幸福会在心里,慢慢开花。
凌云说,“你那么喜欢玻璃,放到树屋里,不容易保护,易碎的。”
云磊转头来盯她,从所未有的牢牢,“就是因为玻璃易碎才喜欢,这样我悲伤时才不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软弱的,至少我的后面还有更加易碎的东西……”
人们去剧院欣赏悲剧,是为了消遣现实世界的实际痛苦感,看到剧中人物更加波折的命运,人们对自我的生活才会有种满足。没有人,是真正坚强的。那些口口声声喊着自己从没受伤过的人,不要去相信他们,你看好了,他们也只是用更加弱小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无泪和伟大,其实他们掉泪在心里。人所虚伪。
云磊将允堂扶住,自己也站起,“我要先送他回房。”
看了凌云一眼,短而深,加了一句,“你等我。”
凌云有没有点头,她自己也不知道。
云磊走后,她咂摸两人刚刚的对话,酝酿一会儿真要见着他,该说些什么。好像,不说比说什么,都好。
凌云一瞥眼,看到前方树丛子里,闪过一个蓝色的影子。
黑长发,蓝丝带,蓝衫子……
凌云追了过去,没有,等云磊。
(①诗句引自阿根廷诗人卢贡内斯《闲趣》。)
七 下坡路
凌云追进大屋里,在一个楼梯堂子口停住。
她往身后看,那里墙壁上挂着一面竖落的白镜子,凌云暗喊糟糕。
她忘记午后筛雨暮时停的事实,在碎叶子上坐那么一会儿,屁股处便浸着两团淡淡的湿渍,有些像六月初熟的桃儿面,不够红,绽青绽青的,不是可爱的象征。低头一看鞋子,更显“辉煌”,底下抹泥面染香,是被碾碎的香樟子的清味,不会让仆人们产生浪漫情调的,单单那撂在后面的一串黑泥印子,就会让他们大喊罪过。
凌云想办法弥补,眼神儿一溜,瞟到镜子旁边,楼梯下面的一钩架子,其中一个搭着一块抹布。凌云将手去扯,小指弯着,便擦到旁边隙开的门延——楼梯下藏着一个小房间,未锁。侧耳听,内里传出“细细簌簌”的响动声。
凌云噘嘴,出指点着那条黑洞洞的缝隙儿,喃喃道:再看,再看我就进去了!我真要进去了!
凌云抬脚,伸平脚丫板子,用鞋尖稍碰碰门角,门缝儿更大了些,也没闻人出声责怪。
凌云将身子融了进去,鼻头一冲,和自家父亲的书房有同样的味道。
借着身后微亮的光,凌云四顾,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杂物间,旧货堆堆,参差而置,地板布灰,有些让人下不了脚。凌云的脚印下,先有一串印子,男人的皮鞋样,正正方方。前头一个着地而放的大箱子,上面歪坐一人,凌云以为他在找东西,却没想,更看一看,他是在看东西。他嘴里唔唔囔囔的,刚才的细微呼哧声就是出自他。
凌云慢慢走过去,他慢慢看凌云。
他身子颤了颤,想站又站不起,酒是五毒,确然。
凌云在于他是背着光,他一定看不清凌云的声色表情,但他显然愣住了。
他晃晃悠悠地伸手,那掌尖子摊开,也在抖。
他冲着凌云喊,“云容,云,云容……”
凌云说,“我是宋凌云。”
她察觉了不对劲,可她是个迟钝的主顾,她忘了住脚,她一直走,离男人很近的地方。
男人突然冲起,两手同时扳住凌云的两肩,凌云至少还会叫一声,然后被他紧在了胸前。男人高大极了,凌云的头正挨着他的脖颈。所以,男人对凌云的,不叫拥抱,而是往死里摁住。她有些喘不过气。她唔唔发出虚弱的声音。她不忘喉里逼出一句,“我,是,宋凌云……”她起码有点小聪明,男人怔怔,让暖暖的体温在凌云面上再徘徊一小阵,然后,呆呆推开了她。男人将她微转,凌云晓得他是趁外头光要仔细看清她。终于,他懊恼一喊,再重重推她一把,让她趔趄,却得到轻松。男人抓自己头发,“不是云容,不是……”
凌云咳咳嗓子,叫道,“齐伯伯。”
齐修缘低着头,对她惶惶然,“你……”
凌云好性子,“我是宋凌云。”
“哦,宋傲然的妮子,”他退坐到箱子盖上,沉顿良久,凌云等他。他看似回过五分神,重新审视凌云这个不请自入的“身外物”,“你,怎么来了。”
“来接我母亲。”
“哦。要回去吧?”
“没能成功接回她。只能自己回去。”
“哦。”
“齐伯伯这里……有我爸爸书房里的味道。”凌云一出口就后悔。
齐修缘默默漠漠着,突然一抬头,凌云看到,他眼睛深处有光,像烧到接近指根处的香烟坯子上最后一星红光,意撩深深。
凌云脚下一动,踩着样东西,弯腰捡起,是张小纸片。
不,是张小照片。
齐修缘刚刚看着的,激动中无意抛落的,捏在凌云的手里了,他也没来抢。
凌云得不到他的示意,可当真管不住自己的手。她稍稍转个角度,一漫光线拂在照片上。凌云竟有一忽儿的恍惚,仿佛是爸爸那张照片里的姑娘,被原封不动地剪了个轮廓,小心谨致地被贴来这一丛风景里,连那笑也是复印过来的,渺淡飘忽,抓不住一处心角。这里作背景的,是三个男生。二十出头,郎当岁月,正是勃勃奔走,消费青春的好时光。三个男生,在姑娘后面各占一个位置,不过分贴近她,也不彼此谦让,有暗暗较劲的味道。与他二人暗思量的其中一个,是凌云爸爸宋傲然。一个,是云磊爸爸。剩最后一个,也是熟的,浩云爸爸慕容谨。
凌云突然耸鼻一嗅,也闻到同父亲书房里的呲呲不祥的味道了。
一种藏了二十来年,被湿旧的棉絮捂透了,从而腐烂发霉的味道。
凌云将照片甩进忽然笑笑开的齐修缘怀里,转身便走。
她又被抓住了,心头咚咚跳,极致恐怖。
齐修缘与她换了个角度,他成了她的背光里,她惊恐的双眼被他看个透,他的方寸神色她一无所知,只听那喉底还是一拨一拨缓缓腾起的笑,“你说你叫宋凌云?好,好。”
她不好。她害怕极了。她鼻里一哧,像被踩着尾巴的猫一样,汗毛微竖。她再次一用力,跑,不,逃了出去。
她后面没有人跟,那小杂间的门还是那么半开办闭,隐住着秘密,也公开着秘密。
有人从旁串出,精准地握到凌云的手臂,凌云“啊”叫一声。
对方有急,“怎么!”
凌云看到云磊,这样房子里应该最不让她适意的人,她现在看到了反而最欣慰。
“怎么了?”云磊秀挺微拧的眉毛,一头蹙着对她的焦急,一头蹙着对她的不满。
“没有,”她抚了抚心口,“喜欢看到你。”
她没有说什么严重的话,云磊却突然……竟然脸颊有红了。
“不是要你等我吗。”
“我,追东西去了。”
“什么?”
“还是不追的好。”
云磊撇嘴,怪然地看她,“看来,你对我们家的兴趣,不小。”
“这里不正常。”凌云恍恍地结论。
云磊没有生气,默而泯然。
“这里……唉,你妈妈,好像我爸爸,你爸爸,好像我妈妈。”
凌云说的是怪胎的话,云磊却真像听懂了。
他突然一把执起凌云的手掌,将它捏作一个拳头,用了很大的力道,紧紧炙炙,姑娘只有随他的份儿。他将来那个小拳头,令人咂舌地用来敲自己的心脏,咚,咚,咚,他一定是疼的,因为凌云自个儿的指关节也受不了。他在做动作时,眼不闪避,就是直辣辣看进凌云眼底深处。凌云因为刚才在黑房间里着了些惊,眼珠儿四方都蒙着水气,云磊的目光温度进去了,一下子就把那地方熨干了。
云磊将凌云的手慢慢放下,仍握住在大腿边,说了一句,“我送你回去。”
云磊将车开得很稳,凌云的下坡路却走得并不轻松。
凌云悄悄拉下车窗,晚来风急,撩着她清爽的短发,乱了,被肆无忌惮了。
凌云看车道前头,“咿”了一声,对云磊说,“把车开到那个人旁边,好吗。”
清月夜下,山朦胧里,烟气绕成画,画里动一个模糊的影,影里揉着纤瘦曼曼的身体,移步的模样,像是花园拾香而归,轻巧踏上闺阁楼梯的姑娘,让人想象着,她会去磕在阳台边上,继续后半夜的幽梦故事。
汽车在她身边刹住,似乎将她吓了一跳。
凌云的脑袋从车窗探出,俏致地唤,“羽裳。”
李羽裳对凌云很意外,“你还没回家?”
她意外的是这个?她怎么不意外凌云坐着云磊的车?
凌云开门而出,拉着羽裳,“一起走吧。”
李羽裳绕开凌云诚诚天真的目光,看来车里的齐云磊,后者的表情藏在车内深处,她怎么看得到。
李羽裳轻摇头,“还是,不用了吧。”
凌云拉她,“走走走。”
凌云不好意思再坐在云磊的旁边,总不能让羽裳撂在后头,而且,她俩说话也不方便。
云磊开车依然很稳。
女孩子的话音世界,云磊插不上嘴,他似乎也有尴尬,尔后的时辰,他便一直静默。
凌云有些兴奋,在皮椅上的身子也是歪向羽裳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凌云问。
“哦,我在这里做家教。”
凌云点点头,突然疑道,“这个坡上好像只有云磊……好像只有他们一家。”
凌云对自己将他的名字如此亲昵地冲口而出,有些羞赧,羽裳却似乎没在意到,也有心事。少了一副瑶筝,要不然,凌云和羽裳可以对弹弹。
“坡那边还有一家,我教累了,有些闷,想过坡走走。”
凌云说,“哦。”其实她没哦到什么。
“你教几年级?”
“高二,那孩子文科不行。”
“你不是念经管的吗?”
“文科是我的兴趣,我教的不错。”
“你喜欢诗词吗?”
“咦?”
“哦,没什么,因为我自己喜欢,想问问你。”
“呵呵,喜欢。你看,人类世界的最高追求,往往是最不具实用性的东西:文学,音乐,哲学……富人家的小孩,比穷人家在这些方面更有资格。那些名牌大学里,念法律,念经济,念商科的,不要去听他们标榜自己的家庭,因为他们往往不是真富。”
“哦。”凌云碜碜笑笑,对羽裳的结论说不出赞同。
羽裳凝视凌云,将话题重新引回诗词,“我喜欢——《长恨歌》。”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