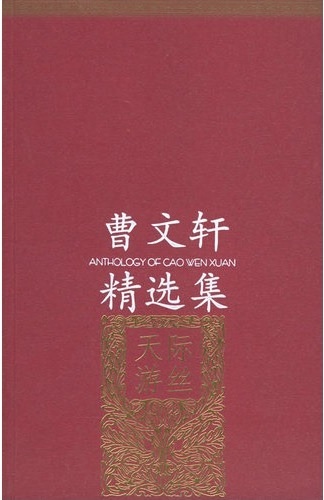尼采选集-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道德之士〃的伪装,在道德法则及礼仪规范的表面,以及我们在责任、德行、公众情绪、荣誉和毫无私利之掩蔽下的行为,难道也不该有支持它的最好理由吗?我并非意味人性的弱点与卑怯,简言之,即是我们心中那邪恶狂野的兽性,应该加以掩饰;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身为驯服的动物,甚为屈辱可耻而需要道德的掩饰——欧洲人的〃内在人格〃很久没有足够的劣根性可以〃让自己公然被见〃
(因而成为美丽)。
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型、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虑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粉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以更加显著而可辨明、更加重要、〃神圣〃的伪装——
三五三、宗教的起源
从一方面来说,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是建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与这种生活模式一种解释,并以其最高之道德观念来启发人们;因此,它成为人们为之挣扎,在某些情况下甚而置其生命于不顾的至善之物。
事实上,后者的发明比前者重要:第一、此生活模式往往已经与其他的生活模式杂然并存,然而却不明白其具体化的价值。一个宗教创始者的创意与输入,通常都以他见到并择取那生活模式,并为将可被利用的事实首度予以神圣化,以及能如何将它作一个圆满的诠释而揭露出来。譬如,耶稣(或保罗)发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之一般人的生活,是一种谦虚、贞节与消沉的生活;他乃诠释这种生活,并给与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有勇气鄙视其他各种生活模式,摩拉维亚教徒①的宁静之狂热、神秘而隐藏的自信日益增加,最后终于准备好了要去〃征服世界〃(意指罗马及整个帝国的上层阶级)。
①摩拉维亚教(Moravian)新教教派之一的教徒,散布于捷克的Moravia地区。
佛陀也同样地发现到人类的同一类型,他发现到那些善良慈蔼的人,事实上是散布在每一阶级(指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阶级——译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无害的——由于怠惰、以及怠惰之人,而使他们过着节制的生活,几乎毫无所需,也毫无所求。他明白这一类型的人,由于其惰性,而不可避免地将会逐渐接受一种可允许其免于再入轮回受世俗之苦(亦即生、老、病、死等一般生命的过程)的信仰——这种〃洞悉〃便是他的天赋聪明。
宗教的创始者能够确实掌握住一般民众的心理,并且深深了解一种特定而平均类型的灵魂,而后者却始终未能憬悟到他们乃是同一类的人,是宗教创始者使得他们聚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创立永远是一种长期认知的仪式。
三五四、〃人类的天赋〃
当我们开始感知我们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免除意识时,才会有意识——或更正确地说,便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感知之始,我们才以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讨论它(因此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赶上莱布尼兹事先提出的暗示)。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感觉、希望和追忆,并且在各种类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样的〃表现〃,然而这种种却都不需要有〃意识〃。
整个人生就好象在镜中一样,无法看到它自己;事实上,人生中的绝大部分用不着对照镜子也一样能延续下去——即使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虽然这种论调在年纪较大的哲学家听起来会颇觉痛心。如果意识是不必要的,那么它的目的为何?如果你听我的回答,这项假设或许也毫无理由;但在我看来,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比较不易被了解,如同个人自身主宰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整个种族以及世代之承袭有关,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长久以来一直驱使着人们与其伙伴沟通,并迅速而敏锐地明了彼此,最后终于得到一种剩余的权力和沟通的技巧。仿佛幸好他早已有所积聚,而现在就等待着一个继承者毫无吝惜地将其挥霍(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些继承者,同样的,雄辩家和传道者、作家等亦然;这些人来自一长串继承的末端,总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他们的本性原本就是个浪费者(spuanderers)。
假如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便可以进一步地推测,意识大体上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自始它就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在上下主从的关系之间)才是必要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适当地说,意识仅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的纲,也只有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至今,隐士以及如野兽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情绪等,都是在意识的范围之内(至少是一部分),结果便造成一种可怕而持续的〃必须〃主宰人类的命运——身为最有危险的动物,他需要帮助和保护,他需要友伴,他必须能表白他的苦恼,他必须知道如何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些种种,他首先便需要〃意识〃,他必须〃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人就象各种生物一样,虽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压力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那足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并不适合属于一个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象会被意识的特性所压抑——藉着其中专制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体的透视。
基本上说来,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而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就我所知,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特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
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我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判定这种区别。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最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而毁灭。
三五五、我们的〃知识〃概念
我在大街上得到这项解释。我听到有个人说〃他认认我〃,所以我自问:〃人类从知识当中真正了解了什么?当他们追求〃知识〃时,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们这些哲学家藉着知识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所谓已知,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一般的状况,不再对之感到惊异,任何我们所习惯的规则、所有我们置身其中时会感觉安适之事物——是什么呢?我们求知的需要不就是这已知的需要吗?去发觉任何奇怪、不寻常、或疑问之事物的意志,难道已经不再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了吗?难道不可能是恐惧的直觉责成我们去求知吗?难道那有所领悟的人只是因为他重获安全的感觉才使他愉快吗?
有个哲学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时,想象着〃已知〃的世界:啊,难道不是为他早已知道、熟悉这个概念吗?因为他对于〃理念〃的恐惧少得多——哦,这个领悟者的节制,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原则,以及他们对这个谜或就此而论之世界的解答!当他们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间找到什么时,或者在很不幸地为我们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们的逻辑、意志和欲望)有了任何新的发现时,就会立即感到十分地高兴!
因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对于这点他们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领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认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于了解,譬如说,从〃内在世界〃以及〃已认知的事实〃发展到外在是经过一种极有规律的次序的,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清楚的世界!错误中的错误!已知之一切是我们所习惯的,而我们所习惯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难了解的,亦即,领悟到它是一个问题,感知它是奇怪的,遥远的,且在〃我们的外部〃。
自然科学的十足确实性和心理学以及意识因素之批判(大致上,这一类的学问皆被称之为非自然科学)相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根据他们以陌生之事物作为客体的事实而定的,而这几乎就象是希望将所有不陌生的事物当作客体一样的矛盾与荒谬。
上一篇
12。txt
悲剧的诞生卷
第八部分
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
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
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
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
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