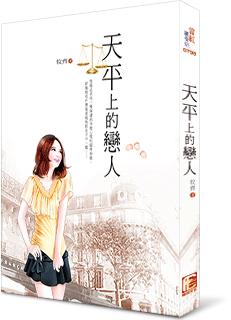被绑在树上的男孩-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东西,找那些籽的吧!我可不想先跟他们说话,我爹也不会先开口的。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人过来,他的眼睛里只剩下他的烟头了。那个比我娘还老的女人离我们很远就忙着打招呼了。我爹听见后抬了抬头,脸上挤起了两个大大的疙瘩,然后又低着头做他自己的事了,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嘛!我对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她的嘴巴太薄了,老师说嘴巴薄的人是多嘴多舌的人,特别是嘴巴薄的女人。她就是这种女人。那个小男孩的嘴巴很厚,是个不爱说话的人,眼睛老是盯着女人手里挎着的那个篮子。
第一卷 《天就要黑了》(下)
《天就要黑了》(下)
她走到我身旁,探着身子往筐子里瞟了一眼。我看到那种眼神怒气就来了。这个女人在嘲笑我们。她的篮子里也放着我早就猜到的那些东西。
“这山上的籽都让哪条狗给吃了!”老女人气冲冲地骂着。
我爹很明显不想跟这个女人说话,他的手又冲着那个口袋伸下去了。一个下午他的手都不知道掏过几遍那个口袋了,这一次和前些次没有什么区别。他不喜欢跟陌生人谈话,即便是熟悉的人,他的话也不多,我娘老叫他老哑巴,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多说的。我娘这么说我爹没有人会反对,就像她说我的脑子想得太多根本不像个刚上学的孩子一样,可是这句话也并不是全部都对的,就比如关于那个城里的女同学玲玲的事情,我就犯错了。
我爹还在抽烟呢,我都看烦了。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一个字都没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火心又旺盛地燃烧起来了。伐木的声音一直在继续,愈来愈响了。不知道是他们在*近我们,还是我听得愈来愈烦厌了。现在是完全没有风了,从那个女人来这里就停了,可是我爹手中的烟却是烧得越来越快了,通红的火心一直保持着它的鲜艳。当然这鲜艳和天空一比就显得更亮了。天就要黑了。我爹现在是完全把我娘吩咐的话甩到不知哪个地方去了。我实在无聊透顶了。男孩子走过来跟我说话,要我跟他玩游戏。我无事可做,很乐意他的想法。那个老女人根本没有顾及他,她正忙着找她的东西呢!我爹也有事情做,他袋子里的烟还没有抽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不然无聊会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的。
“一点都不剩,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老女人咒骂个不停。
“你们不再找找吗?天就要黑了。背空筐子回去啊?!”她还在说。
我爹没有搭理她。刚才脸上挤出来的两个大疙瘩也是逢场作戏一样的。我爹大概在借烟宣泄什么呢!
伐木声叮叮当当地依旧响个不停,根本没有歇下来的意思。
我爹的脚边上已经堆积了好些烟头了,最后的那个大概没有抽完就被丢掉了,正垂头丧气地飘着最后几缕烟气呢!
“回家……”我爹的嘴里突然蹦出这两个字来。他的脚狠狠地碾了一下那堆烟头。
“这就回家了?”就在我惊讶和不乐意跟那小孩分开的时候,我娘不知道怎么过来了。
我爹连看都没敢看我娘一眼,我猜他的手又要伸到口袋里去了。真的是这样。
“抽抽抽,就知道抽!抽了一地还不够呐!”我娘的脸上到处都是早晨天上浮着的红云。
老女人在旁边偷笑,我娘想找她评评理时她却故意背过身去了,仿佛不愿干涉别人家的私事似的。我的新朋友也回到她身边去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从4点就出来了,还没有打,我……我……”我娘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好了好了,为点籽值吗?!”老女人突然迎上来劝我娘了。我觉得她的脸上都是幸灾乐祸。
“好了好了,天都快黑了。回去吧!”她要送我娘回去了似的。我爹一声不吭地就走了。我娘跟那个老女人跟在后头。我和新朋友就跟在她们的后头。
“4点就出来了……现在还没打着一点,底都没垫着……”
“好了好了……”
“我们明天再一起玩吧?”
“好的。”
“你哪个村的?”
“就知道抽烟!”
“我家在这那边……”
“你们班上有没有小妖精的?城里来的小妖精。”
“我辛辛苦苦掰了一个下午的籽,想凑成一担,明天早上挑去卖……”
“什么小妖精?”
“谁不是呢!我这不也是嘛。想凑成一担。这些男人就不知道家里的苦!……”
“城里来的那些小妖精!城里人,老叫我们乡巴佬的。穿得像个番薯,走路屁股扭来扭去的。这样的妖精。”
“我们班上没有城里来的,我们班上都是乡巴佬……”
“回家跟他好好说说,明天再凑一点,后天再卖也来得及。”
“你们班真好。”
“等到后天别人都卖了,价钱就下来了。”
“他以后会改的。”
“你们班上的小妖精长得好看吗?我来看看……”
“孩子都那么大了。改不掉了!”
“她走了。”
“去哪里了?回去了吗?”
“回去了……”
“两口子拌嘴,犯得着吗?”
“那我看不到了?她为什么要回去呀?”
“谁想跟这样的哑巴吵呢,一吵起来倒像是我在欺负他一样。老是装成一张苦瓜脸。”
“我哪里知道她为什么要回去啊!”
“你问过她了吗?”
“嗯……”
“我才不跟妖精说话呢!……”
第一卷 尼采的头骨
尼采的头骨
1992年4月20号;我在《苏州日报》做实习生的第二天,就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电报。我并不想故弄玄虚,说意外是因为除了外公外婆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苏州实习;而且我再三向二老说明不要将我的去处告之他人,以免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打扰我。为了加强效果,我甚至跟他们说,如果有人来打搅我,就会影响报社领导对我的印象,就会影响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二老胆战心惊地点头了。
电报是从杭州发过来的。
“哼!两个天堂都凑成一块了。”我苦笑着。
电报上只有四个字:病危速来。倒挺会吓人的,来这一招!我开始想自己在杭州有什么亲戚。可是想不出来。不多久我就想到了一个人,他是唯一一个我在杭州认识的人,可是我跟他也足有好久没有见面了,他现在突然跟我来这一招……是不是二老告诉他我的地址的?不过,事情已是如此,我还是决定走一遭。幸亏我在杭州还有一间租房,我叫女房东一直替我保留着,她虽然很不满意,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租这样差的房子,也只好如此。于是每次见到我都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却也奈何不了我什么。
严丰是孤儿,很小父母就离异了,性情孤僻古怪;他的奶奶*捡破烂将他抚养成人。到了19岁,他在西湖边上的一所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奶奶就永远地离开他了,于是他索性一个人搬到了杭州,在城西郊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打些零时工和学校的学费减免艰难维持着生计。我也是在他搬到杭州后才认识他的,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是所谓的同病相怜。
虽然由于昨晚那个奇异的噩梦弄得我整晚都没有睡好,但我仍决定跟编辑说明一下情况,希望他能准许我抽身去趟杭州。编辑倒是没有难为我,于是我即刻赶往杭州。当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和以后的工作前景,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我稍微化了个装,也顺便戴了副大墨镜。两个小时之后,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我没有在路上耽搁,迅速就赶到他的住处。那条路我太熟悉了。
在那个住处的外面我见到了一个胖乎乎的女人,40多岁模样,左脸上有些类似青春痘留下的痕迹,她的双手在深蓝色的围裙上搓个不停,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一点作为我们这一行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我没有太多地观察她,我来这里是有其他重要的事。
“严丰是住在这里的吧?”我拿电报给她看,证明自己并非是什么不速之客。听到我的话,她的眼睛马上纯净起来,刚才那种复杂的眼神马上就被一扫而光。
“是是是……我是这里的房东。你要不要租房?”
我摆摆手,暗地里笑了笑。不过其实我早已猜出两分来了:自己的房客出事了,她自然惦记着他们能否按时付房租了,刚才她的眼神里定是那些东西。
“电报就是我拍的,他卧病在床,出不了门!”说这句话时她的眼里又多了些焦急。
“我知道了……”我不想跟她多说,“他在屋里吧?”
“在!他哪里还出得了门呐!”她话里含着的东西太多,这令我感觉不是太好,这句话的分量实在是比那份电报重许多。
我轻轻推开门,在房门沉重拖沓的吱扭声中走进去。整个房间都被一片黑暗笼罩着,而且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严丰就半倚在窗前的书桌上,我只能看清他身体的轮廓。在我不小心踩到一个水罐之后,一个病恹恹的声音就从阴暗中飘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你来了?”
“嗯,”我答应着。
“你找个地方坐会儿。”
“你这里光线太暗了,应该把窗帘打……”
“哼……我这里……”他支支吾吾,仿佛在掩饰着什么。
我摸索着想去开窗户。当然我那时也想通过拉窗帘来表明我和他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在那个时候让病人产生这样一种意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都是十分有益的。可是当我拉开窗帘的一角,借着窗外的光看到他那张痛苦的脸时,我完全震惊了。那张脸瘦削,颧骨高突,眼睛深陷,两颊几乎都没有肉,只剩一张皮包在骨头上。他的脸已经在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下痛苦得有些扭曲了,一只手慌忙地从棉被中抽出来遮在眉上。我马上又拉上窗帘。
“现在的阳光仍太强烈,我承受不住。”他慢吞吞地告诉我,口气中还存着道歉的意思。这自然令我很不自在。是我在打乱他的生活方式。我看了看表,指针模模糊糊地指着两个数字,看不太清楚。我根据自己在苏州上车时的时间和路上花的时间猜测出来,现在大概是傍晚五六点钟。严丰的病情确实让我有些害怕。如果他有什么意外,我可完全没有什么主意,他的家人都不在了,我的情况也不是很好,那该怎么办?他现在的病情已经到了不能忍受傍晚微弱的阳光的地步了。我的手心都开始冒汗了——我完全是不知所措!静默一段时间以后,我决定找个话题缓解一下气氛。
“房东刚才来过了吧?是她在照顾你吗?”
黑暗中只有一声冷笑传过来,虽然笑声很小,但我还是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很容易就捕捉到了。
“怕我死了没法交房租!昨天晚上就催我把家人的地址告诉她。我说我是孤身一人,没有亲人了。她又硬逼着我找出朋友的地址来……我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往你家打电话,”他顿了顿(此刻我已不再追究是不是父母将我的地址告知他了),“这样我就找到你了(他没有提及我父母,怕是受了他们再三的嘱咐吧?我猜测可能是这样)。她连夜就赶出去打电报了,怕我一个人死在这里给她添麻烦。”
我又回忆起房外的那双眼睛来了,现在它除了讨厌之外还令我感到有些害怕了。不过我不想让他乱想,我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点安慰,这一点安慰的破灭很有可能会令他再难以坚持下去。我的注意力转到正题上来。
“你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他一开始并没有作任何回答,连声叹气都没有。许久我才在那张书桌上看到了一只挥动着的手,仿佛在示意我不要再追问下去了。
“你先休息吧?我明天早上再来。”我见他几乎都没有说话的气力,只好提出告辞,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好这一晚该如何度过,我在杭州举目无亲。他没有说话。我拉开门出去了。房东站在门外,好像自从我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她就一直守在外面。
“你要走了吗?你可不能走啊!”她要阻拦我离开。
我自然十分清楚她的心思,为了她不要再来纠缠我,我清楚向她说明我明天早上还会来的。她不相信,我可不想跟她多说无谓的话,抽身就走,她还想拦住我,我急忙躲开了。她还在身后叽叽喳喳。
晚上我在离严丰住处不远的一家破烂旅馆里住下来。虽然严丰的事情令我很头疼,但疲劳和愁烦使我很早就进入了睡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他的住处。房东见到我的到来很高兴,满脸的喜悦难以表达。她朝我笑了笑,我知道她现在跟我笑得这么灿烂,但只要严丰有什么不测,她就会搬出她的另一副尖刻的脸皮来,那时,这张脸可不认任何人了。我勉强挤个笑容,便匆匆地进到严丰的房间去。
严丰的精神状况比昨天好了许多。我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轮廓坐在床沿,不像昨天那样倚*在书桌上了。
“来啦。”他的语气平静缓和,却是比昨天有力了很多,我想今天不用再老是竖着耳朵听他讲话了。
“你看起来比昨天好了很多!”
然而他并不怎样高兴,对我的话甚至都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人在病中性情是会改变的。我这样说服了自己。他挪动了一下位置,*在离我较近的床沿,没有等我开口,他却跟我讲起了一个奇异的故事。他说这是他做的一个梦,并再三向我说明自从做了这个梦之后自己的病就日渐严重,直到病成如今这副样子。医生根本无法下手医治,这样的病不仅仅只是身体上的,光*药物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医治的。
“4月1号那天晚上,当我在整理箱子里的书籍时,发现了一张几年前的报纸,是文化版的,这一版主要是介绍挪威的一位画家,爱德华·蒙克,上面除了介绍他的生平经历和绘画成就之外,还刊登了他的两幅著名画作,一幅是《呐喊》,另一幅是《尼采画像》。当我见到《尼采画像》时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厌恶那粗犷的胡子,厌恶那故作镇静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