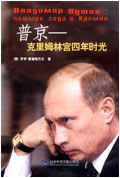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金马可”是由两条平行的宽带组成一块矩形金质薄片,在宽带上绘有微型神像。采用分格注釉法把这些神像描绘在金质底版上。神像四周有用宝石和模压颈饰装点起来的花边。每一尊神像都用喷泉或者壁柱加以点缀。在上宽带的中央——是一块绘有米哈依尔大公的颈饰。总共近八十三尊微型神象,(在圣马可大教堂挂在主宝座后面的那幅圣障上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九块宝石和一千一百九十八颗珍珠,而在“金马可”上就少多了。
4.“格尔莫格诺夫(喀山的)披肩”
(在清单编号第三十二号的后面写着一行注:“不得出售,只能保存。”)
被称为“格尔莫格诺夫(喀山的)披肩”或叫“莫诺马赫披肩”或“阿历克赛·科穆宁披肩”,它的存在至今仍引起许多俄国学者的怀疑和争论。但是某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其中包括我,认为这并非虚构,确实有其物,并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格尔莫格诺夫披肩”早在一八二三年就被发现,是在一个私人手里。
据说,阿历克赛一世科穆宁皇帝从帝城给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送来了皇冠、金链和披肩。皇冠和金链保存住了,而披肩却失踪了。根据传说是,在靼鞑蒙古统治时期它已做为战利品落入一个蒙古军事长宫的手里,而后转来转去,落到了喀山王国奠基人手里。当喀山王国被俄国军队攻陷亡国时,最后一个喀山国王叶季格尔成了俘虏,披肩又失踪了。好象到了一五七九年它才被找到,是在一处被焚的房屋旧址的地下找到的,同时还找到了喀山圣母神像。众所周知,这尊神像后来被放置在波扎尔斯基公爵的营垒里,是她把莫斯科从波兰人手中解放出来。至于披肩,留在了喀山总主教,后来成为全俄的牧首,格尔莫根的手里。他宣称,把波兰人赶走后交还给合法的俄国沙皇。然而,格尔莫根没能活到米哈依尔·罗曼诺夫登上王位。当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组织民军的消息传到波兰人占领的莫斯科城时,波兰人要求牧首出面劝阻波扎尔斯基公爵和说服市民们忠于波兰王太子符拉季斯拉夫。但格尔莫根拒绝了,结果被铁链锁起来,活活饿死了。传说,牧首临死前把莫诺马赫披肩交给了见习修道士丘多夫。丘多夫是梁赞省人,他把披肩隐藏在自己家乡的一个地方。一八二二年前,人们一般都相信这个传说。到了一八二二年,当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奥列宁在离古老的梁赞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金披肩的时候,大多数学者改变了看法。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奥列宁终于成功地找回了举世闻名的俄国之宝。然而,很快就查清,奥列宁发现的披肩是由十一块金板块(薄片)组成,其边缘装饰着宝石和珍珠。在其中六块金板块的中间填满了珐琅釉,在珐挪釉上漏刻出几幅金质圣像:“耶稣受难”、“圣母”、“圣伊琳娜”、“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和两名手里拿着十字架的圣徒。同时从关于拜占廷的历史资料中获知。阿历克赛·科穆宁披肩是用金丝锦缎制成的,它还有两道珍珠边儿,中间是四块大金板块(没有圣像),板块上装饰着宝石。送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不会是奥列宁发现的这个披肩,因为这种样式要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出现。
奥列宁在一八二三年重访古老的梁赞,据说,莫诺马赫的披肩就捏在那儿,然而,他一无所获。但是有人对他说,在他到来前不久,农奴费奥多尔,格尼洛雷鲍夫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宝贝。格尼洛雷鲍夫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是用鞭子揍他的时候,他招认挖到了一只精致的铁匣子,里面放着揉成一团的锦缎衣领,上面绣着珍珠和四块金片,金片上镶着宝石。他把这只匣子卖给了位不相识的老爷,老爷给了他十五个半卢布和五桶伏特加酒。那位老爷的姓名他不知道。格尼洛雷鲍夫又被揍了一顿。在两次受刑后,他死了,死者留下的十二个卢布被没收,其余三个半卢布给了他的家属。事情到此结束。
有关“格尔莫格诺夫披肩”的消息时断时续。
在一九—一年,为皇帝陛下接受呈文的办公室以皇帝名义给我们博物馆转来一封匿名信的副本,署名为“俄国爱国者”。他向尼古拉二世宣称,“莫诺马赫的披肩”在他手里,而他将荣幸地把它献给皇帝陛下。然而,影响他履行自己对沙皇和俄国人民尽天职的是:“在皇帝身边有个窃贼格里什科·拉斯普廷。因而只有当格里什科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和近卫军团象征自由的鼓乐声中被纯正的东正教徒吊死在白杨树上时,披肩将在皇帝的瑰宝之中找到一席荣誉之地。”
杜贝尔斯基上校对我发誓说:一周后,匿名信的作者和披肩都将被找到,然而搜寻毫无结果。在拉斯普廷被杀死后,披肩仍然没有”在皇帝的瑰宝之中找到一席荣誉之地。”
第五章 莫诺马赫的披肩和修士大司祭的好心肠上帝
[披肩是教士胸前垂在两肩之间的金银宝石装饰物。——译者注]
一
“怎么,你是厨师的孩子吗?”我问坐在我对面的卡尔塔绍夫,“把你养活得又高又壮,吃得胖胖的。”
“说的太对了。”他肯定了我的推测,“不过,我想,你好象是另有所指吧?”
“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想,象你这样滔滔不绝地描述珠宝钻石,恐怕也只有厨师的孩子才能胜任。”
卡尔塔绍夫大笑,笑得腮帮子上的肥肉颤动,搭在大肚皮上的金链也被振得直跳。
“怎么?是说厨师的儿子吗?你的目光可太锐利了。饥饿……假如我是一个诗人,我要为饥饿写一首赞美歌。为什么?饥饿把我们厨师的孩子们造就成为美的鉴赏家、反抗分子、发明家、诗人和思想家。饥饿可以使人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人吃饱了是无所做为的,只会坐享其成。拿你来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想为人类造福,想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饭。我认为,你不会成功。不过,倘若实现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羡慕子孙们:那是进步的终结,是停止、腐朽和死亡。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饱的——那比瘟疫还要可怕的多。遭受脂肪流行病的折磨那可太痛苦了!”
“你本人不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吗?”
“根本不是。”他又大笑,“根本不对,我不能算是吃饱了的人,而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这可不是一码事。”
“努,瞧你的体格……”
“哎呀呀,这同体格不相干。我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请相信我好了。我对自己的胃口挺满意,我的祖先: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在上个世纪把胃口养得不错。他们太饿了,也许到了我的重孙子那一辈才能吃个饱。”
我问他对克贝尔的看法。
“俄国珠宝业最优秀的大工匠之一。然而,他很不幸,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犹如脚上的镣铐:妨碍行动并硌路得两脚作痛。”
“你很习惯形象思维。”
“这倒是实话。我说什么?对了,关干克贝尔。我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位对宝石和有价值的宝石史颇有研究的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诗人和极为正直的疯子。疯子,要明白,这可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疯子。他不是那种智力受到损害,四肢爬地的疯子。他的疯颠是在于天才,是崇高的,我甚至想说,是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
“正是如此。不过。这只在我们俩之间说说而已,不会告知给他。”他用手指朝上戳了戳,“就连上帝也多少有些……他创造了人类并给于他们各种恶习,他没有想出任何好办法以使人类遵守圣经上的十诫!克贝尔也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喜欢并擅于言谈。他津津有味地讲着各种奇谈怪论和箴言,就象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一道美味的外国大菜:细细地咀嚼着并怡然自得地眯缝着眼睛。
他以一种荒唐可笑的方式谈完了对克贝尔的看法后,就又口若悬河地谈起了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宝物。可是,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讲,我的思想巳集中在即将进行的同修士大司祭的谈话,此时修士大司祭正坐在杜博维茨基那里等我。老实讲,我可以随时把卡尔塔绍夫打发走,这完全取决于我。然而,我却有意识地推延与季米特里见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块断木板,可是其主人又证明自已不在现场;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周游”了一番;我们找到了一张珍宝清单,可是这张清单又似乎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宝没有任何关系;克贝尔同梅斯梅尔上校的关系很奇特;审讯时珠宝匠的回答又支支吾吾……
也许季米特里在制造混乱,有意把水搅浑?
我认为,他会这样做。
不过,他愿意这么干吗?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回答是相当困难的:季米特里是俄国东正教教会正常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轮子,而且这个“轮子”在某些方面又与众不同。法衣圣器室执事的想法和做法并非永远符合俄国宗教界的通常惯例。
还在童年的时候,在我怀疑有上帝存在之前,我发觉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上帝,而每个上帝又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在我的父亲——一个农村牧师,一个要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和染上酒瘾的牧师的观念中,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教区监督司祭,反对喝酒,在做弥撒的时候,上帝会为区区小事训斥牧师们,威胁要取消其教职。父亲不喜欢上帝,然而却又怕上帝,一有机会就尽量地去献殷勤拍马屁。
对于我的母亲——一个面色红润、心宽体胖,整天嘻嘻哈哈的女人来说,上帝很象在两次酩酊大醉间歇时的丈夫:每当我的父亲祈祷赦免其酗酒之罪时,可谓是个好牧师和模范丈夫。母亲如同亲人似地与上帝讨论各种家庭纠纷,和上帝共享微小的家庭欢乐;商量、诉苦、恳求上帝别忘了在什么人而前求情,好让长子能进人中等学校,而后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可别象丈夫这个样子。对于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也就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来说,上帝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和哲学家,永远不知疲倦地为地球上的居民谋求共同的幸福。修士大司祭心目中的圣明而又慈悲的上帝如同他本人一样,对全世间的生活,亿万人民日常所关心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些人们根本不愿意互爱互助,谦让容忍,因此不断地发动流血战争、造反和革命,就是在暂时平静的年代里——也是枪毙、屠杀、暴虐和醉后斗殴。休金的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存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地骗他。可是他,不管怎么样,却总是容忍和与人为善。
若用卡尔塔绍夫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可以把休金称为“最正直的疯子”,他总是试图把宗教信仰同理智、良心、正派和社会平等统一起来。
中等学校的任何一名教师,甚至包指自由党人,语文教员索林在内,如果在学生宿舍里偶然发现了一沓规规整整放在床头小柜上的号召推翻专制制度的传单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向校长报告。休金却不去告密,他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甘愿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上帝,而不是校长,也不是总监。后来,过了许久,当我在彼得堡为躲避警察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接二连三地更换自己的住所。休金已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了,他建议我到瓦拉姆变容节修道院去避难,并在百忙中抽空同我聊天,并想同我辩论。为了救助这个国家罪犯,修士大司祭冒了许多风险,但他毫不迟疑铤而走险。同时,他也是俄国教会主教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被迫炮击了被士官生占据的克里姆林宫。不能说克里姆林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心理上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不过,有些炮弹毕竟还是损害了尼古拉塔楼、别克列米雪夫、特罗伊茨克塔吉楼和邱道夫修道院的正门、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教堂。炮弹的碎片落到了斯巴斯克钟楼上的自鸣钟上,自鸣钟停摆了,再也不能奏出:“愿我主在天之灵保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的“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侧祭坛的穹顶也被打穿了。
这次炮击是教会发起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借口。一份有号召力的,标题为“来自圣克里姆林宫的求救声”的呼吁书,很快就被刊印问世,主教会以惊人的速度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搜集践踏莫斯科圣址的事实,并委托涅斯托尔主教写一本《炮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也很快问世了。毫无疑问。季米特里以与众不同的狂热参加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信仰的上帝的私敌,因而也成了他本人的私敌。当我受市苏维埃主席团的委托参加制定维修的预算时,卫戍司令的助手同我一道去察看建筑物的损坏情况,陪同我们的季米特里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回答问题时怒气冲冲,双眉紧锁,态度生硬。修士大司祭固执地重复“炮轰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终于把为人和善、性格恬静的卫戍司令的助手惹火了。
“修士大司祭公民,我们开枪不是要射击克里姆林宫,而是打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匪强盗。”他说。
“那是些孩子。”季米特里说。
“不是孩子,而是士官生,”卫戍司令的助手反驳道,“士官生不是孩子。孩子玩的是玩具,而不是步枪和机枪。孩子不会开枪,只会喝粥。平心而论,与其说我们,还不如说你们,信徒们,对炮轰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怎么解释?”
“是谁允许士官生们把机枪架在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的钟楼上、伊维尔小礼拜堂和谢尔盖大教堂上的呢?是你!如果钟楼上不架机枪的话,就不会用大炮去轰击。”
“教会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器去亵读教堂。”
“修士大司祭公民,这已是事实了!”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