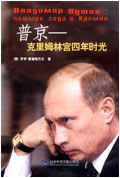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识医治精神病的医生吗?”
“我甚至能帮你搞到一个单间病房。”我有把握地说。
“门锁结实吗?”李图斯笑了,“我对你非常信任和尊重。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请……”李图斯朝站在无政府大厦入口处的哨兵使了个眼色,为我们推开了门。
平时无政府大厦象个喧闹的蜂箱,这一次却静得出奇。在一层楼设有联盟会议秘书处、宣传部、黑卫军司令部、阅览室和出版社,房间里空无一人,阅览室里也仅有几个人,在前厅站着一群黑卫军士兵。
李图斯找到了格雷兹洛夫,并把他带来见我们。
格雷兹洛夫显得比平时更忧郁,他头也不抬,对自己的助手说:“李图斯同志,你去吧,去把巡逻队整顿一下,安排好,告诉他们,无政府主义也讲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不能再发生流氓闹事了,李图斯。”
“再不会发生那种事了,”季马·李图斯保证道,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口上,“你了解那个摔跤运动员,他是个疯子,甚至无缘无故就咬同班同学一口。”
我等格雷兹洛夫提起巴里案件,这起案子同他有直接关系,但他只字不提。他默默地把我们领进一间小会客室。在征用了这所私邸后,就把联盟的宣传部设在这儿了。克鲁鲍特金的门徒把会客室搞得象藏书室:房间里摆满了书柜,书架上摆着普鲁东、马科斯·施蒂聂尔、巴枯宁、克鲁鲍特金、沃尔斯基、阿德列尔、博罗沃依和普罗费兰索夫的著作。在靠近窗户的长桌上放着许多合订本,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之声》、《海燕》和哈尔科夫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一大堆书中,有一本封皮特别鲜艳的小册子,这是莫斯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的作品,书名是《为什么?或农人是怎样站到了无政府主义这一边》。墙上,在前主人留下的两个顽皮的酒神中间挂着一张由联盟的另一位领袖列昂·切尔内绘制的俄国未来体制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委员会被“联合大会”所替代,替代各委员部的是“协议院”;有“外交协议院”、“军事海洋事务协议院”、“教育协议院”……
“宣传部的同志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向格雷兹洛夫。
“开大会去了。”
“我们事先同什捷伦约好了会面。”
“稍等一下,什捷伦同志就来见你们。”他说,并建议我们,“你们随便找点什么读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请你们喝上一杯。我们现在把印刷厂的仓库改成了地下酒窖,因为小伙子们找到了许多酒。”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坏呀!”苏霍夫嘲笑道。而我却关切地问;“还要凭票往下发吗?”
“我们准备送到野战医院去,供为了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享用。”格雷兹洛夫以忧郁的表情对我解释道。
“帕维尔,你喜欢香槟酒吗?”我问苏霍夫。
“我不喝酒。”
“听见了吧,我的同志不喝酒,只好谢绝了。是在二楼开大会吗?”
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第一次抬起了头。他的一双眼晴既浑浊又深沉。从前我见过一个在屠宰场干活的工人,就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那个工人是屠宰行业的能手,一锤子就能敲碎母牛或公牛的颅骨,主人非常看重这种人。
“跟往常一样,大会在天蓝色大厅举行。”格雷兹洛夫不大情愿地说道。
“那么,我们就去那儿。你不反对吧?”
苏霍夫惊异地望着我。他不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个怪念头。
“想去参加大会,那就请吧!”格雷兹洛夫说,“我们这儿用不着通行证,也没有代表证,自由参加。”
四
宽敞的大厅先前是莫斯科商人举行舞会和宴会的地方,此时散发着几百人的汗臭味。人们有的坐在沙发椅子上,有的坐在临时搬的凳子上。通路被堵死了,我们只好站在门口——再往前挤不动了。
据我判断,莫斯科各小组和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都出席了大会,其中也有“独立大队”,它不是联盟的成员,也不承认联盟,因为“联盟做为一种机构限制了革命者的人身自由”。
主席台后面的墙上交叉地挂着黑旗。在主席团就座的有:患肺结核的奥尔尚斯基,医生已断定他活不久了,可是为了气气资产阶级,他偏要活到世界革命来临的那一天;“刻不容缓”者的首领涅沃林,后来成了马赫诺分子(一年后我在彼得格勒碰见了他,他是以“面包专列”指挥的身份到彼得格勒来的,在列车的车厢上写着:“马赫诺老爷子把面包送给正在挨饿的彼得堡无产者”);“大学生小组”的头头,美男子察尔斯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加斯捷夫,后来他做为苏联劳动学术组织的奠基人载入史册;还有紧挨着“独立大队”领导人坐着的是一个头发梳得光滑,模样可亲的女人,这是来自沃罗涅什的女客玛丽娜·尼基福洛娃,就是她的匪帮后来采用恐怖手段骚扰了乌克兰的城市和村庄。
我无论在主席团里,还是在大厅里都没有看见“老爷子”,萝扎·什捷伦和克鲁鲍特金的门徒。工人很少,仅有几十个人。可是、大会却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分看重莫斯科联盟的作用和影响。把无政府主义者看成一种可以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还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兆,体现了以普加乔夫为先驱的俄国农民的愿望,它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任何权力,但是对土地的要求例外,因而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未来。
某些人期望黑卫军能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主张立宪,尤其是对君主立宪格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极左派”吓倒。卡尔塔绍夫教授在同我谈话时曾说。地球是圆的,如果从左边走太远,那么就从右边过去……
卡尔塔绍夫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教授坐在大厅的中央,身边坐着一个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的好学的美国人,显然,他绝不会放过在于政府大厦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从手势看,教授正在向他解释什么。我看见,坐在美术理论家身后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不讲究衣着,手持长柄眼镜的太太。她的相貌我觉得似曾相识,对了,这肯定是莉扎·捷沙克。美国人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呢!俄国的废止主义者,她从生下来直到暮年都在西特洛夫卡市场上混,是英国人约翰逊·布特列尔的狂热追求者)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卖淫自由的斗争。看样子,美国人很了解上个世纪末轰动一时的英国妓女去国会请愿的新闻,可他未必能想到,紧挨着他坐的这个女人是莫斯科妓院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的组织者……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何时起莉扎·捷沙克也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好感呢?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而苏霍夫低声骂了一句:“狗崽子,别得意!”
他骂的是正在演讲的联盟书记。
“革命理论工作者的争论不在于援引名著,寻找论据和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历史。”演说者提高了嗓门,越说越激动,“历史,才是一切理论和体系的最公平的审判官。”他高高举起双手,好象要把历史召进大厅并无拘束地同出席大会的人聊天。“让我们回顾几十年前的历史,当时马克思确信,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巴枯宁不同意这种论点。马克思确信,世界革命的旗帜将由德国的无产阶级举起,巴枯宁也反对。巴枯宁写道:‘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时,要说:‘我是自由人’。德国人会说:‘我是奴隶,然而我的皇帝比世界上所有的帝王都强大。德国的士兵扼杀我,他也在扼杀你们所有的人。’巴枯宁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尚,德国人倾向于国家强权。’而现在,一九一八年的二月,我问你们,无私无畏的勇士们:谁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谁是世界革命的先知者——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演说者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口哨声、狂叫声中,几百只脚在地板上跺着。
莉扎·捷沙克从座位上跳起来,挥动着长柄眼镜,尖声地喊叫着什么。场内椅子吱嘎作响,板凳乱扔。对猛然迸发出的狂热感到满意的演讲者等着喧闹停息,然后挥动着胳膊,好象在指挥乐队,继续说道:“国家组织这个祭坛—一正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碰到的大难题,犹如难以逾越的一块巨石。不,不是德国人、国家主义者和市侩,而是天生的斯拉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世界上举起了摧毁万物的反抗之旗。它,只有它,才被历史这个聪颖的老祖母指定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而这场革命把剥削者扼杀和淹死在血泊之中!彻底摧毁国家、法律、教会!摧毁一切丑化人,使人变成残废和沦为奴隶的制度。革命是飓风!革命是龙卷风!革命是狂涛骇浪!谁能阻挡它呢?是市侩的德国人吗?不是,绝对不是!全俄的革命暴动将如巨浪一段把德国人碾成粉末,防日耳曼人的师团打个落花流水!”演讲者在狂叫,“让威廉皇帝吓得发抖吧!让他的将军和士兵们吓得发抖吧!斯莫尔尼宫盼望德国发生革命——我们对此根本不寄予希望;斯莫尔尼宫里的人正准备向德国资本家妥协——我们不走这条路;斯莫尔尼宫在祈求和平——我们要战争,反对压迫者的全球革命战争。不能同德国的市侩们谈判,不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要高举血染的世界革命大旗驶遍欧洲、亚洲和美洲!前进吧!”他高喊着,把紧握着的拳头向前伸出。
大厅里的人们发狂了,吊灯上的水晶玻璃坠儿被喊叫声和号淘大哭声震得叮当作响。参加大会的人好象已整装待发,立刻“前进”,用暴动者的棍子敲碎傻瓜们的脑袋,让世界革命的旗帜席卷欧洲、亚洲和美洲。而演讲人,似乎还未做好准备,总之,在结束了自己的煽动性演说之后,没有往前进,而是谦逊地向后退去,重又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
“关于派黑卫军上前线的事只字未提。”苏霍夫清醒地发觉了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儿耍嘴皮,而同德国人打仗的是布尔什维克。”
无论演说的风格,还是演说的针对性,都证明雷恰洛夫告诉我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
是的,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还不能同德国人签订和平协议,那么,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联盟可能会挑起事端;狂热已达到病态的程度。下一个发言的是“老爷子”,但是我们没能听到他的演说。此时,季马·李图斯穿过大厅里的人群来告诉我们,什捷伦同志已在楼下等我们了。
在位于楼角、挨着阅览室的那间房子里,除了萝扎,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头发蓬乱,满脸雀斑,尽管是冬天,但衣着讲究。萝扎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谢苗“同志”。从那他傲慢的阴沉的脸色看,他已知道请自己到这儿来的目的,并已准备好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怎么,去听大会了?”萝扎问道,同往常一样又忘了答礼。
“我想试试,能否改变自己的信仰。”
“你可改不了,”她冷笑了一声,“你是块硬石头。”
“你们的演说家说得太好了。你要是听了他的讲演,就立即会站在黑旗下,带着……怎么说的,对了,带着棍棒……”
萝扎皱起了眉头,她可受不了我开笑玩。她是一个极严肃的人,对幽默所持的态度近乎我对尼罗河鳄鱼的恐惧。
大大的眼睛,黑黑的肤色,她很象吉普赛美女。她若是戴上耳环、手镯、项链……但是,唉,远在十年前她就把自已那两条漂亮的辫子剪掉了,她认为长头发不符合她心目中职业革命家的形象。
雷恰洛夫想错了,他认为我对萝扎的印象不好。萝扎不仅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而且是个正派人,一个好同志。我所否定的仅是什捷伦——不是女革命家。革命需要象雷恰洛夫这样的革命者,而不是什捷伦。
我很理解什捷伦大动肝火的原因:她很不喜欢格雷兹洛夫过问肮脏而愚蠢的巴里丑闻,联盟为此事被迫放弃所持有的毫不动摇的原则,萝扎真诚地认为,上述原则是存在的不能帮助和支持那些“国家主义者”,他们幻想的是把革命引入死板的模式中去,给那些虔诚膜拜人民天性的“真正革命者”设置障碍。
她很认真地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次会令不快的义务,并竭力完成它。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把一切搞复杂了。萝扎企图借助我和苏霍夫让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了解对盗窃国宝案的侦破情况,稍微迟来的“老爷子”和季马也想协助她。
谢苗“同志”沉默不语,把蓬乱的头发弄得更乱。
三位知名人士都在给我施加压力,需要明确的答复,需要获得详细情况以及挑逗性的问题接耀而至:
“在法衣圣器室里发现了犯罪分子留下的什么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能确定什么吗?”
“谁有盗窃嫌疑?”
“审讯了哪些人?结果如何?”
“掌握了哪些证据?”
“你们最近有何打算?”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我和苏霍夫难以对付。我们俩人事先就说好不向无政府主义分子介绍侦破情况,但是不回答是不行的,所以不得不想出一些推托之辞和模棱两可、不致招惹麻烦的回答;要么就干脆说句笑话敷衍过去。谁能窃走宝物呢?如果我们知道是谁,那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无政府大厦里……
初步推测吗?那就太多了。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象什捷伦,“老爷子”,和李图斯这样大忙人的宝贵时间呢?谢苗“同志”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初步推测呢?这只会把他弄糊涂。审讯吗?只是走形式,绕来绕去兜圈子,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萝扎·什捷伦对这些回答很恼火,可是火暴性子的“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