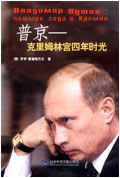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萨拉托夫省刑事侦察局局长
普里瓦洛夫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亲启
因电报线路发生故障(尚未查明故障原因和地点),同萨拉托夫的电报联系暂时被迫中断。待修复后立即告知。
莫斯科市电报局政委
伊万科夫
第八章 钻石窖
一
值班的赤卫队员是一个身穿棉袄留着大胡子的老工人,他象见了老熟人似的同我问了好。
“是见电报局政委吗?谁知道他怎么回事,一忽儿到这儿,一忽儿又去那儿。这可是个闲不住的,使人坐卧不宁的差事……兴许是在第二报务室吧?”
“那么我们就去第二报务室好了,”我对阿尔秋欣说。
“可能就在第二报务室。”他表示同意。
在用黑皮革包着的门上钉着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与本室无关人员严禁人内,末尾是六个又粗又大的惊叹号,确切地说,是五个半,因为剩下的那点儿地方写不下第六个惊叹号了。阿尔秋欣对这句话奉若神明,他疑惑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算无关人员,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说道,“我们在这儿是自家人。”
阿尔秋欣头一次陪我到电报局来,他不大相信我说的话。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他巧妙地表示赞同,“好象不大热闹……”
“不会热闹的,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很有把握地说,“再说,星期四我空着肚子就打喷嚏,星期六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阿尔秋欣的脸微红,说:“假如是星期四,那就要受到夸奖,而星期六会如愿以偿……”
“正是这样!”
报务室里鸦雀无声。休斯式发报机就象士兵似的按规定的距离列成横队。机台上全是白黑两色的按键。在按键的上方是报务员的后脑勺。字盘和圆板在叉形装置上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象家里的钟表一样滴答滴答作响。报务员不时地用脚把一普特重的重锤往上提一提,上满弦。窄窄的白色带子缓缓地向外脱出。它告诉人们在俄国南方的战况,日益迫临的饥饿、伤寒,匪首杜托夫①,没收普罗柏印刷公司以及有关契卡在彼得格勒的活动情况……
【 ①杜托夫:高尔察克的伙伴,1917-1920年在乌拉尔组织反革命暴乱活动。】
阿尔秋欣站在一张机台后面,小心翼翼地用手指碰了碰窄带子。
“人的脑子真是大聪明了,什么都想得出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电报局政委,瘦瘦的个子,红鼻头上戴着夹鼻眼镜,手指头上尽是墨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站在报务室里的一个角上,站在堆满了轴带的桌子后面,神经质地扯自己的头发,好象在检查自己的头发是否牢靠地长在头皮上。
他不用看就知道是我来了,因此没有转过身子就说:“接不通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还从一大堆带子轴中挑出一轴,递给了我,“萨拉托夫搞什么鬼名堂!您自己看看吧……”
带子上打印着:
“通告。今天早晨七点整接到政府通告,我国和平代表团已于昨天,三月三日下午五点钟,同德国及其盟国签定了和平条约。代表团此刻正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和平条约的文本将在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公布。和平条约的批准,即条约的最终确认,定为三月十七日由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是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召开的,大会将于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开幕。
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人民委员会”
透过我的肩头读完电文的阿尔秋欣满意地笑道:“感谢上帝吧!再坏的和平也比善意的争吵强多了……”
政委没有听他说话,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两眼噙含着泪水。这位政委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反对接受德国人的最后通谍的八十五名委员的心腹。对他来说,这封电报是俄国革命覆灭的证据和对刚刚开始的世界革命的打击。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和对整个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正是有了这个信念他才没去国外去谋生,而去服苦役,坐单间牢房……
我理解他,但不同情他。我同情的仅仅是强者,我对弱者只是怜悯而已。当然,进攻比退却更能令人感到痛快。但是真正使部队得到锻炼的却是在退却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反抗分子的棍棒,而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要利用当前的喘息机会建立一支有纪律的武装部队。
“有手帕吗?”
“什么?”
他听明白之后,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涕。
“请原谅……激动了一点……”他略安静后,说道:“代表大会不会通过这个条约。”
“我想,能通过。我希望代表团的成员们能够脚踏实地,而不是想入非非。”
他冷笑了一声,尖酸地说:“至于你嘛,科萨切夫斯基,就不仅是脚踏了,而是四肢着地啦。”
“那就更稳妥了……萨拉托夫的情况怎么样?”
假若电报局的政委要骂街的话,他准会把我臭骂一通。然而,他已经是第四代知识分子了,因而他不骂人,只是提高了嗓门,抱怨地问道:“哎呀呀,你为什么还提这个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房子起火了,而你……这会儿谁还需要那些黄金呢?要它有什么用?”
“黄金就是军队。”我说。
政委恶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他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的青筋暴涨。坐在邻近机台旁的报务员正瞅着我们。
“你对革命军队很有信心吗,科萨切夫斯基?”
“什么时候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我问道。
政委叹了口气,推开他面前的那堆带子,有气无力地反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吗?……让我们先到走廊里抽一会儿烟,在那儿我们接着谈……”
说老实话,实在没什么好谈的。电报局的政委是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已经知道波克罗夫斯基将出任莫斯科市和省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也知道彼得格勒已决定迁都莫斯科;政委还知道在自由市场上有多少牛肉,从西藏进口了鹿茸;也知道在叶卡德琳堡①如何执行国家对火柴的控制,在罗斯托夫打死了多少白匪军以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从投机商人手里没收了多少黄金。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依他看,只有高级人士或者电信总局的电报处处长奇奇金才能知道这件事。
【 ①叶卡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的旧称(1924年以前)。——译者注。】
高级人士都在很远的地方,而奇奇金却近在眼前。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就去找他。……”
我们一起前往。同这位政委相比,奇奇金较为冷静、温和和乐观。同德国人讲和使他高兴,他生就是个乐天派,看来,正是这个缘故,在一九一八年尽管吃着量少质差的饭食他也能发胖。
当然罗,奇奇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但他相信,当我迫切需要时,通讯会恢复的。
“将全面恢复革命秩序,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毫无疑问,也会恢复的。”
“什么时候?”
“很快。”
“一个月以后吗?一年以后吗?”
“今天。”
“几点钟?”
“晚上十一点钟。”奇奇金毫不含糊地说,他那肥厚的手掌啪地一声打在桌面上,象是打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十一点不一定……”政委迟疑不决。
“十一点。”奇奇金重复了一遍。
“准时吗?”
奇奇金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以一个老革命者的名义发誓。”
奇奇金自认为是个老革命者。电报局政委曾对我讲过,十二年前,大学生们闹事的时候,当时奇奇金也是个大学生,鼻子被一个警察打出了血。尽管这段小插曲在俄国革命运动史册上算不上金色的一页,但奇奇金喜欢回顾它。
“请在十一点整到报务室来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将同萨拉托夫通话,”奇奇金说。
“你最好能事先给我打个电话,科萨切夫斯基,”当我们离开“老革命”的办公室后,政委说道,“我非常怀疑今天能恢复联系。”
“就是嘛!”阿尔秋欣随声附会道,奇奇金的那番话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俗话说,柴禾堆里找不到草料,欠债人那儿找不到钱,手心里种不出粮食……”
“大对了,太对了,”政委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说大白话。”
但是他们都错了:联系确实于夜间十一点整恢复了,然而不是在当天,而是一周以后……
二
我们步行回到了位于彼得洛夫门的刑事侦察局。
没被踏过的白雪和宁静无人的林荫大道极其洁净美丽。只有特鲁坡那边有些影子在晃动:大概是在做买卖。栖在树枝上的乌鸦乏力地叫着……
代表大会能否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我不能做出肯定答复。一切都变幻莫测,大令人难以捉摸了。脚下的雪松软而易碎……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阿尔秋欣在喊我。
“什么事?”
“这是怎么啦,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寄,全部三千万,就象花一个戈比那样,都用去买步枪和包脚布吗?”
从他的语气中我明白了,他不同意我的计划。阿尔秋欣是个会过日子的庄稼汉,他知道,如果在军用仓库里找一找,能找出不止十万支步枪。
武器不是肉,也不是油脂。在一九一八年,武器是不值钱的。在苏哈列夫卡一支最漂亮的左轮手枪只能换到四俄磅油脂,一挺机枪的公道价格是……
“三千万这个数字不准,而是二千九百万将用来购买军用物资,”我同他开玩笑道。
“真有你的!”
他不吭声了。
“那一百万干什么用?”
“另有所用”。
“用在哪些方面?”
“那还少嘛!比方说,给那些出色的战士买金牙……”
菲立蒙站住了,立在雪里发愣。
“嘲笑人吗?”
他大笑,摇晃着树于。从树上落下的雪花犹如一等面粉那么细白。这使我想起,昨天曾遵照雷恰洛夫的命令,分给刑侦局每个工作人员一俄磅黑麦面粉,这是对消灭了四名武装匪徒的奖励。
现在每天下午两点整,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就会响起来:雷恰洛夫十分关心来自萨拉托夫的消息。
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啦?在生活里我最不喜欢情况不明。一切都应有始有终。
……这次,当有人轻轻叩旅馆房间的玻璃门时,第一个醒来的不是我,而是菲立蒙。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摇晃我的肩膀,“通讯员来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屋里的灯已亮,我对刺眼的灯光还不习惯。我怎么也不能从睡梦中醒过来。吊灯的灯光一会儿聚成一束光点,一会儿又散为浑浊不清的黄色光斑。
“通讯员?什么通讯员?”
“从喀山铁路管理局来的,”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床旁站着一个穿棉袄的小伙子,他头上戴着缀着红缨子的带兔皮长耳罩的棉帽。
“是找你的,”阿尔秋欣说,“找你本人。”
“紧急电报,”小伙子清晰地说,并递给我一个蓝色的长信封,封面上还印着过了时的盘踞在皇冠下的双头鹰。
我坐在床边,两脚垂地。阿尔秋欣把短皮袄披在我的肩上,房里很冷。
信封里装的不是电报,而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局政委用那潦草的字迹写的便函。政委写道,他用直线电话同梁赞分局局长通过话。莫斯科刑侦局的特派小组已从萨拉托夫到了他们那里。小组带着贵重物品(后两个字的下面划了横道),由四名赤卫队员组成护送组负责押运。根据梁赞运行处政委的命令,已将小组成员和护送物品的赤卫队员安排在监察员专用的车厢里,挂在十分钟后即将开往莫斯科的邮车上。小组组长博林同志请政委迅速将此情况通知我。他还要求派人去接从梁赞来的小组……
莫非这张便条预示着牧首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即将结束了吗?
阿尔秋欣不解地瞅着我。
“大概是给军队买的包脚布运到了,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当我得知通讯员是乘政委的汽车来到旅馆时,我请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烟,赶紧穿好衣服。阿尔秋欣看着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现在的差事比沙皇那会儿还难干,”当我们三人下楼走到前厅时,菲立蒙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着,“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静。”
“将来让你睡个够,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我算什么?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觉。”
当然,阿尔秋欣说的很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乘政委的汽车先到了铁路局,然后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最后来到了刑侦局。帕维尔·苏霍夫已经在等我们了。
……从梁赞开来的邮车,在整个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时刻表准时到站。这种情况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电话通知我火车已进站的车站值班员感到惊异。
在我同他谈完话,挂上听筒半个小时后,两辆小汽车开进刑侦局的院里:在警车上坐着赤卫队员,在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那辆车上坐着博林和沃尔任宁(后来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暂时留在萨拉托夫)。撑着雪橇的纠察队的战士们紧跟在汽车的后面,飞也似地驶进了院子。
“停车,停车,老弟!”沃尔住宁对司机喊道,他站了起来,在一群刑侦局的战友面前特别惹人注目。
汽车转了半个圈,车轮在冰面上直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