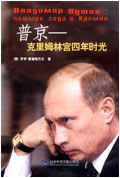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色如同鸽子血的钻石甚至比“婆罗门”还名贵。印度教徒认为,有这种颜色的钻石是幸运儿,他永远得到皇上的欢心,他会获得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不必担心灾难的降临。颜色均匀的红金刚石是极为罕见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就是这种金钢石,确切地说,是钻石,因为已经过琢磨加工和抛光。
宝石越大宝石上的光泽闪变就越少。但这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是不适用的,它的重量有一百一十六又四分之一克拉,但它的光泽闪变甚至胜过一颗重量不到百分之二克拉的小钻石。
“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上下两端呈八角形,为三棱柱体。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类似的钻石……
苏:请谈谈“三少年”。
克:这是三粒黑色象形珍珠。其中一粒重二十九又四分之一克拉,另一粒——二十四克拉,第三粒——二十三又五分之四克拉。
获得黑珍珠比找到玫瑰色或灰色珍珠的机会少六十倍,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苏:你刚才说“象形珍珠”,是什么意思?
克:象形珍珠是指珍珠的形体很象人或动物躯体上的某一部分以及花的形状。尼康牧首法冠上的两粒象形珍珠很象人头,而最大的那粒则象埃及的三角形十字架,也就是说很象字母“T”的样子。
苏:“苦行僧”是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宝石吧?
克:是的,这是菲拉列特牧首拐杖把手上的宝石。
苏:清单上写明,这是一颗蓝宝石。
克:对的,是蓝宝石。在它的表面可以看见带有珍珠般闪烁的小星,这是蓝宝石中最为贵重的一种,被称为阿斯杰利克斯或称什捷尔撒波菲尔。这颗蓝宝石重三十六点五克拉。它上面没有一点儿缺陷,一般来说,刚玉——是蓝红宝石所固有的缺陷。
苏:“苦行僧”是属于哪种颜色?
克:它的颜色不是单一的,有多种颜色。如果在白天从上住下看,是深蓝色,色调柔和;从侧面看,光线从侧面照射过来,它就成了绿色;夜间在灯光下——几乎是黑色。
苏:“圣母泪”也是钻石吗?
克:它是一颗纯净如水的无色钻石,镶在十二世纪的福音书金书 上,重量不下三十一克拉。
苏:它是怎样磨成的?
克:当代的金刚石琢磨方法还是路易·贝尔格姆在十五世纪中叶创造的,而福音书金书 的装饰是一九一二年完成的。那时在金刚石的晶体上只磨成了上帝赐给的上部四个棱角——尖椎形,下部还掩藏在框子里,没有动过。
苏:为什么那颗重量为三十八克拉的红宝石在清单中被称为“特级公爵”呢?
克:“特级公爵”不是红宝石,而是缟玛瑙红宝石—一它具有红白两种颜色。“特级公爵”被磨成了两头圆中间较粗的球体。它的样子象鸡蛋,一头粗,而另一头尖一些。球体的上部呈白色,下部为红色。它被起名叫“特级公爵”是因为它曾属于某位梅尼什阔夫公爵所有。卡尔塔绍夫教授讲过,梅尼什阔夫很喜欢冠冕堂皇的封号。他曾被命名为圣罗马公爵和俄罗斯公爵、伊约尔公爵、杜伯洛夫诺伯爵、戈尔卡赫和波提那的伯爵、最高统帅、大元帅、红旗海军上将……他的佩剑上的宝石与他的每一个封号相对称。缟玛瑙红宝石好象是标志红旗海军上将的封号。梅尼什阔夫被流放后,他的佩剑也失踪了。后来公爵佩剑上的缟玛瑙秒红宝石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手里,这位女皇又把它送给了波将金。遵照波将金的指令,缟玛瑙红宝石被镶嵌在香炉上。这个香炉和沙皇达官贵人的其它用品一起从十八世纪后期就被放进法衣圣器室。
苏:在某处是否存有法衣圣器室失窃的宝石和珍珠的画片或照片?
克:没有。不过,如果刑事侦查局的先生们想要看的话,那可以看看我搜集的仿造宝石,它包括了收藏在牧首法衣圣器室和乌斯宾大礼拜堂法衣圣器室里的全部特大宝石。
记录无误。克贝尔(签字)
第二章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罗特斯尔德是革命前的金融界巨头,后进入国际金融界。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
一
大理石的楼梯很宽敞,镀金栏杆上包着红色丝绒套子,警卫室的一位年青红军战士在楼梯口对我的通行证查看了好一阵子。年青人的皮带上挂着一串自制炸弹。我们直到十月革命前不久才能在古容工厂里生产这种炸弹。
在扔出“古容”之前,先得点燃火柴形状的引伙线,因而红军战士都在左袖头上缝了一块特制的涂着硫磺的小木牌。检查我的通行证的那位小伙子棉袄袖头上没有这种小木牌。
“爆竹可点不着啦!”
这并没有难倒他,在把通行证还给我后,他说:“干吗要点着它呢?就是不点它也能把脑袋砸碎,这可是生铁铸的!”
原总督院内的卫生和井然的秩序使我震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半月前从这里的窗口探出机关枪,底楼变成了小医院、饭堂和武器供应站,镶木地板上乱扔着烟头,木板和废子弹壳。只有一幅被扯成碎片的油面还能使人回想起不久前的情况。这幅画描绘的是亚力山大三世接见地方自治代表团的情景。
“你总是迟到吗?”雷恰洛夫瞅了顺挂在墙上的钟,指针指着二点零六分。
“你的钟快了五分钟。”
“只快四分钟。”他准确地说道。
“好吧,就算是四分钟。只晚了两分钟不能算迟到。”
他笑了笑。
“你总是让我听你的,对吗?请坐。我只能同你谈半个小时。”
雷恰洛夫通常听汇报最多不超十五分钟,他认为,这就足够阐明任何问题的实质、而这一次却给我半个小时,这不仅说明,他多么重视所发生的案件,而且也表明我们的谈话不局限于我的汇报。
“吉洪牧首接见你了吗?”
“没有。”
“看来,他们还没有想好怎样更好地利用这起盗窃案件向我们发难……我希望,不要发生冲突,办得到吗?”
“还没有付诸武力。”
“那很好,”雷恰洛夫说,“而现在……在我看你的报告和记录时,你来看看这个,这是对那份主教公会呼吁书的有趣补充……”
“补充”是指在《俄罗斯新闻》上登载的鲍里斯·萨温科夫写自彼得堡的一封公开信和贵族联合会理事会写给吉洪牧首的致敬信。“冷清的街道,冰凉的雪片……”萨温科夫写道,“满目荒凉.雾露沉沉。赤卫队员同德国军官……德国人巳不再是战俘,他们——是‘同志’了……昨天我们是沙皇的奴隶,而今天我们是列宁的奴隶。明天将是威廉的奴隶。”
_贵族联合会理事会避免了激烈的措辞,可是透过字里行间仍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意图。“俄国的贵族,秉承先祖的遗训,永远同创立伟大的、统一的、神圣的俄罗斯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能,也绝不会同那些对敌人的人侵和淫威漠视不见的人走同一条路。”致敬信的作者竭尽全力说服吉洪牧首:“我们同阁下一道期望着俄国人民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响应您的号召……出于热爱濒于灭亡的祖国而振起,并在自身找到力量去复兴祖国和建立在基督教保护下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同主教公会的呼吁书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严整的反革命观念。
它声称,掌握着政权的人在践踏东正教,糟踏人民的圣物。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道地的异教徒。他们是日耳曼人的间谍,现在日耳曼人觉得在彼得堡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把受教会保护的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教会将引导俄国的东正教徒们去从事反对外部敌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企图把俄国奉献给目已的主子——德国人,使它永远受奴役。斗争,也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拯救自由和东正教的圣物。
教会——保皇党——社会革命党,他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上表现惊人的一致,并时刻准备携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就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案件。是的,雷恰洛夫不会无故占用这么多时间同我谈话: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值得这样做。
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有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做些记号。在我讲完后,他问道:“你怎么看,会在俄国销赃吗?”
“很有可能,回炉熔成金锭和银锭,卖掉小块宝石也不太困难,至于大块宝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怀疑有人敢去买尼康法冠上的独一无二的红宝石、黑珍珠,或者比如说,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巨型蓝宝石。这些珍宝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这也不敢担保,一切都取决于宝物落在谁的手里。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被窃物品流到国外。我争取今天向各省市刑事侦查机关通报案情。”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雷恰洛夫说,“要利用电报。我去商量一下,争取能破例地发布一道政府通告:通报发生盗窃案和失窃物品的简要清单。至于不要流到国外和动员居民帮助寻找的问题,我们明天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我巳拟出决议草案的草稿。第一点,”他继续道:“请全体公民协助寻找和送归失窃的珍宝;第二点,根据被找到的珍宝的价值,奖金可达五十万卢布……”
奖金的数目显然同失窃珍宝的实际价值不相称。
“拿出一百万吧!”我建议道。
雷恰洛夫皱起了眉头。他一贯反对挥霍,早在一九一六年在他负责党的出纳工作时,他发放经费时,就是这副面孔,以致许多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在别处搞到经费,就绝不去找会计。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我知道。”
“也不是里亚布申斯基!”[革命前纺织业大资本家,到一九一三年资本达二千万卢布。反对十月革命。——译者注]
“我明白。”
“是谁给了你和我挥霍人民钱财的权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全室环视了一遍,好象要找到那位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公民。“是谁?”
“没有任何人。不过失窃物品的价值要超过三干万金卢布。”
“反正工人不会来领赏金。”
“如果不是工人呢?”
“六十万。”雷恰洛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数字。
“卢布每天都在贬值。”
“那好吧,八十万,八十万!再多一个戈比也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坚持己见获胜了。
“不过请注意,”雷恰洛夫说,“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我可不会坚持这个发疯的数目。现在再来谈谈草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由外事人民委员通报世界各国有关国宝被窃情况,并请求给予协助,在国境线上截获。”
显而易见,写上第三点仅为了自慰而已,珍宝一旦出了国境,它们就不再属于俄国的了。雷恰洛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对资产阶级不抱期望。他们无时不在冥想,如何对付我们,还谈什么协助呢?他们迫不急待地盼望着德国的进攻……”
“你认为德国人已拿定主意了吗?”
“十分可能。需要军队。列昂尼德,军队!”
“暂缓复员已不行了。”
“我说的是新型的军队,革命的军队。”
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好罗,明天要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知道了,而现在……究竟是谁盗窃了法衣圣器室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在纸上画了两道斜线,在一边写上:首饰匣.在另一边写上;刑事犯,并打上了一个问号。
“那么,有两种说法,而你能排除有第三种说法吗?”
“第三种是什么?”
“先别着急,”雷恰洛夫说,“让我们先看看事实。”
“先看看事实。”他平时在学习小组会上总爱用这句话开始发言,他把各种材料强行灌入听者的脑子里,通过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结论是……”
“第一个事实,”雷恰洛夫说:“盗窃案发生在信仰自由的法令发表之后。因此,因盗窃而受损失的不再是教会,而是劳动者的俄国,被窃的是人民的财产。这是事实吧?”
“完全正确。”
“第二个事实:牧首法衣圣器室是由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负责照看的,他好象是位尽职的人。可是他竟然两个星期没有到那儿去,而当发生盗窃后,修士大司祭根本不急于向当局报告。请愿的人们都知道了被盗的事,甚至听信了教会圣物被窃的谣传,要动用暴力,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当你赶到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已经在那儿了。随便说一句,你错过了时机,没有询问他,不妨向问他,是谁告诉他这里出了事……现在,再看第三个事实,你还记得多布龙拉沃夫大司祭的声明吗?”
“是关于战壕的事吗?”
“是的,关于教会蹲够了战壕,应当走出战壕了。瞧,他们可真走出来了……由于‘教会和祖国’受到了威胁,教徒们从莫斯科的各个教堂来到红场,举行了全民祈祷,结成保卫圣物的同盟会……而你是在教堂附近逮捕了俄国民众同盟[革命前反动黑帮组织]的盟员之后,才对我交给你的那份材料深信不疑……”
“这一切都很清楚。”
“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我们:利用每一次疏忽,每一件意外事故。从政治观点看,在这种时候圣物被窃对教会是有利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
雷恰洛夫用一道粗线把人字形斜线的下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吗?”
“是的。第三种说法——盗窃是出于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