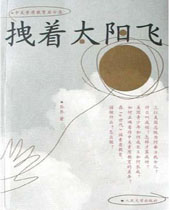太阳鸟-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一说:“你既然来了,何不帮个忙呢?”
“你这个‘既然’说得好。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你那个男朋友呢?他怎么不来帮忙?”
“分手了。”杨一很小声地说,“以后也不要提这事了。”
大森听了:“可怜。那我帮你们搬家吧。唉,对了,我们干活,管饭吗?”
“到时候喂你点食物。”
“为什么?什么时候?”大森说,“哦,我是指你分手的事。”
“前些时候吧。他想有一个小的BREAK ,看看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走下去。我同意了,我也知道这类似于分手吧。好,报告完毕。”
“噢,这样啊。我估计人家也是被你吓跑,铩羽而归了。女孩子还是要温柔一点才好。”大淼点点头,若有所思,“唉,我一直希望有个美国人可以收留你,现在连美国人也不要你了,你怎么办呢?”
杨一瞅了他一眼:“男人话多有时真让人烦。你不要像一个妇联主任一样,好不好?”
“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美国男人可能会被你的假象迷惑,和中国人没有接触的美国人,通过好莱坞电影了解中国女子,才会觉得现代的中国女子还是温柔又体贴,会把老公伺候得像个KING(国王)。我姐夫就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娶一个中国女子。娶了,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苏锐走近杨一:“有什么想不开的,跟组织上说说吧。”
“你们不要这样嘛,没事也让你们惹出眼泪来。”
“杨一,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帮你四处看看。”
“要找一个具有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正气,莎士比亚TOBEORNOTTOBE(生存还是死亡)的深沉,岳飞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的人。”
“完了,你是找不到的了。我看你还是趁早死心吧。”
杨一撇嘴道:“不觉得现在的男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少了男人顶天立地的气概吗?二十多岁的男性同胞都自称,我们男孩子……唱歌都是些什么‘心太软’、‘其实我很可爱’,这种发育不全的‘男孩子’怎么敢找?找了,你还得帮他挑润唇膏护肤品。”
这个场合,大森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要这么讲,我就有话说了。那二三十岁的女性也都是自称我们女孩儿,注意,不是‘女孩子’,是‘女孩儿’,带着儿童的色彩。一边如此自称,一边和男人耍帅、比酷,这女人也不像女人了。而且话多,女子的‘口舌’在古时候是休妻七出之一。”
“这个现象可以从以下两点分析,第一点……”
大淼和杨一都有诲人不倦的嗜好,自认站在真理一方,对方也没有说错什么,就是一个忍不住想辩倒对方。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两个忍不住,对话相当的精彩,也好笑,就像听相声。
家搬得差不多了,杨一把天舒拉到一边:“他们帮我们搬家,我们请他们吃饭。我们一人出一半,买外卖回来,怎么样?”
“好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你去买。”
“我?”天舒指指自己,“第一天和你搬到一起,就要我为人民服务。”
“好了,去吧。”
天舒闷着脸出去了,回来带了外卖和啤酒。苏锐喜欢喝啤酒,说是液体面包。大森则笑苏锐喝酒不行。
“苏锐啊。一杯下去,轻言细语;两杯下去,甜言蜜语;三杯下去,豪言壮语;四杯下去,胡言乱语;五杯下去,无言无语。”
从大淼那儿知道关于苏锐的许多事,比如他喜欢看《三国》,睡觉前读一小段,他喜欢早睡早起,天舒听得咯咯直乐,问:“还有呢?”
“还有什么?”大森说。
“关于苏锐呀。讲他的事情。”
“你这个人还挺无聊,爱听这种小道消息。”
天舒也喝下大杯的啤酒,但愿长醉不醒。她知道爱上一个人时,会如同喝醉般的晕头晕脑——苏锐愿与她同醉吗?
当天晚上,天舒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给父母写信。
她一写字就忘字,可还得写这种没啥重点又不得不写的信。
告诉他们她搬家了,不要再往旧住址发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停住笔,自己好生奇怪,她从来不这么对父母说话,动了笔,怎么就是这个模式?她换了张纸,又写“爸妈,你们怎么样了?”
这么写来,也觉得不顺,又换了张纸,还原:“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杨一则坐在饭桌前做作业。教授在课堂上讲了新闻大意,叫学生当场写出报道。这是杨一最头疼的。教授的新闻信息里面大量的地名人名、社会背景,杨一觉得比较吃力。
有一次,教授讲到一个人物说的一句话,全班同学都发出会心的一笑,杨一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看见别人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下课问同学,才知道是美国卡通片里的主角,是美国人成长的一部分,就像中国的“孙悟空”一样,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杨一只能生吞活剥地记下了一串的英文,然后回家反复推敲。现在算是渐人佳境了。只有杨一自己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这时天舒在房间里问:“杨一,‘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啊?”
杨一不耐烦地说:“查字典。”
“你不就是我的字典吗?”
“别问我,我是文盲。”
“你要是文盲,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识字的人了。”天舒从房间里出来。
“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反应得过来吗,我。”杨一指指手头的英文作业,对天舒说。
“别人不行,你行的。”天舒已经将纸张递到杨一的眼皮底下。
“这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小学毕业啊?”杨一边说边往纸上写字。
“太长时间不写汉字,忘了。”天舒看了那两个字,叹了口气,“我发现我的英文没有直线提高,中文却是直线下降了。”
杨一做完作业,到楼下倒垃圾,看到一个沙发,还算可以,匆匆跑上楼来,要带领天舒去搬。天舒还在写她那封家书,头也不抬地说:“现在黑灯瞎火的,看也看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一团狗屎在上面。明天早上再去搬吧。”
第二天早上她们再去的时候,沙发已经被“捷足者先登了”。杨一连声叹道:“可惜了,你都不知道那沙发有多好,否则也不会一个晚上的工夫就不见了。”
天舒摇摇头,笑杨一:“没得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原本那沙发只是不错而已,现在被人捡走了,就变成很好的沙发了。”
周末,天舒和杨一开车去YARDSALE (庭院旧货摊),买了一张电视机台子,七元;一张餐桌,还有几把椅子,十二元。
往回行驶,老远就看见一个牌子,提醒大家注意,这里住有聋哑人。杨一立刻放慢了车速。一个说:“说到残障人士的福利,美国实在比中国好太多了。”
另一个说:“是啊,美国任何场所都有无障碍空间,有优先的停车位,有自己的卫生间……”
正说着,杨一看见那位“最有趣的人”威廉教授与一个小男孩穿过马路,杨一把车子往路边一停,下车叫住教授。
教授见到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在他的脸和身上溢开:“你好,这是我的儿子。”
杨一半弯下腰:“你好,小家伙。”
小家伙礼貌地对她笑笑,没有说话。
教授解释了一句:“他是一个聋哑儿童。”
“哟?”杨一小声地叹了一句,原来刚才看到的牌子是为老师的儿子而设,她连忙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带着刺到人家隐痛的内疚。
教授笑笑,风趣地说:“你不需要道歉,你并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杨一望着这位“最有趣的人”,心想他真是少有的坚强。
她想起不少同学说过,做他的家人,每天都会有听不完的笑话。上帝与他开了一个怎样的玩笑——儿子永远无法听到父亲绝妙的幽默。
教授看出了杨一的所思所想:“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工程师,儿子出世后,当我知道他是一个聋哑儿童,有相当长的日子,我痛苦不已。我问上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惩罚?在儿子出生前我们为他所买的风铃、电子琴就像一个讽刺,我愤恨地把它们砸烂。这时,我的儿子‘哇’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他完全听不到我砸东西的声音啊。突然间我明白了,他虽然听不见,但他看得见父亲愤恨的样子。他看得见,而且比我们这些人看得更清楚。打那起,我决定重回学校学习语言,手语,肢体语言。对,他仍旧听不见,但他可以享受我肢体语言的幽默,而我享受我言语的幽默。我们都很快乐了。”
“教授,您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谢谢。现在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常感谢上帝,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礼物。其实人生只是一个态度问题。”
“什么态度?”
“以前我是每一件事上抱怨,无一件事上感恩。现在是每一件事上感恩,无一件事上抱怨。”
杨一与天舒开车继续行驶,似乎听见小孩子开怀的笑声。
三、相爱容易相处难杨一和天舒还是合适做室友的。天舒烦做饭做菜,杨一正好相反,对于家里的事,除了做菜,什么都不爱理。家里付房租、电费和电话费都是天舒的事。
天舒自认为比杨一细心,杨一也趁机省心。到了月底,杨一就递给天舒一张支票,说:“我的房租。”天舒很认真地看看,以免杨一出错,看过之后,说:“知道了,没问题。”活像个二房东。
做饭做菜,自然就落在杨一头上。通常是杨一做菜,天舒洗碗。天舒虽不会做菜,因著有一个中医师母亲和学了生化专业,常常讲一些让杨一不知所措的话:“夏天吃牛肉对人体不好。”有一阵子又传出鸡肉也有问题,天舒忧心忡忡地说:“听说笼养的鸡肉含有尼古丁,吃多了,人会越来越笨。”杨一起初不以为然,听得多了,上了心,有个学生化的室友,使得百无禁忌的杨一看着冰箱里的食物,顾虑重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做饭做得多了,也成了习惯,后来,天舒一进门,就问:“可以吃饭了吗?”好像杨一做饭是理所当然的,而她天舒回来吃饭也是天经地义的。
而天舒洗得多了,很气愤杨一浪费碗筷的作风。杨一做一盘番茄炒蛋,洗番茄用一只盘子,切完番茄放人另一只盘子,打蛋一只碗,做好的番茄炒蛋又另换盘子。她做一道葱爆牛肉用了六只盘子。每晚天舒要洗一水池的碗筷。
“杨一,你省一点用碗用盘,你看这一水池的碗盘,不知道的以为我们这里住了十个人呀。洗碗很辛苦的。”天舒盯着重重叠叠的碗筷说。
“做饭也是很辛苦的。”杨一不以为然地又往水池里塞了两只碗。
“那以后我做饭,你洗碗。”
杨一似笑非笑,天舒见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做饭给你看就是了。”
第二天,天舒下厨。天舒确实不常下厨,杨一考察了一下厨房,立刻下了这个结论。天舒做菜毫无章法,先后次序不分,手忙脚乱却进展缓慢。杨一不帮忙也算了,偏偏每十分钟就进来一次,说些诸如此类的话:“咱们什么时候有饭吃啊?”“今天晚上能吃上饭吗?”“要是实在不行就吱声,我可以帮你。”
终于天舒端出一桌子菜,说:“四菜一汤,我们提早进入小康了。”
杨一见一桌黑不溜秋的东西:“能吃吗?找找看你那儿还有没有保济丸。”
“你尝尝就知道了,味道不错的。”
“天舒,你真是贤惠啊。”
天舒含笑道:“这么快就有共识了?”
“你真是闲(贤)得什么也不会(惠)啊。”
天舒抿抿嘴:“我是脑力工作者。”
“这么说,好像我是体力劳动者了?”
两人哈哈大笑。不过,两人很快有了矛盾,杨一觉得她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找好朋友做室友,相爱容易相处难,就跟朋友之间不要有生意往来一个道理。
一天晚上,天舒正在洗碗,杨一说了句什么,天舒在哗哗的洗碗声中,叫:“你说什么?”杨一以极快的语速重复:“这个LONGWEEKEND(长周末),我要去LA看望同学,把我的伙食费去掉。”
天舒呆了一下,也嘟囔了一句什么。
哗哗的水声中,杨一说:“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我周末常去我表姐那儿,伙食费也该去掉。”
天舒说完自己也有点难为情,转身洗碗。
“可周末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在外面吃呀。”
“你还常常请人来家里吃饭。”
“你请的人多,还是我请的人多……”
天舒把水龙头一关,还想说什么,可这哗哗哗的音乐背景没了,话也说不出口了。
突然间,水声没了,话声没了,寂静得很。两个人都为对方如此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不快。各不说话,各自回房,各自想事。
门被敲响了,杨一想去开门,才出她的房间门,见天舒已经先行一步,杨一转身回房,关了门。
进来的人是她们的邻居台湾女生雅惠。杨一、天舒私下里叫她“非常女孩儿”。雅惠年轻爱玩,每一个星期都要租几盘录相带回来看,除了BLOCKBUSTER 的英文带子,还到中文录相带店租,最爱租来看的是《非常男女》。她看完了,租期还没到,便拿过来给天舒和杨一看,说那是台湾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杨一既然是学传播制作的,可以看看。杨一说:“你这么爱看,是不是也要上一次《非常男女》?”雅惠说:“我妈妈说了,在美国什么黑的、白的,别乱找,遇见马英九那样子的,就赶快找一个。”逗得她们哈哈大笑。
雅惠的父亲同天舒的父亲一样,是早年的留学生。雅惠的父亲也对雅惠提及当年他留学的事情,说那些大陆学者和留学生生活极为节省,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有次他向一位大陆同学借一个夸特(二十五美分)打电话,之后就忘了此事。几天后,那位大陆同学不见他来还钱,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那天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父亲没有明白,那人又说,那天你打电话……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