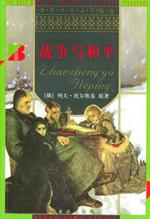布什战争内阁史-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第8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8)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第9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9)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9)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第10节:士兵和水手(1)
士兵和水手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季攻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越南海岸附近的一艘6门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服役。短暂的“春季攻势”令美国人措手不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舰上,阿米蒂奇焦虑不安,闷闷不乐。在无线电里,他听得见枪炮大作的声音:美国陆军来回冲杀;海军陆战队在交火;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叫。在阿米蒂奇与战斗行动之间,是一片汪洋,他鞭长莫及。
阿米蒂奇一年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在亚特兰大长大,是个头发黄中带红、胸脯滚圆的青年,他总是喋喋不休,身体特别健壮,参加四种体育活动,是皮尤斯X学院高中班里的联合班级主席。他的计划是拿足球奖学金,上肯塔基大学或者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但是父亲成功说服海军的足球教练招募了他。①
一到安纳波里斯,却发现阿米蒂奇虽然体格健壮,速度却不足以加入校足球队。在高年级的时候,他担任了新生足球队的教练。他还参加举重,每周在这项后来变成毕生的业余爱好上花许多小时。他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里奇”,有时候又叫他“骡子”。毕业时,海军学院的年级年鉴《幸运口袋》用这番话总结了阿米蒂奇在校期间的情况:“里奇翻开一本书的时间从来超不过一小时,但他总能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由于个性杰出,里奇是全大队的知名人物。”②
毕业时,阿米蒂奇打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要好的朋友、足球队的中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未婚妻的室友、一位名叫劳拉·桑福德的姑娘,使他改变了计划。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经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最显赫、最成功的商人的千金。阿米蒂奇坠入了爱河,于是,他决定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是到一艘海军驱逐舰上去服役,然后回家结婚。这些计划一直持续到“春季攻势”使他意识到就在附近的战争离他有多么近。“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时代的这些重要事件而不去更积极地参与其中,”阿米蒂奇许多年后解释道。③
他极想离开舰艇,因此,他志愿去南越,给那些乘坐小型船只在那个国家的热带丛林和内陆地区的混浊的河上巡逻的“浑水海军”担任顾问。他接受了四周的越语培训,然后仓促地投入了战斗。阿米蒂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作战,而不愿享受呆在舰船上的安全。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再志愿参战,宁愿去面对危险而不愿贪图安全,并且参加了越战中一些最艰巨和最秘密的行动。
对于科林·鲍威尔来讲,在越南执行作战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选择。鲍威尔选定了美国陆军作为自己的职业,于是,陆军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1962年,在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的最初日子里,陆军派遣鲍威尔去驻扎在老挝边界附近的一个南越步兵师担任顾问。美国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 3 200 名增加到 11 000名,他是其中一员。
鲍威尔的父母是牙买加移民,定居在南布朗克斯,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发现自己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纪律、结构和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于是便把训练团的项目作为大学生涯的核心,最后升任管理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团的学员队长。④1958年毕业后,他按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要求服了三年兵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陆军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是个黑人青年。除了当兵之外,其他我一无所知,”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能干什么呢?在成衣工厂区跟我父亲一起干吗?……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能比此提供更多机遇的道路了。”⑤
他在布雷格军营的非常规作战中心学习了五周,然后于196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西贡。能够参战使他感到兴奋。这是分配的而不是选择的任务,但分配的任务不错,说明陆军是重视他的。“我成为职业军官同僚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凡是被选中去南越的人,都被认为是有前途的,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