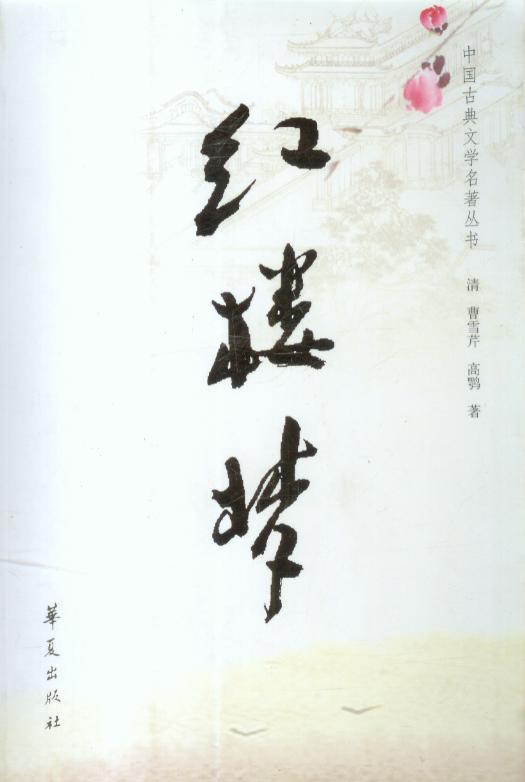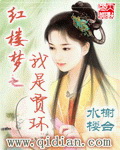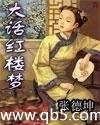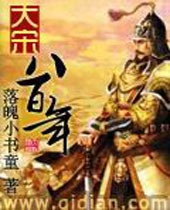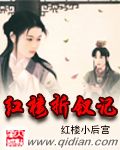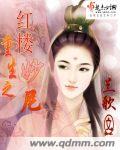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碍需要克服。钱锺书先生在论翻译和原作的关系时说:“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者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电视系列剧和多集影片,作为一种译本,应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成败得失究竟如何,似值得探究。
《红楼梦学刊》五十辑,我却说了这样一番话,近乎红学呓语。如果读者把我这番话看做“异兆发悲音”,可是事前不曾想到的。如同《红楼梦学刊》一出十二年我当初不曾想到一样。国际红学会已经开过两次,这有点像“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如果开第三次,正合“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我想也一定是一次盛会。
下篇“这鸭头不是丫头”
《红学呓语》上篇写好之后,恰值海峡两岸红楼文化恳谈会在上海举行,我随喜着参加了此项活动。海峡那边来了三十多人,其中不乏研究《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是一支“红楼梦文化之旅”,上海的活动结束后,还将挥师北上,去杭州、过苏州、到南京、下扬州、走燕京,沿着曹雪芹的足迹寻踪探胜。上海的活动,也是以游览青浦大观园、参观红楼文物展览、观赏以《红楼梦》为内容的文艺演出、品尝红楼宴为主,学术研讨不是重心所在。台湾“红楼梦文化之旅”领队康来新教授问我,参加了这样的红楼文化活动,我坚持的学术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说改变倒不一定,但对《红楼梦》的诠释,确可以有多种方式。“红楼梦文化之旅”活动,似乎也可以看做是诠释《红楼梦》的一种尝试,至少有助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走这么一趟之后再来读《红楼梦》,感受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感到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一个《红楼梦》是作为清中叶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红楼梦》,它属于十八世纪;另一个是不同时期读者心中眼中的《红楼梦》,它属于今天和明天。后一个《红楼梦》随着读者的参与性阅读而常在常新。两种红学,一种是研究《红楼梦》本文和作者家世生平及版本流变有关问题,另一种是从《红楼梦》和作者的世界中走出来,把《红楼梦》描写的内容作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特别着重从渊源和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比如红楼建筑、红楼服饰、红楼茶艺、红楼宴饮,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戏剧、电影、绘画、书法、篆刻、雕塑、陶瓷、编织、刺绣等等,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评价,如何看待。光是大观园,现在就有三处,即北京南菜园附近的大观园、河北正定的大观园和上海青浦大观园。正定我没去过,不知具体情形。北京和上海的大观园,建筑都颇见特色,开放以来,游人络绎不绝。《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虽有江南园林和北方皇家林苑的蓝本,终是拼凑加工改造过的,绝不是把现实中的某一个真实的花园原封不动地搬入书中。因此研究者说是随园也好,恭王府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假设,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弊。可是如今竟然把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大观园,在生活中复制出来,而且是三处,群众也表示认可,不能不说是对《红楼梦》影响研究的一种补充和创造。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4)
《红楼梦》里成为贾府贵族生活组成部分的饮馔,与其说是物质享受,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以此我曾提出: “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这话说于1986年,不久,“红楼宴”就在大江南北竞相摆起来了。这次上海红楼文化恳谈会,内容之一就是到上海扬州饭店品尝丰盛的红楼宴。刘姥姥摇头吐舌、口念佛祖,说得“十来只鸡来配”的“茄鲞”虽没进入席面,“姥姥鸽蛋”却使宴席平添气氛。只是熟读《红楼梦》的与会代表到底比刘姥姥聪明,很少有人夹不起鸽子蛋,至于“滑下来滚在地下”的事故,更没有发生。当然刘姥姥的闹剧,是凤姐和鸳鸯一手导演的,为的是“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鸽蛋滑落的事故,说不定是演员的“规定动作”,似乎也不便作为昔日书中人物和今天的读者孰愚孰明的依据。“红楼宴”中另一道菜是“老蚌怀珠”,显然出自前些年所传《废艺斋集稿》中所谓敦敏《瓶湖懋斋记盛》残文,《集稿》真伪固不可知,其中提到的“江南佳味”却再现于二百年后的宴席,信乎红楼文化影响之深也。此外“雪底芹荤”、“宁荣姣龙”、“南酒套鸭”、“粉黛眉酥”、“鸳鸯烧卖”之类,不一定样样都有出典,品其色香味,自是淮扬菜系无异。大观园有主南主北的分野,“红楼宴”则一色江南肴馔,说明《红楼梦》的读者,眼之于物、口之于味,各有取意焉。恰好证实属于今天的《红楼梦》,是随着读者的诠释意向来转移的,离开新的时代的读者参与,谈不上古典作品的新生。
但红楼文化的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典范,传统文化的结晶,对《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做深入探讨,自是红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者做出过努力。只是包括上面提到的红楼园林建筑、红楼饮馔在内的红楼梦文化,现在人们注重的不是从学理上加以研究,而是用各种方法进行实施。曹雪芹把生活变成艺术,红楼文化活动又把艺术还原为生活。看来这种还原的努力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台湾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却大力传播《红楼梦》描写的十八世纪的文化生活,是否会有负面的作用。上海恳谈会后,我与另外几位朋友赴浙江省平湖县做《红楼梦》演讲,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红楼梦》里的文化能不能成为今天的生活准则。我说当然不能以《红楼梦》的文化内容作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准则,那样就未免可笑了;但《红楼梦》中描写的众多的文化现象,例如不识字的丫鬟却懂得接人待物的分寸感,以及贾宝玉选择恋爱对象不仅重视容貌,尤其重视思想追求上是否志同道合,这些即使到了今天也不无启发意义。第四十回凤姐和鸳鸯导演由刘姥姥演出的闹剧,黛玉笑岔了气,史湘云撑不住喷出一口茶,宝玉滚到贾母怀里,惜春拉着奶妈叫揉揉肠子,读到这里,读者恐怕也要笑倒,可能不会注意在这幅百笑图之后,作者还有重重的收梢之笔,那就是凤姐向刘姥姥解释:“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鸳鸯更进来道歉,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以凤姐之尊、鸳鸯之贵,竟然向一个乡野村妇致歉赔不是,可不是一件小事,甚至比刘姥姥演闹剧本身的分量还要重得多,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补充性肯定。这件事情背后的文化内涵,足可以超越时空而传之久远。
台湾电视记者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因为这涉及对清王朝的文化举措和文化生活的总体看法,也涉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认识。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入关以后,中经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帝,有过稳定时期、极盛时期、衰落时期、灭亡时期。当极盛时期,版图、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是超一流大国。但在文化上,不论处于哪一时期,都表现出十足的小国心态。别的不说,在所谓“康乾盛世”,不也是文字狱最惨烈、思想统治最严酷的时期么?清代朴学固然前无古人,成就巨大,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不也是学者们被挤压得无路可走,才去匍匐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吗?学术的发展常依赖于学术以外的因素,倒也是学术史昭示的一个法则。只不过后世的研究者,有时难免看到了学术成果,却忽略了这些成果取得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四库全书》以及其他大型类书的编纂,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建设,其功德足可永世;另一方面未尝不是笼络和控制人才,强化思想统治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还不要说编纂《四库》过程中对古籍滥加删改,毁书二千四百余种的巧夺奇劫。经纪昀、陆锡熊等加工润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目列清晰、介绍简明,为人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方便,但馆臣们写的小序和案语,同时也是在古代著作和后世读者之间筑起的一道障壁。因此我总以为,清代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扭曲,既不如唐代文化的恢弘博大,也没有宋代文化那样深邃自由,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像明代市民文化生活那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就拿服饰和男女发式而言,清代和唐、宋、明的装束相比,美丑妍媸昭然可见。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唐宋时期传播的多。如果红楼文化仅仅指的是清代文化,我想台视记者的问题不难回答,也可以说不是有无负面影响的问题,而是应不应弘扬传播的问题。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5)
《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其实不那么简单,虽说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社会生活,却有长期积淀起来的具有恒定因素的文化成分渗透其中,这些成分不仅属于清朝一时一代,而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物而被作者和读者所感知。古代文字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有《红楼梦》这样丰盈的文化包容量。我们从《红楼梦》里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可以说尽在其中了。换言之,《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流露的文化精神,很多可以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传播。何况曹雪芹的思想中残存有反满情绪,或者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具有“汉族认同感”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和《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两文有专门论述,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3页至第210页,台北联经公司1981年版。,因而在具体描写中,官制历代互用,服饰非满非汉,甚至小姐、丫鬟的脚是小脚还是天足,红学家都深感难辨参见唐德刚的《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51至第16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及《本书》第272页至第274页。,可见《红楼梦》作者用心之苦,亦可见处在当时历史环境所反映的满汉文化冲突之重。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应该是个说不完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
但时下人们所提倡并力图加以实施的“红楼文化”,偏重于实用文化和世俗文化方面,所以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前面我曾说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所谓“应用红学”,应该属于那一种?对《红楼梦》反映的文化现象做学术研究,如前所说,是红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应用不应用的问题。但举办《红楼梦》服饰展、摆“红楼宴”、酿《红楼梦》酒、表演《红楼梦》茶艺,就有点应用的味道了。但这是红楼文化的应用,是让古典进入现代生活,不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红学。《红楼梦》八十回之后,有后三十回或后四十回;一百二十回之后,有各种续书。红学研究,有红学与曹学的分别,曹学又分芹学与脂学。历史上,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小说批评派红学,是红学的三大学派。如今红学衰微,“红楼文化”出焉,随之又有“应用红学”之目。莫非应了“礼失,求诸野”那句古语?可是,这种发展前景是曹雪芹和他的古典文学名著的幸还是不幸?是红学的兴旺还是不兴旺?
也许我不过是白居易笔下的“上阳白发人”,当贞元、元和之际仍穿着天宝年间流行的“小头鞋履窄衣裳”,不知时世已换“宽妆束”。但我想学术研究总有别于时装展览,学者无须随时世来转移自己的观念和方法。如果一定认为“应用红学”也是红学,可以用得上《红楼梦》里史大姑娘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之谓也。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再检讨
我在本书初版的时候写过下面一段话:“现在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说,固然是实情。但如今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畸轻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曲则显得不够。
实际上,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缺乏对红学索隐一派的深谅明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