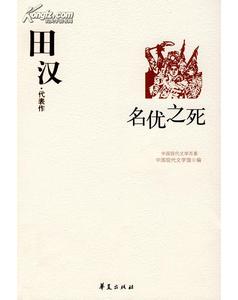人民文学0701-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小跑的耳边说;你一定要挺住;我很快就出来的。陈小跑迷糊中;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王小奔离开的时候;闭着眼的陈小跑准确地握住了王小奔的手;慢慢地;他自动松开了;因为他握不住。王小奔愣愣地望着病床上的陈小跑;终于;他走出了病房。
再然后;大炮、杨子和拖油瓶;一起送王小奔去派出所。
那是一扇亲切的铁门;铁门上方;用铁条焊出一个五角星的形状。现在它无声地打开了;像是一条河流的闸门。所长就站在院子里;他换了衣服;那是一套老旧的钉着胶木扣的军服。所长也是一个老兵出身。所长看到王小奔走了进来;所长就笑了;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王小奔说;所长;你为什么不穿警服穿起了旧军装?
所长说;我是老兵;我也是侦察兵。我要穿着旧军装去看看小跑。
王小奔说;所长;小跑说你太瘦了;你要再胖一些。
所长说;我一定会胖起来的;我不胖起来我就不姓华。
这时候王小奔才知道;所长是姓华的。
华所长说;你进去吧;没几天就可以出来。王小奔就向里走去。这时候;铁门外的大炮喊起来;大炮说;王小奔;我想在赵家镇上开一家油条店;我会炸油条的。
王小奔回转身;点了点头。
大炮又说;王小奔;我们等你出来;一起炸油条。等我们赚了钱;再一起去看瘦的西湖是什么样的。
王小奔又点了点头。他笑了一下;挥挥手;继续向派出所院子的深处走去。走过一棵冬青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去年下雪的时候;这棵冬青身上一定积下了好多雪;陈小跑一定看到;风中那些从树上落下的雪;飞扬起来的样子。王小奔在冬青树边稍作停留。他仿佛听到冬青树笑了一下。他又抬起脚步;继续向里走。
王小奔的身影消失了。夏天真正来临;植物开始疯狂生长。
'责任编辑 徐则臣'
父亲的愿望
忻晟和忻斐是在火车站碰面的。他们要回一趟老家。老家在一千公里远的南方;坐火车得十余个小时。
是忻晟先到站的。忻斐生活严谨;办事从来都是从从容容、有条不紊的。她是在约定的那个钟点到的。忻晟听到火车站的钟声刚敲了五下;忻斐就出现了。忻斐一身黑衣;手上的包也是黑色的。他们姐弟俩快一年没见面了;忻斐还是原来的样子。一张娃娃脸;眼睛很大;眼神里有一种幽怨而固执的气质;好像这世界亏欠了她;这使她看待事物总是有那么一种放肆而无礼的神情;好像什么都看不顺眼。
“到多久了?”
“一会儿了。”
“进站吧。”
车站里人很多。人挤着人。忻斐几乎是搂着她的黑包。忻晟本想替忻斐提包的;那包应该是有些重量的;但又想了想;觉得还是算了。
通过了检票口;一会儿就上了火车。这趟车的卧铺票一直很紧张;没搞到;他们只好坐硬座。硬座车厢已挤满了人。忻斐不大适应这种闹哄哄的场面;她显得很紧张。忻斐看到身边站立的那几个民工模样的脏兮兮的男人;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她没把她的黑包放到行李架子上。她已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把包搂在怀里。她那不安的模样;就好像她的包随时会被人抢了去。边上的人满怀好奇地看她几眼。
忻晟觉得刺眼;说:“姐;你还是放下吧。”
忻斐的脸上毫无表情。忻斐总是这样紧张兮兮的。不过;她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包放在自己的身边;那个靠窗的位置上。包占据了自己的座位;她只好把身体外移;屁股的一半悬在座位外面。她正襟危坐的样子;就像一个正在接受老师训斥的小学生。
一会儿;列车启动了。坐着的和站着的乘客各就各位;车厢似乎也不像原来那么挤了;但声音依旧很大。列车的广播声;旅客的吆喝声;列车服务员推销食品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声浪涌动;此起彼伏。
火车的速度很快。车窗外掠过的景物显得很模糊;傍晚的光线照在这片模糊上;呈现出一种明晃晃的金色。但不久;这金色慢慢消退;变成灰暗色。
天暗了。车厢里的灯亮了。窗外的灯也亮了。忻晟和忻斐一直没有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忻晟看着窗外;透过窗外的灯光可以辨认出一个村庄或一座城镇。
车厢里依旧乱哄哄的;一些人开始打牌;一些人摆起了龙门阵;一些人则喝起了小酒。
忻晟感到很困。这段日子。他经常失眠。奇怪的是;到了这乱哄哄的场所;他倒想睡觉了;就好像这人声鼎沸是最好的安眠曲。他不好意思在忻斐前面睡去。支撑了一会儿;可眼皮总是盖下来。他的太阳穴也麻痹了;好像整个脑袋都要失去知觉了。他可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睡意。
“姐;我困死了;我睡一会儿。”
说完;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差点把口水都打出来了。
“你睡吧。”
“你也睡一会儿;明天一早还得办事呢。”忻晟的口气显得含混而幼稚;有那么一种底气不足的讨好的味道。
忻斐冷漠地点了点头。
忻晟后来是被一声尖叫声惊醒的。那尖叫声骤然而起;短促、敏感;就好像一把匕首刺入了某人的胸膛;刚想叫出声来就戛然而止。
忻晟已在睡梦中辨认出叫声的来源;他的心狂乱地跳起来。他快速睁开眼睛;看到忻斐惊恐不安的脸。她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好像她刚才被人强暴了。她在座位边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低头搜寻座位底下;一会儿看忻晟;她几乎要哭出声来了。忻晟发现放在靠窗位置的那只黑包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刚才还在的呀;怎么不见了呢?”
她急不择言;说话结巴;一反平常有条不紊的说话腔调。她着急的样子;就好像生命的某个部分消失了。
“不要着急;没人要的;再找找看。”
忻晟虽是这么说;他自己也急了;就好像他又做了一件错事。在忻斐面前他总是犯错。他怕忻斐埋怨他刚才睡得像死猪;他趴在地上;试图发现丢失的黑包。
一无所获。
忻晟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多了。边上站票的乘客都成了陌生面孔;火车肯定已停靠了数站。他想;也许有人顺手牵羊;把包拿走了。
忻斐的尖叫声惊动了整节车厢;乘客纷纷往他们这边涌;前后左右都是人头。他们好奇地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有乘客在转述:那女人的包被偷了。
“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不知道;那女人一直把包放在身边;肯定是宝贝。”
有人问忻斐:“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忻斐默默地流着泪;呆呆地坐着;像傻了一样。
忻晟没好气地回答:“没什么。”
他对这些看客充满了不耐烦。
这时;乘警来了。旅客自觉地让出道来。见到乘警;忻斐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她说:
“我睡过去的时候还在的;偷的人肯定在前站下车了。”
又说:“我们要下车;请你们马上停车。”
乘警没说话;他甚至没看忻斐一眼。
“听见没有;请让我们下去。”
忻斐悲伤地大叫起来。忻晟是知道的;这个看上去平静的女人;激动起来是不可理喻的。忻晟因此很怕她;她干什么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让他无端生出自卑来。他知道要求列车停下来很无理;但他无法劝她。他劝不动她;也说不过她。
乘警站在一边观察了一会儿;轻轻地对忻晟说:
“你们去乘警室说吧。”
乘警把他们带到乘警室;然后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列车长。列车长神色相当严峻。好像出了天大的事情。
“包怎么被偷的?”列车长尽量和蔼地问。
“我一直放在身边的;只睡过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忻斐没吭声。忻晟也觉得开不了口。
“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次是乘警在问;口气相当严厉。乘警满眼狐疑;警惕地打量着他们。忻晟有些慌了;他想;怪不得这么大阵场;看来他们在怀疑包里面可能藏着违禁品。
“究竟是什么东西?不好说吗?”
忻晟不想引起什么误会;没必要惹麻烦啊。他想了想。结结巴巴地说:
“也没什么东西;只是一只骨灰盒。”
乘警好像没听清楚;反问:“什么?”
“是一只骨灰盒;是我父亲的。”
忻斐突然无声地哭了起来;哭得相当悲伤;相当压抑。她的哭让人想起那些忧郁症患者;想要竭力掩饰;结果还是控制不住;终于越来越歇斯底里。
“请你们把列车停下来;让我们下车。”
列车长和乘警都没回音;面无表情地坐着。
“求你们了……”
忻斐太悲伤了;无法再说下去;哭泣让她无法表达。
列车长有些动容;他说:“这不大可能;列车运行是有时间的;否则会乱了套。”
“求你们了……”
“火车动了;谁也别想让它停;否则要挨枪子的。”
这话是乘警说的;说得相当决断、冷漠。
回到座位上;忻斐依旧不能平静下来。
她说:
“我们在前面一站下车吧;我们一定要找到父亲……”
忻斐似乎完全投入到对父亲的哀思之中;她悲伤的眼泪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就好像父亲刚刚离开了人世。她呜咽道:
“爸;你好可怜;你怎么这么可怜……”
忻晟不知如何安慰忻斐;在忻斐面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他认了;总归是他做错了;忻斐心里面对他的不满和怨恨他都能理解。
父亲的死和忻晟有关。父亲死之前的两年是在床上度过的。有一阵子;忻斐奉父命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忻斐就让忻晟暂时照顾父亲。父亲因为卧病在床;是请了小保姆料理的。小保姆怕忻斐。忻斐在的时候;不敢松懈。可碰到忻晟就彻底放松了。一放松;出了大事。一天晚上;小保姆去和男友约会;忻晟也不在家;结果父亲突然心脏不舒服;因心肌梗塞而暴毙了。
忻晟明白;这回自己的祸闯大了;忻斐和父亲的情感是如此深厚;忻斐无论如何是不会原谅他的了。
忻斐一直没结婚。她和父亲住在一起;照顾着父亲。不知是为了照顾父亲而不想结婚;还是另有原因。忻晟和忻斐很少交流彼此的想法。父亲年事渐高后;对忻斐非常依赖;而忻斐也把照顾父亲的职责当成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忻斐对父亲的情感;忻晟一直不是很理解。他想;大概忻斐崇拜父亲才会这样吧。总之;忻晟认为这次自己是罪孽深重;对不起忻斐。
忻斐在父亲死亡这件事上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冷静。她没有哭;把所有的悲伤都隐藏了起来。她的坚强和隐忍里面;有一种令人动容的脆弱气息。忻晟本以为忻斐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忻斐并没有指责他。她一句话也没说。这让忻晟心里没底;在忻斐面前低三下四的;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他好想忻斐骂他一通。
忻斐开始着手父亲的葬礼。她想把葬礼搞得轰轰烈烈。她通知父亲的单位及市有关方面;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忻晟因为自觉罪孽深重;对忻斐的行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谓言听计从。照忻晟的想法;人都死了;身后的哀荣都是可笑的。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着。忻晟遵忻斐之命去墓园买了墓地;但这时;姐弟俩发现了父亲的遗嘱;在遗嘱里;父亲希望自己葬在成华墓园里。成华墓园是一处革命公墓;里面埋葬着的都是高级官员;在本市;成华墓园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忻斐不愿违背父亲的愿望。她让忻晟退掉了新买的墓穴。但是要实现父亲的遗愿并不容易。成华墓园的墓穴十分紧张;早在五年前已经冻结;仅有的几块墓地是给市里的大人物存留着的。总之;按相关规定;父亲要葬于成华墓园还不够级别。
忻斐和忻晟只好去求人。忻斐对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惊人的固执和激情。她全身心投入到落实父亲遗愿的奔走之中;好像唯此才能告慰父亲。她找过很多领导;托了很多关系;惊动了父亲的朋友;但是一无结果。
忻晟对父亲的愿望非常不理解。不过想想;似乎也符合父亲的性格。父亲虽然大名鼎鼎;可人们想得起来的学术成就还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创立的;一九四九年他归国后;虽然在历次运动中并无太大的冲击;但在学术上几乎一事无成。晚年。父亲作为国家工程院院士;也算德高望重;管着一个科学机构;父亲表面上顶着科学家的光环;事实上是个官员。他好像也喜欢自己是一个官员或革命者。父亲说起革命教条来;不会输于一位政工干部。他想;这恐怕同父亲年轻时对革命一直存有浪漫的想法有关。因为这份浪漫;父亲才会在一九四九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不顾阻挠回到了祖国。
忻晟不喜欢父亲那副动辄讲大道理的习惯。忻晟是有点烦父亲的;他一直认为父亲有点“左”。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子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这种严苛近乎变态。忻斐原本是个能干的人;在一个机关工作得很出色;在快要提拔为处长时;父亲给组织部门写了一封信;信中父亲说忻斐天真、头脑简单、易冲动;不适合成为一个领导干部。希望组织严格把关。父亲的信让组织部门惊异;组织上也不想得罪父亲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考虑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索性安排忻斐做了父亲的专职秘书;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令忻晟不能理解的是;父亲竟邮芰俗橹庖话才拧P藐扇衔盖自谡饧律咸运健2还?父亲多年来一直只想着自己的声誉;没有好好照顾过他们姐弟俩;就好像他们姐弟俩只不过是父亲光芒下的尘埃。
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市里来了不少大人物;当他们问忻斐有什么要求时;忻斐没提别的;就提了父亲的遗愿。市领导答应会考虑这一要求。可父亲葬于何处一直悬而未决。忻斐只好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里。
忻斐说;如果父亲不能葬于成华墓园;那她宁愿让父亲待在家里。
三年来;忻斐一直在为这事奔走着。
忻晟对忻斐的狂热不能理解。他认为她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有一天;忻晟实在忍不住;说:
“父亲为什么要挤到那地方去呢?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和那些达官贵人和所谓的‘革命家’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这是父亲的心愿。”
“难道父亲葬在那里;他在天堂就会高人一等?”
忻斐的脸上露出鄙弃的神情。她不想同忻晟这样无知的人辩论什么。忻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忻斐对自己的家庭一直是有优越感的;有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幻觉。
每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忻斐必定会打电话给忻晟;商谈父亲的


![(霹雳mit同人)[霹雳mit]亲爱的007老公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80.jpg)

![(好男同人)[07好男同人]一路上有你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