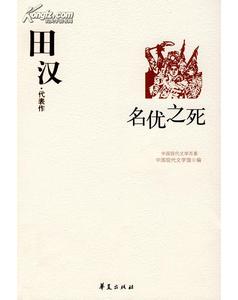人民文学0701-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人的嘴唇动了一动;发出一个极为微弱的声音。与其说沃尔佛医生听到了女人的话;倒不如说沃尔佛医生感觉到了耳膜上的一些轻微震颤。过了一会儿;那些震颤才渐渐沉淀为一些含义模糊的字眼。
沃尔佛医生突然醒悟过来女人说的那句话是“救我”。
女人的话如一柄小而薄的铁锥;在沃尔佛医生的思维表层扎开一个细细的缺口;灵感意外地从缺口里汩汩流出。
“请你躺下来;雪梨。”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之后;女人身上的蓝条子渐渐地平顺起来;变成了一些直线。女人的双手交叠着安放在小腹之上;袖子翻落着;露出右腕层层缠绕的纱布和纱布上一些形迹可疑的斑点。
“闭上眼睛。”
女人脸上的黑洞消失了;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谧。
“雪梨。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十年。请叫我小灯——那才是我的真名。”
“中国名字吗?”
“是的;夜里照明的那个灯。”
“小灯;你对两方心理治疗学理论了解多少?”
“弗洛伊德。童年。性。”
女人的英文大致通顺;疑难的发音有些轻微的怪异;却依旧很容易听懂。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是怎么看的?”
“一堆狗屎。”
沃尔佛医生忍不住轻轻一笑。
“小灯;上一次发生性行为;是在什么时候?”
女人的回应来得很是缓慢;仿佛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心算。
“两年零八个月之前。”
“上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一次女人的反应很快;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和停顿。“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七岁以前不算。”
“小灯;现在请你继续闭眼;做五次深呼吸。很深;深到腰腹两叶肌肉几乎相贴。然后放慢呼吸节奏;非常;非常;非常缓慢。完全放松;每一丝肌肉;每一根神经。然后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两人都不再说话;屋里只有女人先是深沉再渐渐变得细碎起来的呼吸声。女人的鼻息如一条拨开草叶穿行的小蛇;窸窸窣窣。草很密;路很长;蛇蜿蜒爬行了许久;才停了下来。
“窗户;沃尔佛医生;我看见了一扇窗户。”
“试试看;推开那扇窗户;看见的是什么?”
“还是窗户;一扇接一扇。”
“再接着推;推到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那扇窗户;我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女人叹了一口气。
“小灯;再做五次深呼吸;放松;再推。一直到你推开了;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女人的呼吸声再次响起;粗重。缓慢;仿佛驮兽爬山一样的艰难。
沃尔佛医生撕下桌子上的处方笺;潦草地写了两张便条;一张给凯西;一张给自己。
给凯西的那张是:立即停用一切助眠止疼药物;改用安慰剂。
给自己的那张是:尽量鼓励流泪。
1976年7月24日 唐山市丰南县
李元妮在一条街上挺招人恨的。
李元妮是她在户口册上的大名;其实在街坊嘴里;她只是那个“万家的”——因为她丈夫姓万。街坊只知道她丈夫姓万;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众人只称呼他“万师傅”。当然万师傅只是当面的叫法;背后的叫法就很多样化了。
万师傅是京津塘公路上的长途货车司机;一个月挣六十一块钱工资;比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还多出几块钱。万师傅个子极为壮实;常年在路上奔走;晒得一脸黑皮。十天半个月回趟家;搬张小板凳在门口一坐;高高卷起裤腿;一边搓脚丫子上的泥垢。一边吧嗒吧嗒地抽闷烟;那样子和搂草耙土的乡下人也没有太大区别。别看万师傅一副土老帽儿的样子;他却是一条街上见过最多世面的人。万师傅常年在大城市之间走车;大城市街角里捡起来的一粒泥尘;带回小县城来也就成了时兴。虽然万师傅对自己很是苛省;但对老婆孩子;却是极为大方的;每趟出车回来;总是带回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万家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和一条街上的人都有些格格不入。
李元妮招人恨;除了丈夫的原因;也还有她自己的原因。李元妮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被省歌舞团挑上;练过几个月的舞蹈。后来在一次排练中摔成骨折;就给退了回来。李元妮回来后没多久就嫁了人;过了两年又生了孩子。同样是人的媳妇人的妈;李元妮和街上那些媳妇那些妈却很有些不同。李元妮的头发上;永远别着一枚塑料发卡;有时是艳红的;有时是明黄的;有时是翠绿的。那发
卡将她的头发在耳后拢成一个弯月形的弧度;衬着一张抹过雪花膏的脸;黑是黑;白是白。李元妮的外套里;常常会伸出一道浅色的衬衫领子;有时尖;有时圆;有时锁着细碎的花边。李元妮的衣兜上;常常会缝着一颗桂圆色的或者砖红色的有机玻璃纽扣。李元妮穿着这样的衣服梳着这样的头发;一踮一踮地迈着芭蕾舞的步法行云流水似的走过一条满是泥尘的窄街;只觉得前胸后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目光;冷的热的都有。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目光;这些目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夭的演员生涯留给她的种种遗憾。
这一天万家院子里很早就有了响声;是李元妮在唱歌。李元妮的歌声像是有了划痕的旧唱机;一遍一遍地转着圈循环着——因为她记不全歌词。
温暖的太阳啊翻过雪哦山
雅鲁藏布江水哦金光闪闪啊啊啊
金光闪闪;金光闪闪……
街坊便猜着是万师傅回家了。只有万师傅在家的日子里;万家的“那个”才会起得这么早。果然;李元妮的唱机还没转完一圈;屋里就响起一阵滚雷似的咳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那是万师傅常年抽烟造下的破毛病;万师傅呸的一声吐出一块浓厚的痰;连声喊着他的一双儿女:“小登小达;再不起来我和你妈就走了。”这天万家四口人是盘算好了去李元妮娘家的——李元妮的小弟在东海舰队当兵;正赶上在家歇探亲假;李家的七个兄弟姐妹约好了;一起在娘家聚一聚。
小登小达却一点也没有动静。昨晚天热得有些邪乎;两个孩子挠了一夜的痱子;到下半夜才迷糊着了;这会儿睡得正死。李元妮走过去;看见小登手脚摊得开开的;蛤蟆似的趴在床上;一条腿压在小达的腰上。小达的脑袋磕在膝盖上;身子蜷成圆圆的一团;仿佛是一个缩在娘肚里等待出生的胎儿。李元妮骂了声丫头忒霸道;就将小登的腿拨开了。
小登是个女孩;小达是个男孩;两个是龙凤胎;都是七岁。小登只比小达大十五分钟;多少也算是个姐姐。小登一钻出娘胎;哭声就惊天动地的;震得一个屋子都颤颤地抖。一只小手抓住了接生婆的小拇指头;半天都掰不开——是个极为壮实的丫头;小达生下来。不哭;接生婆倒提在手里;狠狠拍打了半晌;才有了些咿咿呀呀的微弱声响;像是一只被人踩着了尾巴的田鼠。
洗过了包好;放在小床上;一大一小;一红一青;怎么看都不像是双胞胎。养了两日;那红的越发地红了;那青的就越发地青了。到了一周;那青的竟气若游丝。万师傅不在家;李元妮的娘在女儿家帮着料理月子;见了这副样子;就说怕是不行了。李元妮叹了口气;说你把那小的抱过去再见一见大的;也算是告个别了;到底是一路同来的。李元妮的娘果真就把小达抱过去放在小登身边。谁知小登一见小达;呼地伸出一只手来;搭在了小达的肩上。小达吃了一惊;眼睛就啪地睁开了;气顿时喘得粗大起来;脸上竟有了红晕。李元妮的娘跺着小脚连连称奇;说小登把元气送过去给小达了——姐姐这是在救弟弟呢。
从那以后小达就一直和小登睡一张床上;果真借着些小登的元气;渐渐地就长壮实了。小达似乎知道自己的命原是小登给的;所以从小对小登在诸事上就是百般忍让;不像是小登的弟弟;倒更像是小登的哥哥。
李元妮拨弄了半天;也弄不醒两个孩子;却看见两人的头底下都枕着个书包;便忍不住笑了。那书包是孩子他爸出车经过北京时买回来的;一式一样的两个;绿帆布底子;上面印着天安门和首都北京的字样。孩子们名都报上了;只等着九月就上小学了。昨晚吃饭的时候他爸把书包拿出来;两个孩子见了就再也不肯撒手;一晚都背在身上。李元妮去抽书包;一抽两个孩子就同时醒了;倏地坐了起来;两眼睁得如铜铃。
李元妮在每人脑勺上拍了一巴掌;说快快;早饭都装饭盒里了;边走边吃。太阳这个毒;赶早不赶晚。说着就和万师傅去推自行车。万家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二十八寸的永久;是万师傅骑的;一辆是二十六寸的凤凰;是李元妮骑的。虽都是旧车;李元妮天天用丈夫带回来的旧棉丝擦了又擦;擦完了再上一层油;两个钢圈油光锃亮的;很是精神。
李元妮的娘家虽然住得不算太远;可是骑车也得一两个小时。大清早出门;太阳已经晒得一地花白;路上暑气蒸腾;树叶纹丝不动;知了扯开了嗓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嚷得人两耳嘤嗡作响。万师傅的车子最沉;车头的铁筐里装的是果脯茯苓饼山楂膏;那都是从北京捎回来孝敬丈母娘的。后头的车架上坐着儿子小达;儿子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兜里是两条过滤嘴的凤凰烟;那是给老丈人的。李元妮的车子就轻多了;车梁上只挂了小小一个水壶;后架上坐着女儿小登。儿子是叉着两腿骑在后车架上的;女儿懂事了;知道女孩子不该那样;就并拢两腿偏着身子坐在单侧。一家人风风火火光光鲜鲜地一路骑过;惹得一街人指指戳戳;却是不管不顾的。
那天万师傅戴的是一顶蓝布工作帽;原是为遮阳的;结果攒了一头一脑的汗。那汗顺着眉毛一路挂下来。反倒迷了眼。索性就将帽子取下来;一边当扇子扇着;一边就问李元妮;我说娃他娘;要不把他舅接家来住几日?孩子们跟老舅最亲。李元妮说好倒是好;只是住哪儿?万师傅说反正我明天出车;先去天津;转回来再去一趟开滦;转一圈一个星期才回来。他舅来了;跟小达搭铺;小登跟你睡;不就妥了?
小达在车后踢蹬了一下腿;说我不嘛。李元妮就骂;怎么啦你;不是成天说等老舅来了教你打枪的吗?小达哼了一声;说我还是跟姐睡;你跟舅睡。万师傅听了嘿嘿嘿地笑;说娃他娘;你看看。你看看。别家的孩子总扯皮打架;我们家这两个是掰都掰不开呀。
骑了两三刻钟;就渐渐地出了城;天地就很是开阔起来;太阳也越发无遮无拦了。小达直嚷渴;李元妮递过水壶;让小达喝过了;又问小登喝不?小登不喝;却说饿了。李元妮说饭盒里有昨天剩下的馒头;自己拿着吃吧。小登说谁要吃馒头呢?我要吃茯苓饼。李元妮就骂;说这丫头什么个刁嘴;那是给你姥姥的;哪就轮到你了?小登的脸就黑了下来;哼了一声;说那我就等着饿死。万师傅听不得这话;就对李元妮说不就一个茯苓饼吗?两大盒的;哪就缺她那一张了?李元妮刀子似的剜了万师傅一眼;说那还是你闺女吗?我看都成你奶奶了。两个孩子就在后头吃吃地笑。
便找了一片略大些的树阴;将车停下了。李元妮从盒子最上头小心翼翼地抽了两张茯苓饼;一张给小登;一张给小达。小登撕了一小块慢慢地嚼着;一股甜味在舌尖清凉地流淌开来。突然;她停了下来。那股来不及疏散的甜味;在喉咙口集聚成了一声惊惶的呼喊。
她看见路边有一些黑色的圆球;排着长长的队列;旁若无人地爬行着。后面的咬着前面的尾巴;前面的咬着更前面的尾巴;看不出从哪里开始;也看不见在哪里结束;歪歪扭扭地一路延伸至原野深处。
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那些圆球是老鼠。
1976年7月28日 唐山市丰南县
万小登对这个晚上的记忆有些部分是
极为清晰的;清晰到几乎可以想得起每一个细节的每一道纹理。而对另外一些部分却又是极为模糊的;模糊到似乎只有一个边缘混淆的大致轮廓。很多年后;她还在怀疑;她对那天晚上的回忆;是不是因为看过了太多的纪实文献之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她甚至觉得;她生命中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那夜很热。其实世上的夏夜大体都是热的;只是那个夏夜热得有些离谱。天像是一口烤了一天的瓦缸;整个地倒扣在地上;没有一线裂缝;可以漏进哪怕细细的一丝风来。热昏了的不仅是人;还有狗。狗汪汪地从街头咬到街尾;满街都是连绵不断的狂吠。
万家原来是有一架电风扇的;那是万师傅用了厂里的旧材料自己装搭的。可是这架电风扇已经在昼夜不停的运转中烧坏了机芯;所以万家那晚和所有没有电风扇的邻里们一样;只能苦苦地干熬。
母亲李元妮这晚一个人睡一张床。父亲出车了;两个孩子和小舅挤在另一张床上。母亲和舅舅不停地翻着身;蒲扇噼噼啪啪地拍打在身上;声若爆竹。
“老七呀;上海那地方;吃的跟咱们这地方不一样吧?”母亲问对过床上的小舅——小舅的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区。
“什么都是小小的一碗;看着都不敢下筷子;怕一口给吃没了。倒是做得精细;酸甜味。”
母亲羡慕地叹了一口气;说难怪南方那些女子细皮嫩肉的;人家是什么吃法;咱是什么吃法。听说南边天气也好;冬天夏天都没咱这儿难熬吧?
“人家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天比咱们这儿暖和多了;夏天白日也热;到了晚上就凉快了;好睡觉呢。”
黑暗中母亲的床上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小登知道是母亲在脱衣服。母亲从来不敞怀睡觉的;可是这几天母亲实在熬不住了。
“你说小七啊;今年是不是热得有些邪乎?你看看小登小达身上的痱子;都抓得化了脓;他爸回来见了那个心疼啊。”
小舅就嘿嘿地笑;说我姐夫平日见了谁都是个黑脸;可就见了这两个小祖宗;一点脾气也没有。
母亲也笑;说你还没见过他爷爷奶奶的样子呢。你姐夫家三个儿子;才有小达这么一个孙子;他爷爷奶奶恨不得把小达放在手掌心上当菩萨供起来呢。
小舅摸了摸小达的腿;瘦瘦的;却很是结实。没动静;大约是睡着了。“这孩子身子骨倒是长好了呢;性情也好;是个招人疼的样子。不过我看姐夫;倒是更宠小登。”
“闺女长大了是爹娘的贴身棉袄;不过小登这孩子的脾气;唉。”母亲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说;“七;你睡吧;这两个冤家缠你讲了一夜的话;也倦了。”
舅舅嗯了一声;蒲扇声就渐渐地迟缓低落了下去;间隙里响起了些细细碎碎的鼻鼾。小登的眼皮也黏耷了起来;却觉


![(霹雳mit同人)[霹雳mit]亲爱的007老公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880.jpg)

![(好男同人)[07好男同人]一路上有你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