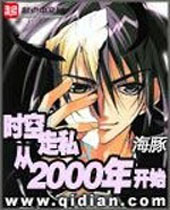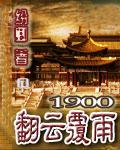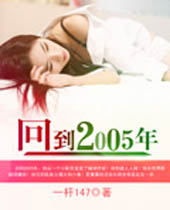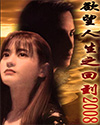当代-2003年第1期-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之后的,更近处的记忆都泯灭在身体的深处了。说起来不合乎逻辑,这一刻突兀在混沌之上,如此孤立地存在着。它一直停留于走在台阶中间几级的地方,前边和后面,全隐没在光晕里。安静之前的哭闹,印象全无,只是感觉,这样的安宁,不会是持续的,而是在强烈的悸动之后,肌肉紧张到痉挛,再松弛下来,方才可以达到,深入骨髓的安宁。
天空特别温柔,抚慰着一个哭闹到筋疲力尽的婴孩。全是由于莫名的不安,身体内的,电解质忽然错乱了排序。这深藏不露的奥秘,没有人能够参透。在电线杆子上,贴着的那种粗糙的黄裱纸,纸上写着语般的歌谣:“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就是这无助的求助,求向莫名的路人。这时,波涛平息,不是静如止水的“静”,而是潜深流静。婴孩的四肢无限地伸展,电解质经过激烈的调整,重新排列组合,达到和谐。这样的宁静,其实是处在高热之中,体温上升到一个高度,肌肉松弛开来。在我相当长的一个发育过程中,都是以高烧来和解体内的错乱不安。高烧使我的眼睛分外清澈,天空映入眼睑。巨大的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是安全,安心,我开始体会到身下那个怀抱的温意,带些粘滞的。那是我的奶母,我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只是知道,她摇着我,哄我的一句话是:长大了带你去六合。于是我知道,她是六合人。
在婴孩的知觉中,看见的和知道的,总是混杂的。知道的,在混沌,内外不分的意识中,溶进视觉,变成可视的画面。就像原始人,凭着知道的情形,画出侧面耸立的鼻子上方,两只正面的眼睛。但在这一切混杂的知觉中,那眼望星空的安宁,不会有误,一定是在直观的范畴内。
我的身体,是以疾病的方式进入知觉,它以不适唤起注意。因食欲旺盛,我时常感觉到腹胀腹痛的折磨,还有,药片“食母生”的无味与干涩的折磨。这两者使我啼哭不止。有一回,母亲从同事处得到一则偏方,将砸碎的核桃壳,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调合成一种褐色的药膏,用绷带裹在肚脐上,睡一夜。一夜过去,坚硬的肚子真的变得柔软,那忽如而过的轻松,亦刻进了知觉。非常奇妙的,疼,涨,绞,一切挣扎全消。我越过婴孩平坦的胸脯,看着柔软的腹部,四肢张开着。由于这种身体的舒适感,人便经常地回进婴孩的身体内,这时候,却有了全视的功能。就像电影里的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在此合二为一。这影像越过许多年头和阅历,一点没有褪色。在母亲的大床上,早上凌乱的被褥上,摊平了的身体,面对后弄的窗,进来光,均匀地布满房间。舒适,只有婴孩才可有的,洁净的舒适。脏器全是柔软,娇嫩,敏感,只一点点错序便颠覆了全盘。那一种精致的结构,所达到的平衡,岌岌可危,亦无比的舒适。这舒适使人沉静下来,沉静到虚空来临。
尤其是午后,酣睡中醒来的一霎那。由于孩童对时间的不客观,这一霎那在身体中变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段落。房间里没有人,窗外进来阳光——此时,是向南的房间。光线是晶莹剔透的,将物体表面的绒毛都照亮了。在一段酣睡之后,明亮中睁开眼睛,视觉里注满光明,眼前的物体有一种膨胀的效果:松软,和暄,空虚。身体沉思着,飘渺起来。最贴近眼睑的物体,棉被压在脸上的一角,儿童铁床上的护栏,被眼距分离开,变成重影。这是一个奇幻的景象,你好像同时在不同的位置上注视对相。并且,你可以自由地调节,将双重合成单重,再分成双重。影像在视觉里离析,变化,不再是确定的,以至渐入茫然。那无度的明亮使一切太过敞开,没有遮蔽,无依无托,人浮在空间中,轻和虚,略一持续便害怕了。
婴孩也许真有着全视的功能,因它是方才从另一种物质转换为人,这种物质,它的体内残存着上一种物质的余骸,所以就有了旁观的立场。否则,我便解释不了这些记忆的画面完整性,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全面性。我无从解释我为什么会“知道”这许多,我知道的,与我看见的,合成那幅原始人的奇异图案:侧面的耸立的鼻子上方,两只正面的眼睛。这图案远比原始人刻在洞穴的岩壁上的,来得自然和正常。当那舒适感在身体内部伸展开来,周遭的环境似乎全成为条件而存在着。松弛,舒泰,和顺,从肢端流淌出去,迎合着环境。环境是单纯的,没有压迫,不需要抵抗。此时,婴孩还没有完全作为人——这种物质,从环境剥离开来,它还没有挣脱环境——这个温床,与之亲密地贴合着。然后,渐渐分离。婴孩脱去它的最后一件胞衣,胞衣随风漫卷,腾作一片星空。婴孩是星空下的籽,降落下来,种进人类。
这间朝向后弄的小房间,倚墙放一张大床,将近占去一半面积。床对面的窗下,是书桌,顶一侧墙放,另一侧墙,立一具大橱。似乎已经挤满了,可是,橱和书桌之间,居然安了一架烟囱炉。炉座挺高,烟囱直升天花板,将抵未抵时拐一个弯,伸出窗户——玻璃窗上割一个圆洞,正好容烟囱伸出。我感到犹豫的是,这床安置的位置,究竟是什么方向。是头顶南墙,还是侧过来,头东脚西——西墙上有门,因床抵着,只够开大半扇的。从房间的全局来说,是后一种比较合理,可是从我视线的角度,则是前一种。许多景物我是从那个角度看见的。我头顶南墙躺在枕上,下巴颏顶着胸脯,看前边,房间里的景物。这间大约八平方米的小房间,四角渐渐清晰,细条木质地板显现出水波般的纹理,窗帘遮住惟一的向外的窗户,将空间关闭起来。再说那个烟囱炉。这个烟囱炉使房间更挤了,然而,还是有空余,供安放一个洗澡的木盆。空间就是这样有弹性,它近乎是柔软的,就像刚成形的蛋,壳是皮质的一般,可以变形。不过,基本的格局是定下了,床,橱,书桌,三足鼎立,拉开了房间的四壁。
木盆里的水气,铁皮炉的暖气,还有炉上坐着一壶水,蒸气掀开壶盖,将房间罩得雾蒙蒙。雾气中有晃动的人影,还有许多声音。这雾气,人影,声音里,包藏了亢奋的情绪。总有压抑不住的悸动,是快乐的,而且激昂。寒冷的没有供暖的江南冬天,人裹在层层棉,毛,绒,布中间,像做茧的蚕。现在,一层层地剥下了,肌肤接触到空气,有着莫名的刺激,陡然紧缩起来。汗毛孔闭住,收起来,一粒粒的。然后,水又来了,刺痛着,针尖样的小疙瘩在刺痛中放松开,无遮无掩,完全失去抵抗。水一层一层上去,滑下,渐渐安静下来,适应了在空气中裸露,快乐便油然而起。水气充斥了房间的四角,以及家俱切分出的无数角落,均匀地飘浮着微小的水的颗粒,空气就变成有形的了。房间的棱角都有些抹圆了,那些家俱的几何形也变得圆润,边缘毛绒绒的,温和地存进眼睑,特别容易被吸纳。心里有一种快乐,小孩子通常叫作“开心”,在这变形的空间里洋溢开来。原先间离着的四壁,此时变得贴身了,合体,而且绵软,蓬松,暖和,沿着身体的轮廓拓出空间,容纳人体进去,随了人的动作移动改变位置和形状。很像在水里游呢!
后来,门开了,只一小条,是由于被床抵着了,或是生怕室内的温度流走,只开了小半扇。进来一个人,雾气中拓开一张脸,是母亲的脸。母亲的大衣帽子的毛边上,布着水珠,寒冷的水珠。室内的空气有一阵的搅动,冷与暖在交替中互相碰撞,躲闪,然后调和起来,恢复了平静。母亲在空间中占了很高很大的位置,渐渐深入进来,脸上是笑容。她手上举了两张硬纸片,是车票,两张车票,妈妈和姐姐的,我的呢?疑虑间,两张车票后面出来第三张。我乐得一声尖叫,这个场景在小魔术的演出后陡然落幕。
这个朝北的封闭的小房间,盛着暖热,水气,还有亢奋。将房内的空间撑得很满,每一丝裥皱都拉平了。照理是令人感到窒息的,可奇怪的是,非常舒畅,自由。它的封闭只是使人有保护,伸手便可握住些什么,身体有依托。而且,在那里面,有着一股情绪,逐步推上高潮,这增添了激越的动态。
空间,就像舞台。有了舞台,里面多少就有了一些情节。也或者是反过来,先是有情节,方才开拓出舞台。那幽密的光线之中,这里,那里的隔离,投下暗影,背景就有了深度。透视的效果越来越强烈了,近大远小,景和物愈益立体。原始人所表现的“知道”,一个侧面的耸立的鼻子上面,两只正面的眼睛——这平面的图画,渐渐还原了“看见”的真实。光里面,呈现出深浅不一且和谐一体的影调。随了“看”进步,全视的功能不知觉间消失殆尽,视觉依着事物表面的顺序展开和进行。视野狭隘了,但却因了逻辑的相衔的链条,可持续攫取影像。这便是情节的来源。当然,在早期,逻辑的锁链还不那么紧密,影像呈出片断性。情节一是不够连贯,二是陷于简单,还有三,声音和图像略有脱节。知觉还没有发育完全,综合能力不够。就像儿童市井游戏:爆炒米花。一只手掌贴了腿来回搓,另一只手握拳捶击,两只手就是协调不起来。许多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都是经过潜在的训练,方才化为本能。
方才,第一幕落幕了。关紧的大幕上,脚灯的光从下向上,打在紫红的丝绒面上,洇开来,一圈湿润的光晕。这是影像与影像之间,相隔的一段暗寂。本来是黑的,但是之前与之后的影像渗进光来,使它微亮着。那是还未被知觉发掘的段落,泯灭在未知中。在此一段的情节里,担任了幕间。微光中,知觉休憩着,积聚着能量,再一次张开,伸出触脚,攫取。下一幕,蓦然地开场了:火车站的候车室。它的辽阔,已大大超出一个孩童的视觉范围,所以,它没有四壁,也没有穹顶,只有一排一排看不到尽头的长椅,还有人。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脚下停了一个旅行包。前后都没有别人,长椅上许多座是空着,并不拥挤,可是,一股令人不安的骚动空气,浮在头顶上方。我感到紧张,似乎四周潜伏着阻止我上车,将我与母亲和姐姐分离的迹象。当那老头悠闲,却有目的地向我们走来时,我再也止不住地战起来。我的腿打着抖,牙齿轻轻磕碰。老头在我们面前站定,背着手,向我们的旅行包微微弯下腰去,问妈妈一句话。我惊惧地看着妈妈,希望她立刻将这只旅行包交给老头手上,可消除他对我们的注意。可妈妈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还用脚踢了旅行包一下。老头直起腰,又向妈妈说了一句话,这一次妈妈答应了一声,然后老头走了。我紧着问妈妈,老头说的是什么,妈妈说,老头让我和姐姐到儿童候车室去。此其间,母亲一直保持着微笑,这与我们面临的被拆散的恐惧非常不适宜。它非但不使我释然,反让我加倍不安。之后,我便处于极度的犹疑中。一会儿,我坚决要求妈妈将我们送去那里,免得老头亲手来拉我们;一会儿,我又坚决表示不去那里。这样不停地改换决心,倒是平息了身体的战。候车室非常暖,并非来自任何供暖的设施,而止是由于人的体温和呼吸,结成氤氲,在室内流动。这多少叫人窒息的暖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我的脚和手,非常温暖,身体烘热着,脑门上沁出汗珠。我们这三个人变得非常小,而且相依为命。接下来的场景是站台。灯光在开放的户外构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火车,站台,也加强了空间的壁垒感。一格一格明亮的车窗,嵌在灰暗的空间里,光照出来,映了一地光。于是,空旷的车站变得狭隘了一些,有倚傍了。人们都在奔跑,我和姐姐也夹在其中。情绪在奔跑中亢奋起来,近乎狂热地,我一边奔跑,一边尖叫,叫着:妈妈,快!妈妈手里提了东西,落到我们身后。妈妈也变得兴奋起来,大笑着,长大衣的下摆裹着她的腿,她努力抬高腿,像个短跑运动员一样奔跑着。我又怕与母亲离散,又怕乘不上火车,火车就开跑,紧张万分。我跑一段,停下来,转过身对妈妈跳一阵脚,再跑一段。我的小棉大衣压着我的身子,箍着我的腋下,妨碍了手臂的摆动,心都快跳出胸膛了,我只得声声尖叫。
我们直跑上火车,跑进那明亮的,温暖的,有着居家气息的小格子里面。我们在空火车座之间来回跑着,这么多的空座,令人欣喜若狂,无奈我们只能占一格。我们的亢奋几乎无法遏制,火车车厢的大小,正好能为我们的视野容纳,它使我们感到安全了。我们的疯狂已经引起旅客们的注意,可是,因为上了车,有了座位,大家心情都很好,没有对我们厌烦。然后,亢奋被等待开车的焦虑替代了。我们一声迭一声地问:什么时候开车?窗外的站台此时显出阴冷乏味,没有生气,尤其与热腾腾的车厢比较。我爬在椅上,手抚着窗玻璃,急切等待窗外变换景色。紧张,亢奋,焦虑,还有奔跑,尖叫,耗尽了我的体力。等到车开,站台移出车窗,灯光逐渐稀疏,最终变成一片漆黑,精神萎顿下来,然后睡着了。母亲预告的山洞,摆渡长江,在睡眠中过去了。这睡眠如此严实,没有渗漏进一点印象。火车在知觉的黑暗隧道里穿行,走过多少公里,经过许多车站,站台上的灯光明亮而又昏晦,静静移过车窗,留在身后。这一串明暗相衔的旅程,全沉落在混沌暖和的睡眠中,没有知觉。第二幕,这高潮的一幕,暗转入下一幕了。我们陡然地在了一条石子路上,那种石块相嵌,形成整齐均匀图案的小街。我们:妈妈,姐姐,我,还有爸爸——爸爸也是陡然多出的,他在这里,这条石子路所属的城市,等待着我们。脚步在石子路面上敲响清脆的声音。就因为这,“石头城”的名字进入印象。其实,完全无干的,可这石子路,路面上清脆的声响,却筑成一座石头城。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