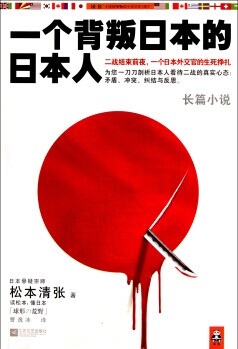背叛 麦冬著2-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投诉的标准也不同,仿佛道德风纪甚至刑事案件在各地的评判标准存异一样,同样的婚外情,有的地方叫搞破鞋,有的地方就是观念开放,同样的贪污金额,在贫困地区就“数额特别巨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却都不好意思立案。
一班最让人挠头的侯山,现在也老实了不少。魏老师鼓动大家对他采取了全面孤立的政策,让他的恶作剧往往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他可能开始怀疑自己的幽默感和搞笑能力,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没有信心再制造闹剧了。
白露说:“一班是不是太死气了?二班倒还有几个开心丸。”小果说你那才叫得便宜卖乖,忘了以前被那些家伙给气得吐白沫了?
这时,施展和苏家栋那里也谈得欢畅,好象俩人有不少共同语言呢。范江山跟我汇报说,“学生奶”的项目马上就要搞了,施展已经联系了20多个学校,一天估计得喝两千来袋牛奶,除掉包括校领导提成在内的费用,一袋也能赚一毛来钱,一天就是二三百块。
“我操,到时候还教个鸡巴书!?”范江山可能是以为那二三百块都是给他的。
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一天就超过我一个多月的收入啊,施展更是夸下让我心动的海口,说一旦赚了钱,就不用我上班了,他们哥几个养着我写作,巴尔扎克不是喝咖啡写“人间喜剧”吗,咱非用鲜牛奶供出一文豪来不可!
我甚至暗暗地有些后悔,抱怨自己没有在先期投入更多的热情。老范则更加活跃,被金钱滚滚而来的声音激动得目光闪烁,很多人也开始把他当未来的款爷看了,说话间充满了讨好和醋意。
岳元那里也有了动静,场部找佟校谈了,说让岳元过精密铸造厂当业务厂长。佟校吸取了错放苏家栋的教训,开始收紧口袋,死活不让岳元钻出去,不惜和场部领导象小孩子似的闹着别扭,而且在教师会上也不点名批评了“青年某些教师”,说学校一直把他们当骨干培养,他们却忘本,被市场经济的铜臭熏昏了头脑。佟校愤怒地说:“谁要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就离开学校去搞,离开我老佟眼皮底下去搞!”我心里又赶紧庆幸了一下:多亏开始就把这个热山芋塞给了老范。
虽然佟校说明了是在批评“某些青年教师”,估计大搞传功创收的邵主任也要恨恨地别扭一把呢。
一面批判着铜臭,佟校又不得不宣布另一项决议,说根据中央方面关于企业改革的新精神,场部要求学校也纳入整改范畴,以后不再跟场部干部一起拿平均奖,要公布量化的教学指标,成绩与奖金挂钩,下面又是怨声飞扬。
会后,涉案的老丁、老范都不屑,继续我行我素,岳元却很受打击,跟我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佟校死板,不给年轻人自由发展的出路。
米亚男嫌他罗嗦,气气地说:“有那个血性,你不会辞职?”
“左右要在桑树坪干,能弄得那么僵吗?再说了,场部也不会同意我先辞职再去搞铸造啊,他们能不照顾老佟的情绪?”
我说佟校可能是老了,想不开了——你这么死硬,场部能不瞧你碍眼?说过了,又觉得误导了岳元他们对佟校的理解,佟校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学校好的,老师都走了,他还搞什么搞?这教育又不象盖猪圈,随便从路边扒拉俩民工就能成的,场部也是混蛋,要调动老师,怎么也得等到学期末吧?而且那个老师的课也需要有个接替才成啊。混蛋。怪不得佟校急。
佟校转悠到初三办公室,看我们都在伏案工作,进来感叹:“看到你们我才塌实点儿,现在这学校快成菜市场了,一个个眼里除了钱还是钱。你们再出来俩折腾的,这学校就黄了,成烂菜帮子了。”
魏老师笑道:“没听说学校还能黄了的,亡国都亡不了学校啊,文化大革命那么折腾,最后这学校不还是得接着开?”
“呵——”佟校看魏老师扭曲了他的意思,很苦恼地长“呵”了一声。
我说佟校放心吧,至少您退休前,我们都得坚守阵地,捧您退了休,我们也就散伙了,这学校是没法呆了。
佟校叹息着,鼓励了我们几句,轻轻地关门走了。我突然觉得有些怜悯他,他在出去的一瞬间,背影如此苍老。
不足一周后,邵主任歇了假,据说是不再来学校了,只等着凑到日子退休了。章书记暂时代管了小学的教导处工作,佟校也不再客气,告诉所有人:谁也不准再在办公室伸胳膊闭眼儿地装神弄鬼,要练您回家练去,什么中功,我看你们都中邪啦。
邵主任一走,很多人觉得空虚不少,华中良更是魂不守舍了许多天,估计是在担心佟校拿他开刀放血杀杀老邵留下的邪气,佟校却偏不理他,甚至依旧让他一个人占着一间已经失去权利象征的办公室,好象在给他足够的空间进行反思。
几周后才把丁茂林从初二办公室挪过去,说是副科老师在一起方便交流,其实,华中良和丁茂林的几门课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地方。大家都说佟校这一调动够损,无非想让华中良明白:你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丁茂林第二。事实上,我们几乎都忘记了,华中良一直还教着初三的生理卫生课,不过这个课行同虚设罢了,哪个老师的课忙了,就挤他一节,他也似乎高兴如此,直到下学期,基本已经没有他上课的机会,考试的时候佟校就吩咐开卷吧。去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从学生到老师,谁把“副科”当回事?只要是中考不考的东西,就没有人在意,你任课老师再认真也白搭,更何况碰上华中良这样识相的。
正 文 第四章:迷乱 22…23
22,“五。四”的前两天,傅康就告诉我们,说青年节那天,红旗农场的团委要带队来,到林三柱的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笑了:“是不是矫情了点儿?林三柱会不好意思的。”
白露道:“远道儿和尚会念经,咱这里都快把林三柱给忘了,人家还真当回事。小傅,你这个团支书,到时候也不能落场啊?”傅康笑道:“我这不就是跟麦麦商量呢嘛,佟校说了,到时候咱俩至少得出一个人给他们讲讲林三柱的先进事迹啊。”
我马上一摆手:“还嫌咱不够忙?让尤校去不完了嘛!要让我说,我可不敢保证不说漏嘴啊,我跟林三柱感情太好了,一动情准露馅儿。”
小果说:“咳,白老师、白老师去啊,再带上侯山,叫这娘俩现身说法去,能便宜了她?”我们都说“好主意”。傅康只好回去商量。
后来决定下来,因为傅康要领学生去场部搞联欢,“红旗”的人来受教育时,我方就由尤校牵头,我陪同,再带上侯山当活人证。佟校指示,到时候让尤校负责介绍,我就去那个捧哏的角色就成了。
“明天,咱还得派几个学生去扫扫墓。”佟校说:“这个事儿傅康安排吧,让小学出几个胆儿大的就成了,看看是不是长草了,清理一下,墓碑也给擦擦,顺便搬几盆花摆着,别太寒碜了。”
安排妥当了,才安心去干别的。
转天放学,白老师带着几个学生,驮着两盆死不了去墓地。我事先跟陶丽说了,当时林小平、毛健和肖壮也和我一起随着去了。白老师说:“你们也去啊,那我就叫那几个小家伙回去了。”我说你们去是工作,我这几个学生是为了感情。白老师看着我们的队伍恨恨地说:“侯山怎么没来?这个没心肝的。”陶丽马上噎她:“我们根本就没叫他!”
林三柱的坟很干净,墓碑上刻着“小英雄林三柱之墓”,也清清爽爽的样子,好象是刚扫过不久的。
“清明那按他家里肯定来过了。”白老师如释重任,抓紧吩咐几个学生把花盆在两旁摆了。虽然做过了战前动员,有个学生还是怯怯地往后退。
我抚摩了一把墓碑,说:“柱子,你的好朋友来看你了,江勇革没来,他现在是人民警察了,替他也高兴一把吧。”
毛健先在一旁抹开了眼泪。
林小平突然说:“麦老师,咱也没带香来。”我苦笑着摇了摇头,陶丽说:“麦老师你给柱子点支烟吧,这小子以前总偷着抽,现在没人管了。”我感觉陶丽的语气里居然有几分调侃,似乎对死亡并不介意。
白老师看我们磨蹭,招呼一声,带着几个小学生先走了。陶丽望着她的背影骂道:“这个白大屁股,我瞅他就来气,以后我看见她儿子再往河边溜达,我就一脚给他踹下去!”
“柱子为她儿子死,太不值啦!”肖壮也义愤填膺。
往林三柱坟上捧了几把新土,我说:“走吧。”
走了好一段路,我还有些伤感似的,在我眼里,林三柱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个喜欢呵呵傻笑憨头憨脑的“坏学生”,不好学、不会学,也没有资质,不过品性还是不错的,仅此而已。如果不是和我亲密相处了一年多,我想他的死对我不会意味着任何东西吧,就象很多人感受到的那样。
突然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很寡情的人,能被什么感动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江勇革和林三柱都离开了,陶丽显得有些落落寡欢,放了学,偶尔就赖着不回家,跑楼上跟岳元我们闲扯,嘻嘻哈哈一通才走。米亚男说她倒挺喜欢陶丽的:看着咋呼,其实心里什么也没有。我说那你收个干妹妹算了。米亚男说那不乱了辈分?我说你真以为师生父子啊,鲁迅还娶了许广平呢。米亚男口无遮拦:“那你干脆娶了陶丽算了,我看这丫头对你可够铁,这样的女孩啊,别看疯野,要是……”不等她说完,我赶紧笑道:“小米你要再乱讲,以后不许进岳元我们俩宿舍啦!”
岳元打岔说:“师兄,我想要尤校那几间平房呢,我跟亚男准备暑假就结婚。你看老尤家那点破东西真值几千?”我说这么快结啊?也好,到时候我继续吃你们去,你们可要负责到底,谁叫你们开始拉我上贼船的,不过你最好先弄两间房就乎着,等将来钱富裕了再换不迟,况且,何必跟内部人弄那个扯不清?
岳元说:“我是怕委屈人家小米不是?”米亚男立刻揭露她:“我无所谓啊,想要好房子那是你自己的虚荣心,我要真想挤兑你,能不叫你买楼去?”
岳元说会的。
“什么?”
“我说有一天我会让你住上楼房的。”
米亚男恨恨道:“没想到你把我想得这样市侩!”玉臂轻舒,已经热烈地给了岳元一个深拧,岳元凄厉的叫声向围墙外窜去,居民区的人一定以为哪个老师又治学生呢。
23,
岳元说,一放暑假,他就马上到铸造厂去了,场部已经答应佟校要新的物理老师来。所以他要我到县图书馆给他借两本企业管理的书来恶补,他说他就不信农场这些当头儿的有几个正经学过“企管”。
施展很早就帮我办了借阅证,每个月我都要去两趟县图书馆,借书或者查资料,顺便也常去方主编那里坐坐。方主编说了两次:小麦你要想调文化口儿来一定找我。逐渐地,我的心思还真的活动起来,不过一时也下不了决心,想这“文化口儿”,也不过和学校一样无聊吧,这两个地方,都有我要追求的东西,到头来,我看到的现实,却都是我希望以外的东西。这里和那里,又有什么区别?想着挺无奈的。
独自呆着时,寂寞的感觉显得有些陌生,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充实地生活下去,我一直相信我有这个能力,直到现在,我开始觉得疲惫、无聊。
前几天小果说:“我现在是打心眼儿里腻歪教这个破书了。”当时我说同感啊,说过又不禁吃惊:我真的有“同感”吗?
我检讨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才发现我顺口说出的话,并不完全是敷衍。
对这种单调枯燥的“授业解惑”的教育,我的确有些厌倦了。我所向往的洋洋洒洒的教育形象越来越萎缩,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模式,学生们以为自己是教育的奴隶,殊不知我们这些老师才是第一批受害者,中国的应试体制其实是由奴才培养奴隶的体制,教师就是奴才——有才的奴隶,郁闷,愤怒而无奈,就是每天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即使能不停地工作、看书、写东西、间或搭帮去喝酒,却偶尔会感到这种强迫症般的所谓充实有些茫然,这时我会想起李云虫对云生我们两人说的话来:“你明白你一生何求吗?”
这样的问题使我痛苦,所以我宁愿回避,我已经没有信心承受那种近乎宗教狂热般的对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诘,浪漫和激情似乎都已远去,偶尔记起大师兄胡致力说的韶光易逝催人老、红了什么又绿了什么的话来,愈发苦闷。
眼前除了混乱,便是迷惘和空虚——以迷乱的“充实”压抑着的空虚。
给云生和李云虫写了几次信,都半路揉掉了,我无法理清思绪,我也不清楚我究竟要对他们说什么?愤怒地倾诉?抑或可怜巴巴地求助?
倒是云生先来了信,他又使我意外,他说他已经离开九河市的公司,去了大邱庄——大邱庄当时正红得血胀,号称“天下第一村”。云生说他想多跑些地方,钱不钱的倒在其次,主要是想增广见识,积累经验,他说他总有一天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给人打工太憋屈。在去大邱庄之前,他已经两下海南、深圳,还跑了其他几个沿海城市,最后还是被“第一村”庄主禹作敏的创业史和经营理念所吸引,决定投怀送抱了。
云生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新鲜的激情,那种活泼热烈的感觉使我仿佛回到从前。我立刻给他回信,写到一半,已经禁不住伤感:“你是一路奔波,在流浪般的路途上不失执著,使人羡慕和怀念;我则步履蹒跚,一路走,一路看着曾经的激情和梦想逐个破灭着、萎缩着,生命还在,却似乎没有了鲜血在流淌的感动,青春似乎失语,呐喊已觉无望,呻吟又恐做作,只好隐忍着堕落。”我说我的处境很尴尬,并且正从尴





![[综漫主k跟背叛]不一样的背叛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