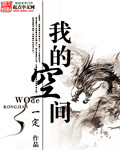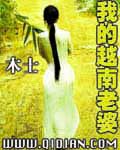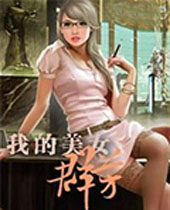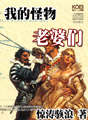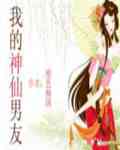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
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
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
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
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
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
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
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即便对某君说,如果《大江东去》出单行本,一定要将日军令人发
指的屠城罪行及光华门之役中国军民的英勇行为,增写进书中。果然第二年新民报社要将此书付梓,父亲
将存稿校阅一遍,删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写了光华门之役及日军屠城的惨状,父亲从来
写书都是根据生活而进行创作的,而《大江东去》则虚构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说:“则其地名人名,即
虚构亦不写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写出者。纪念某班长之壮烈,国家将
来自有恤典在,彼决不与草木腐。此间不实亦无妨。更就整个小说言,正如舞台上之戏剧,自不同于社会
事实。若必一一加以索隐,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不亦可笑乎?”
《大江东去》在连载时,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出了单行本后,更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在当时的抗战文
学作品中,发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则是,父亲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
京军民的血腥暴行。这些场面的如实描写,给侵略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行径做了血淋淋、活生生
的纪录。《大江东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的文艺作品!2005年
恰是抗战胜利及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虽然事隔60多年了,当我们重读《大江东去》时,仍然是热血沸腾
,义愤填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忘历史,中国古训有“殷史可鉴”,所以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大江
东去》及时而真实的描述,对那些想冲淡、粉饰日本侵略军侵华罪恶行径的人来说,仍然是无可辩驳的铁
证!
由于《大江东去》一书的真实描述及曲折的悲欢离合,很受读者的欢迎,所以抗日胜利后,1947年,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女主角是袁美云女士饰演,拍到快结束时,由于北平的解放,这部片
子未能拍完。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曾引起读者很大兴趣的问题,那就是男主人公原型是谁?我看到海内外一些涉及《
大江东去》的文字,都说这是国民党元老钮永健的侄子钮先铭先生亲身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不仅婚变是
事实,而且为了躲避日军追杀,钮先铭藏身寺庙,假作僧人也是真。但是在父亲生前,我没有问过他,所
以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事实,父亲和钮先生私谊不错,据说他是留法学生,文笔很好,
父亲曾约他为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写过连载小说,事隔多年,书名已经忘记了,但是还依稀记得
书的内容是写一位中国留法学生的罗曼史。
我最近看到一篇钮先铭先生生前在台湾发表的《我为什么写———抗战初期南京笼城战血泪
史》,文中钮先生自认不讳地说《大江东去》就是写的他,附笔于此,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考证吧。
第46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
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
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
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
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
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
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
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
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
,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
,诗云:
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春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
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
,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凤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
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
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
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
注云:“ 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
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
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
,每食必饮,饮必‘ 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第47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
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
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
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
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兽杨志”,注曰:“空学得
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
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
“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贴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
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
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
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
,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
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
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黄雀在后”,
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
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
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
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
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
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
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
。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
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
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
,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
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
110114110114 第48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强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
,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
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
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
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
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
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奸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
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
,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
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
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
,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