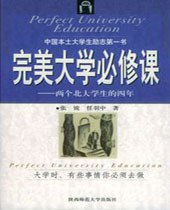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7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红卫兵说“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后来周总理说及回赠
外宾,人家有各种百科全书,我们只有《新华字典》);另一个“梁”,是梁启超公子了,梁
思成的藏书,什么《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以及乃父的《饮冰室文集》等都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其夫人林徽因在笔记本上记有:“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
运 45 车次,计售人民币 35 元”(转引自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45 车 35 元,真是“惊
呼热中肠”。这算什么,太多的例子了。陈垣先生明智,遗嘱捐书 4 万册,俾得所归,而陈
校长所在北师大更有学人刘盼遂夫妇为书烈死的惨烈故事。不独刘先生,为书遭了罪的还有
黄药眠、钟敬文、启功、李长之、谭丕谟、陆宗达、穆木天、袁翰青等。惨烈之余,就有许
多近乎“黑色幽默”的成分。比如黄教授家藏一部《廿四史》,迨罡风起时,实行“大破四
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还有“旧”的物质载体——古籍,
,
黄教授的一部连木箱在内的《廿四史》原来是好友、明史专家丁易先生的转赠,此时顾不得
了,急如星火地奔忙处理,如果实给收废纸的当然再便当不过,可是也太可惜了,只好送人,
给助教邓魁英。邓不敢接受,一是怕连带保护“四旧”的罪名,再说谁家也不宽敞了,何况
邓先生已有一部“图书集成”版的《廿四史》了,也就拱手谢免了,不过建议黄先生可将书
连同木箱平排起来当床,让小孩子睡在上面,庶几可保平安。黄教授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将书搁在家中过道上,那意思仿佛是“鸡肋”——食之无味却弃之可惜的,后终被勒令搬家,
这才叫读书人的“挥泪对宫娥”。书堆放在一边,有个青年站在一边好奇地看,黄教授索性
问道:这书你懂不懂?青年人说倒是颇愿一读。黄教授自是大喜过望,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连说:拿去!拿去!未想世风日下这个小伙子却犹有士风,讷讷地说:没有
钱,怎么好意思白拿。黄教授急问:那你有多少钱?青年说只有 20 元,
:黄教授不假思索:
足矣。楚弓楚得,也是书得所归。说书厄,再不妨看那不显山不显水的。二、中华书局《1949
—1981 年古籍整理编目》 合 32 年所出 1559 种,
, 其中 1966 …1976 年, 78 种,
仅 再其中 1966
年所出悉为 5 月之前;1967…1971 这四年,一书不具;1971 年后除《二十四史》标点本以及
法家人物著作、作为“政治教材”的《石头记》等外,今人研究,其作品只有 1971 年章士
钊《柳文指要》——书,而此书得以问世也尽在“红太阳”恩准以特例对待的(尼克松访华
以之馈赠,赠田中首相则是大字本《离骚》),这算不算“书厄”之一例?三、学人半成品的
书稿,如陈直先生等,手稿亦不得存,勒令上交,不忍,藏匿煤堆中,被发现,尽焚之,马
寅初亦自焚其所著《农书》。再如顾颉刚先生等,先前如何高产,后来“牛鬼”而已,于是
十年学术纪录,只有标点史籍的“伟业”了,但这已经很幸运了,而原来那些谨守治学之道,
以为“四十岁以前要博,以后要逐渐收缩,五十岁以后应该开花结果,写点东西了”(何兹
全)的一代学人在本该厚积薄发的学术巅峰期,与几代青年一样,蹉跎了岁月,一场浩劫,
不但没有开花结果,
“差点连根挖掉”
。于是有人终于恍然,若王亚南华东医院弥留之际对家
人喃喃:“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哑子”不写书,
” “骗子”
写假书,乃众人大多“失语”为哑,作“万马齐喑”状。若不甘,则有顾准式的“地下话语”;
再不甘,欲“地上”作文字魔障,遇罗克、张志新以及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之做噍类而
不可得矣。则寻例可得更有其人后来自忏之“依傍党内‘权威’的现成说法”度日,结果教
训却是“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云云。
“反右”和“文革”的书厄,有形如卖书、焚书以及“刘项元来不读书”的社会推崇,
无形则如《编目》的空缺和学人学术年谱的积年荒芜,以及学人的充聋作哑以及骗和被骗虚
假繁荣的“评法批儒”“评《水浒》”之类的出版业。若据以勾勒一部《中国书厄史》,大概
可以让人从中窥见国家、民族、学人几重的悲哀吧。
托付
刘烨园
(1954…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精神收藏》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有删节。
三十年,仅仅是一瞬么?如果是一瞬,我怎么切肤着几千年何其相似的一切?
早已欲哭无泪。
三十年。异化的泪。
……
1968 年,
“初中”二年级。我读书的城市日夜枪炮骤响,火光不断。担惊受怕的母亲终
于在犹豫中,人性大于政治了,不再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学校、街道“骗”到几百里外的群山乡间,偷偷给了亲戚一
些钱,然后在我睡熟的深夜,又乘火车返回去照顾多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妹了。
我被“撇”在深山里。几次试图归去,终因火车很快在炮火中停开,到处是荷枪实弹的
关卡,天天有身份不明的人被无辜打死的“传闻”而被迫幸存下来。我不知道,这时邮路亦
早已不通了。四个月后战事结束,回到家里,我才“一次性”收到了一百多天在乡下向家里
“诉苦”的七八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大意):
……他们有六个人,都带着枪,是那种汉阳造“老套简”,很旧,擦得精亮、其中
有一个是民兵队长,他有两杆枪,还有一支驳壳枪。村里的人都被通知到了场,大人孩
子都围在水塘边,那儿有很多芦苇,前面的已经被民兵拖着“犯人”弄得东倒西歪了。
我不是村里人,没人通知我,当我听到什么声音赶到时,
“审判”已经完了(是我自己觉
得像是经过了什么仪式似的)。那两个人五花大绑的,都很年轻,大约有二三十岁,穿
着和材里人同样的土布衣服,黑色的,跪在水里,面对芦苇,背对人群,不许回头。这
时民兵队长提着驳壳枪走过去,“代表贫下中农枪毙你”,说完,对着一个人的后脑勺,
上身一偏,一声枪响,那个人就栽倒了(迸出的血果然没有溅到他身上)。他招招手,过
来一个民兵,又给了死人一枪,是用老套筒贴着背心打的,枪声很闷。另一个活着的人
这时哭了起来,哆嗦着,头越低哆嗦得越厉害,终于趴下了,民兵队长把他拎起来,又
给了他一驳壳枪,他中弹了还在哭(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像少年时一样纤脆地颤抖着疼),
周围却一个哭的也没有……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十几步之遥,以这样的名义。在此之前,我只
见过尸体:被批斗而自杀的邻居叔叔、战死的校友、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麻袋中泡涨的无名女
尸,路过村前漫水桥、被大水淹死的武斗队伍中的复员军人……也看见过抬棺游行的队伍,
听说过追悼会上为祭战友而炸死俘虏,几十号人被八毫米铁丝穿着掌心押去枪决等“小道消
息”……这一次的恐怖、惊吓,刻骨铭心,不仅因为是目睹,还因为杀人者曾是我所尊敬的
人。他豪爽热情,助人为乐。十几天前,发大水的时候.他撑着竹排,围着村子给人送东西;
我因水土不服发疟疾,高烧半月不退,奄奄一息.也是他撑竹排从公社医院拿药回来治好的。
就在昨天夜里,我还和他在村里代销店的—张矮桌上有说有笑地打了半夜扑克牌!而他后来
杀人的神态、动作,却是多么当仁不让、坚决、娴熟,甚至悠然自得——回村的路上,没忘
了依旧有说有笑地走在田埂上向旁边的人让烟、逗乐,说谁谁真有福气,娶的女人好漂亮,
好能干!
我那时并不懂法律,不知这是惨无人道的愚昧.只是骇然、茫然,只是震惊、同情;就
这样在“同类”的人群中,如先生(鲁迅)所言,充当着一名默默的看客,终身难宁。
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残忍,死去的人是多么冤枉,已是十几年之后了。
只是十几年后,历史并没有平息。在幸存者的生命里,它的伤恸甚至远远深过当年,虽
然这一次是被史料(官方文件)惊栗的(此史料 80 年代末由该省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1967 年 10 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 76 人;
同年 11 月,某县民兵枪杀 69 人;
1968 年 7 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 46
人;
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 3681 人,使 176 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
中死亡人数的 93%;
同年 8 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 1342
人,俘虏 8945 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 26
人;
还在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
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 1016 人,其中国家干部、工人 260 人,参加过
红军的 20 人、赤卫队的 12 人、游击队的 117 人;全县 86 个大队,81 个杀了人……
真想用“文革”中流行的一句话愤怒地吼一声——够了!够了!因为这还只是风毛麟角,
且还不计“不明不白”
“失踪”十几年的另一些冤魂!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
成批杀人之事,该省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
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
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
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
然而如今真实被拒绝描述。
如此“夜正长,路也正长”,当年先生(鲁迅)被层层淤积的血,埋得不能呼吸时,尚要
挖一个小孔,延口残喘,如今一个想忘也无法忘记的青年,又怎样才能不负重沉沉地生存呢?
我逃得掉吗?命。
异族入侵的南京大屠杀不能容忍,一祭再祭,天下难忘。那么本民族残杀本民族的“文
革”呢?悲剧底因,孰更深层孰更重要孰更惨重?却能掩则掩,能忘则忘,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么?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事件”,五十步笑百步么?不是当年慈禧太后“宁与外
邦,不掷家奴”心态(或曰国民性)的另一翻版么?
然而更糟的是,历史亦并非“无声无息”。在人为的遗忘深处,浮上来的是人为的“撰
述”,各有用心,“宜粗不宜细”,水不仅浑了,而且浅了,浅得没有实质,好像史无前例的
浩劫不过尔尔,让后人看来好笑好玩,不解我们何以如此大惊小怪,“没什么嘛” (我已听
见孩子们如此说过了)……眼见自己亲历的历史如此这般,我由此而大疑前人的历史是否亦
非如“籍”所述。
而且如此那般的如“籍”所述,是否导致了我少年时代目睹的罪恶?
谁言东方文化没有创造性?至少不乏“独到”
。看看德国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反省和浩如烟海的二战“寻根”便知一二了。
三十年无祭。
仅仅是祭,毫无意义。
三十周年的某天,我选择了独自一人默默站在他们墓前。痛苦深得平静,思考亦复杂得
平静。又是大水刚刚涨过,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我曾读书、生活的城市十屋九淹,树梢
也挂满淤泥。人们忧伤,忙碌,个个表情沉重。这样的瞬间,三十年前的死者自然是被彻底
忘却了:然而,这样的生存现实也被我彻底忘却了。存在是对等的。
荒草萋萋。坟茔满山。烈日如昨。我在我的异化里。
异化是必然的。凡事不走火入魔,难有成者。
与其被遗忘同化,我宁肯被铭记杀死……
我们的父亲刘少奇
刘平平 刘源 刘婷婷
刘平平 刘源 刘婷婷,均系刘少奇子女。本文选自《历
史在这里沉思》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
1967 年 8 月 5 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①的大会,分别在
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
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
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
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 “喷气式”
坐 ,
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号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